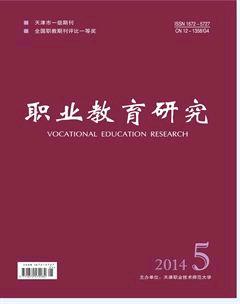“永、久、黃”團體的職業素質教育
陳凱
摘要:永利化學公司、久大精鹽公司、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是實業家范旭東于1914~1922年先后創辦的,統稱“永、久、黃”。久大的精鹽生產結束了中國人幾千年食用粗鹽的歷史,永利的“紅三角”牌純堿更獲得國際金獎的榮譽,黃海社則從技術上支持了久大、永利的生產事業,它們共同為中國的化學工業奠定了重要基礎,開辟了新局面。而取得這些成就的重要前提則有賴于企業精神——“四大信條”對職工素質的凝聚和培育。
關鍵詞:“永、久、黃”團體;職業素質;范旭東;人才觀;四大信條
中圖分類號:G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05-0177-04
“永、久、黃”團體,是天津永利制堿公司、久大精鹽公司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三個單位組成的企業和科研團體,創辦人是著名實業家范旭東(1883~1945),其后加盟共同創業的有著名科學家侯德榜(1890~1974)、企業家李燭塵(1882~1968)以及科學家孫學悟(1888~1951)等,他們都生于封建王朝岌岌可危的清末,個個懷有救國、強國志向。毛澤東在總結近代中國歷史時曾經指出: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要維新,只有學外國,而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范旭東1901年東渡日本求學,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應用化學專業,侯德榜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李燭塵畢業于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后稱工業大學),專攻電氣化學,孫學悟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化學博士學位。他們都是留學外國而尋求救國、強國之道的“求進步的中國人”,也全都是早年的愛國“海歸”、知識精英。
范旭東1912年回國不久,奉財政部派遣赴歐洲考察鹽業,準備在國內建立精鹽制造廠,后因財政部人事變動,精鹽廠計劃流產。范旭東由此萌發了自己創辦精鹽公司的念頭,遂與鹽務署顧問、《鹽政雜志》主編景本白(學鈐)等人于1914年共同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注冊資本5萬元,以“海王星”為商標,工廠設在天津塘沽,管理機構設在天津市區。由于產品符合市場需要,經營得法,多次增資,擴大生產。據統計,1934年久大的精鹽生產運銷量達28萬余擔,占全國精鹽運銷總量的40%以上。久大就是在這塊原本荒蕪的不毛之地,成功地創建了近代中國第一個精鹽制造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長期仰賴進口的純堿來源中斷,英商卜內門洋堿公司囤積居奇,造成堿價暴漲,民眾生計大受影響。1917年,范旭東邀集同道,成功試制出純堿,隨即著手在塘沽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制堿廠。1920年以“永利制堿公司”注冊,資本總額為銀洋40萬元,并獲特許所需之工業用鹽免稅30年優惠。從建廠到1926年“紅三角”牌純堿在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獲得金獎,歷盡曲折艱辛,終于為祖國贏得榮譽。而侯德榜博士創造的“侯氏制堿法”聲名遠揚,更是功不可沒。
注重科學的范旭東,于1922年在久大精鹽公司化驗室的基礎上,又創建了國內第一個私人科研機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取名“黃海”,是因機構地處沿海,資源無限的海洋是他們研究、開發的對象。研究社聘請美國哈佛大學化學博士孫學悟主持社務,并開始招攬人才,購置圖書、儀器,陸續建立了化工原理、應用化學、發酵化學、海洋化學等研究部門,其科研成果不但為久大、永利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為公司培養和輸送了大批技術人才,也為社會其他方面相關化學工業的需要做出了貢獻。
此后,又于1936年在南京建成了永利硫酸铔廠,生產出自己的硫酸銨產品,從而揭開了我國化肥制造工業新的一頁。
“永、久、黃”團體為“互通消息,聯絡感情”,于1928年創辦了《海王》旬刊,它既是團體的喉舌,也是傳播知識、研討學術、團結職工的輿論陣地。這樣,“永、久、黃”就形成了近代中國唯一的私營化學工業團體,不但為中國的化學工業奠定了基礎,打開了鹽、堿、酸生產的新局面,也成為培養中國化學工業人才的搖籃。其間,范旭東經歷了舊鹽商造謠打壓,糾纏訴訟,軍閥綁架勒索敲詐,國民黨官僚刁難、挾持的種種劫難。抗日戰爭爆發后,沿海地區相繼淪陷,“永、久、黃”遭毀滅性打擊,為保全民族工業,決定全部西遷入川,選址重建。1945年“8.15”日寇戰敗投降,“永、久、黃”再度返回天津塘沽,重新恢復生產,個中曲折艱難,非同一般。
確立職業素質目標
自1914年久大精鹽公司創辦到“永、久、黃”團體形成,范旭東團結全體同仁艱苦奮斗,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科學的認識論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精神意識又反過來影響物質存在,世間一切事物都離不開這一法則。范旭東等實業家、科學家最初選擇創業,就是本著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理念,從衰敗落后的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投身化工事業的建設。而其后創業的成功,則是在他們所信奉的理念精神的指導下所獲得的。為總結、豐富、提升團體的理念精神,需要尋求一種更為明確的“團體”的職業素質目標,以便推動“永、久、黃”事業更好地發展。
當1933年久大精鹽公司成立20周年之際,《海王》有文章回顧說:公司之創辦“惟期改良鹽質,以振起國民之新事業,亦即所以富國而便民用”。其后,永利制堿成功,“純堿產量大增,銷路推廣,其輸出日本者亦不下萬噸,創中國化學工業史上未有之先例”。黃海社作為私營科研機構,一種不求名利,只求奉獻,潛心學術研究的風氣更是自不待言。正是黃海社社長孫學悟,于1933年提出了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工廠事業的性質“與其僅只視為生產的,謀利的,毋寧當作一種學校看”,在工廠里學習,進行生產試驗,鍛煉人才,“無處不是要訓練我們做現代的新國民,無處不昭示我們是這社會大學的先鋒隊”。這就意味著需要創建一種企業文化的全新理念。
1934年,團體領導人自覺地意識到建立“團體信條”,也就是職業素質目標的重要與必要,于是通過《海王》旬刊發起了“征集”活動,并成立了專門的“征集委員會”,指出“每個團體都有一個目標,凡屬團體內各個分子,都努力以赴之;有組織,有計劃,有信條,意志統一,步武整齊,一心一德,不顧一切往前邁進,……其事業乃得以成功”。隨后,出現了熱烈研討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見,建言獻策,8條、10條、12條、14條……,不同的見解暢所欲言,活動長達兩個月。endprint
最后,至1934年9月,在《海王》旬刊公布了范旭東總結提煉的“四大信條”,即:“(一)我們在原則上絕對的相信科學;(二)我們在事業上積極的發展實業;(三)我們在行動上寧愿犧牲個人顧全團體;(四)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其內在邏輯是:“相信科學”是根本指導思想和前提;“發展實業”是強國富民的手段;“服務社會”是最終目的;而“犧牲個人顧全團體”則是必要條件。“四大信條”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永、久、黃”團體構想的職業素質目標由此確立了起來。自然,“四大信條”不是突然形成的,可以說從1914年久大初創時起,“四大信條”的不同要素便已存在,此時只是在實踐后的升華。
“四大信條”在《海王》旬刊的每一期都以醒目的字體刊登,至1949年9月20日停刊,長達15年之久,它如滴滴春雨,起到了潛移默化、深入人心的作用。“四大信條”不但是“永、久、黃”全體職工的行為準則,更是其團體前進發展的共同目標和不竭動力。
培育職工職業素質的舉措
范旭東認為:“事業的真正基礎是人才”,“事在人為”,“凡事待人而興”,這是他創業、興業的一貫認識和實踐的結論。范旭東不但廣攬人才,特別是高層專家,同時又注重對不同人才的培養訓練。在人才培養中,從實際出發,根據需要,分門別類,既著力于生產一線操作者的基礎教育,又著力于以半工半讀形式培育中層技術骨干,更不惜代價選送優秀技術人員出國深造,為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儲備人才。
提升職工的職業素質,文化教育是基礎。中國長期以來是農耕社會,近代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和部分城市貧民,他們處于社會底層,在舊中國經常處于食不果腹的悲慘境地,根本沒有條件進學校讀書接受教育。而近代大工業生產需要的是有文化、懂技術的操作者,這一矛盾在當時國家貧弱的社會環境下,只能由需求勞動力的工廠方面解決。
1921年3月,在富有遠見的范旭東倡議和多位廠領導與職員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人“夜讀班”(后改為“工讀班”),利用工余,每晚為工人授課。第一期報名者八十余人,按識字程度分甲、乙兩級,聘請廠內工程技術人員義務教授,成效良好。
為使工人教育制度化,1921年7月,在《久大精鹽工廠管理規則》中規定:“本廠為增進工人知能幸福起見,特聯合永利工廠共設工讀班,三年畢業,凡本廠工人有志求學者,均得報名入學。”同時又規定“本廠藝徒,均須入工讀班讀書,不得規避”,就是說對藝徒入讀是帶有強制性的,逃課甚至要加以懲罰(后已取消)。至于學習、書籍、文具等均不收取費用,完全是義務教育性質的。
1922年1月“工讀班”擴充為甲、乙、丙、丁4個學級,學生增至145人。至1925年更擴充到8個學級,學生達420人。于是補充教員,配備專業教師,增設學科、課時,逐步與正規的國民教育接軌。求知上進乃是人的本能之一,《海王》旬刊曾有報道:工讀班“雖在嚴寒中,學生竟鮮有缺課者,可見工友努力之精神及求知之殷切,殊堪欽佩”。
為進一步規范久大、永利兩廠職工教育,1927年12月,范旭東又親自函告兩廠稱:“教育事宜關系國家前途至鉅,現為塘沽本工廠謀教育發達起見,組織教育委員會,特派傅冰芝、沈舜卿、李燭塵、歐陽谷貽四君為委員,辦理明星小學校(子弟小學)及工讀班一切事務……”。這充分表明范旭東對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
1927年以后,久大、永利兩廠的職工教育進一步規范化。工讀班改用中華教育促進會編定的《市民千字課本》,該課本從市民已是成年人的心理特點出發,按照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公民經濟、公民衛生幾個部分編定。高級班則增加公民法制、公民道德、應用尺牘等新學科。已經成立的工廠教育委員會還根據工人的特點,添設科學常識課,并創辦演講會,培養工人的演說能力。
工讀班每年進行學期考核,對學習成績優秀的前三名工友頒發一定的獎金,以示鼓勵。
當年久大、永利兩廠地處偏僻,國家教育又不發達,當地沒有國辦學校,兩廠職工子弟的教育便成了問題。為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更是為社會分擔兒童教育的任務,1925年8月,創辦了職工子弟小學,以兩廠創辦人范旭東“旭東照明星”之意,定名為“明星小學校”。至1926年,全校6個年級已有學生一百九十多人。不久,呈報塘沽所屬河北省寧河縣教育局轉呈省教育廳立案,從而與國民小學教育接軌,納入了政府舉辦的小學教育體系,但在實際運作上還是依靠兩廠,具有久大、永利的特色。如學校根據“四大信條”制定了自己的教育目標,即:“(一)啟發民族的意識;(二)培養團體的意識;(三)鍛煉健康的身體;(四)養成勞動的習慣;(五)建立科學的基礎;(六)訓練前進的思想;(七)增進藝術的興趣;(八)發展創造的能力”。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學校停辦。永利公司西遷入川后,于1940年1月在四川省犍為縣重建了明星完全小學(久大入川后去了自貢)。
1932年,永利堿廠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舉辦了一個高層次的藝徒班(后稱工藝班),目的是以知識激發藝徒的才智,造就一批有頭腦、有經驗、有技術的工人和技術人員。通過考試,錄取了33名藝徒。據史料記載,考試的一些細節很有特色,如考試項目分“身體測驗”、“知識測驗”兩種,前者包括“舉重及身高”;后者包括“寫字、筆算及誦讀”。口試不但要“詳細的采詢”其“以往經歷和未來志愿”,更“注意他是否具有堅強不拔的決心”,十分嚴格。課程設置包括英文、算數、物理、機械工作法、制圖、常識(含簡淺的政治學、經濟學、工廠管理學、園藝學以及修身處事之道)等6門。教學以半工半讀形式進行,日間工作、實習,工余上課。課前用10分鐘講解時局形勢,灌輸愛國思想。其時,正是日寇侵華逐步擴張之際,藝徒班在一年后不得不停辦。至1934年8月,又重新舉辦“特種藝徒班”,從冀、魯、湘、浙等省選拔初中畢業以上學歷的二十余人,以及本廠考取的插班生5名共三十余人組成。仍采取半工半讀形式,白天分別到鐵工房、翻砂廠、模樣房、電工房工作實習,晚間上課,全天共11個小時學習訓練,為期三年。在此期間,還組織他們到唐山、北平、保定、青島、太原等地參觀、學習,增長見識。endprint
據曾在1934年入“藝徒班”學習、后移居海外的張榮善回憶,他是在不滿16歲時經考試被錄取的,實行半工半讀,學習期限為三年。這個班共有三十多人,每個藝徒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從雜工做起,再慢慢學習技術方面的工藝,晚間有3小時的課。有一年全班去山西太原參觀了十幾個工廠。他認為,“藝徒班”的學習效果“不比一般大專學校差”。學習期滿還沒有正式分配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幾經輾轉去了四川犍為縣永利川廠,被派到翻砂廠做技術員。1941年離開永利,考入內遷的武漢大學,畢業時正好日寇投降,張榮善進了永利南京硫酸铔廠。據他所知,當年“藝徒班”的許多人都成了重要部門的工程師,其中成績突出的優秀者成為總工程師的也不乏其人。
培育拔尖人才出國深造,也是“永、久、黃”團體注重人才培育的舉措之一。有史料顯示,僅在1938~1948年的10年里,永利派出留學(含考取公費留美的)、進修和工作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被范旭東視為“事業的神經中樞”,更是格外看重培養新生力量。據不完全統計,黃海社在經濟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派遣青年研究員往國外留學的也有10人。他們后來都成為“永、久、黃”團體的骨干中堅力量。
史料顯示,至1935年,“永、久、黃”團體興辦的教育單位就有8個,即明星小學校、永利藝徒班、懷瑛幼稚園、工讀班、外國文補習班、婦女補習班、聯舍兒童補習班、成人義務教育學校。企業辦學具有這樣的規模,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
十分遺憾的是,1945年日寇戰敗投降不久,積勞成疾的范旭東不幸因病辭世,其后“永、久、黃”團體的事業主要由李燭塵、侯德榜主持。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在一次視察永利時曾說:“永利是一個技術簍子”。可以理解,這其中包含了對“永、久、黃”團體開展職業教育的肯定。
“永、久、黃”團體經過公私合營、合并、調整,雖機構幾經變動,但它們對職工教育、培訓的傳統則薪火相傳,一直繼承延續了下來。
注釋:
①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1359頁
②《范旭東企業集團歷史資料匯編——久大精鹽公司專輯(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7、283-284、287、297-312、67頁
③《鉤沉——‘永久黃團體歷史珍貴資料選編》,天津堿廠2009年出版,第343、412、414、415-417、418-419、418頁
④《化工先導范旭東》,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31-134、138-139、153-154、146頁
(責任編輯:王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