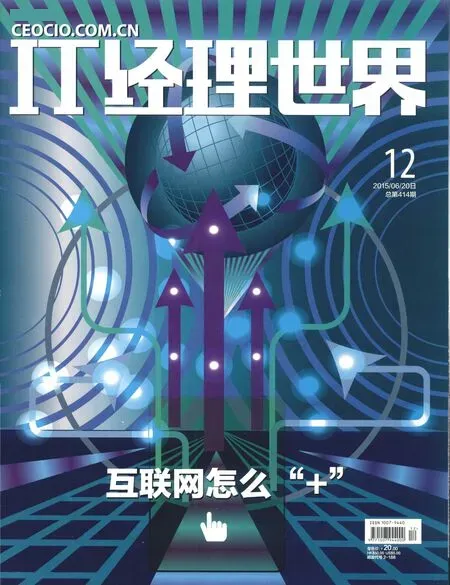繞過(guò)貨幣政策的“結(jié)構(gòu)性”難題
劉西曼
中國(guó)的諸多事情,都很擰巴。比如,大量低端制造業(yè)產(chǎn)能過(guò)剩,高端卻嚴(yán)重不足;比如,明明貨幣非常充裕,但是很多實(shí)體經(jīng)濟(jì)部門缺錢,但是,一放水呢,房?jī)r(jià)先漲,實(shí)體經(jīng)濟(jì)連湯也喝不到。
近期,中國(guó)的貨幣政策,也遇到了相似的“結(jié)構(gòu)性”擰巴問(wèn)題:一方面,中國(guó)現(xiàn)在貨幣面根本不緊張。根據(jù)本周央行發(fā)布的報(bào)告,預(yù)計(jì)全年M2的增速依然有13%,鑒于本年經(jīng)濟(jì)增速約7.5%,通脹不會(huì)超過(guò)2.5%,13%減去名義增長(zhǎng)率,Margin仍然有3%。這不是一個(gè)很低的數(shù)字,經(jīng)濟(jì)依然在加杠桿,總體仍然是負(fù)利率。但是,另一方面,無(wú)數(shù)人開始叫囂、期盼,降低存款準(zhǔn)備金、甚至降息——事實(shí)上,政府也進(jìn)行了“定向降準(zhǔn)”舉措,讓市場(chǎng)有些摸不到頭腦。
本月9日,央行宣布對(duì)符合審慎經(jīng)營(yíng)要求且“三農(nóng)”和小微企業(yè)貸款達(dá)到一定比例的商業(yè)銀行降準(zhǔn)0.5個(gè)百分點(diǎn),這是央行在兩個(gè)月內(nèi)第二次定向降準(zhǔn);同時(shí)下調(diào)財(cái)務(wù)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的存款準(zhǔn)備金率0.5個(gè)百分點(diǎn)。這是一種態(tài)度,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也可以微調(diào),但是,優(yōu)選的策略是結(jié)構(gòu)性微調(diào),不會(huì)和2008年“四萬(wàn)億”期間那種一刀切大放水。
但是,這種態(tài)度其實(shí)充滿了曖昧,也讓人疑惑。因?yàn)椋@次定向降準(zhǔn)涉及到的資金量,可能不超過(guò)800億元,這樣一個(gè)資金量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實(shí)質(zhì)幫助微乎其微,有“純粹表明態(tài)度”之嫌。同時(shí),針對(duì)小微企業(yè)的貸款總體利率并不會(huì)下降,小微企業(yè)的風(fēng)險(xiǎn)也不會(huì)降低,降準(zhǔn)真的有意義嗎?更不用說(shuō)“三農(nóng)”貸款了,其壞賬率極高,主要是因?yàn)檗r(nóng)村沒(méi)有太多具有競(jìng)爭(zhēng)力的產(chǎn)業(yè),降準(zhǔn)易,提升三農(nóng)產(chǎn)業(yè)能力難!
那么,這時(shí)候,更好的選擇是什么?財(cái)政政策優(yōu)于貨幣政策。
最近,政府在西部鐵路建設(shè)、棚戶區(qū)改造等領(lǐng)域,加大了財(cái)政和金融的支持,應(yīng)該說(shuō)是非常好的一種選擇。這些地方的最大特點(diǎn)是,確實(shí)存在需求,存在供給不足,財(cái)政政策的定向支持,只是提前了其建設(shè)進(jìn)程,不存在金融政策的“亂入效應(yīng)”。所謂“亂入效應(yīng)”指的是,一旦放松貨幣,貨幣會(huì)優(yōu)先流入那些具有投機(jī)性的資本品領(lǐng)域,比如大宗商品、住房,而不是國(guó)家期待的創(chuàng)新、結(jié)構(gòu)升級(jí)等領(lǐng)域。與之相比,財(cái)政政策的可控性要好得多。
既然如此,針對(duì)小微企業(yè)、針對(duì)三農(nóng)問(wèn)題,優(yōu)先序列也應(yīng)該說(shuō)財(cái)政稅收政策。比如,進(jìn)一步降低小微企業(yè)的稅收,由國(guó)家財(cái)政支持改善農(nóng)村土壤、修建水利設(shè)施等。這些政策的價(jià)值會(huì)在較為長(zhǎng)期的周期兌現(xiàn),是企業(yè)們很難、也不愿意去做的,政府的角色名正言順。
與貨幣政策、財(cái)政政策相比,政府的其實(shí)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甚至比“微刺激”的力度更大,但是連帶的副作用更小。
第一,產(chǎn)業(yè)并購(gòu)基金及其政策。在眾多的產(chǎn)能過(guò)剩領(lǐng)域,僵而不死的企業(yè)很多,為什么?地方政府的利益糾葛是第一大問(wèn)題。很多地方企業(yè),明明生產(chǎn)力落后、污染嚴(yán)重,但是領(lǐng)先企業(yè)很難對(duì)其進(jìn)行并購(gòu)改造。多年前,寶鋼參股邯鋼,最后不得不退出,與河北省的地方利益關(guān)系甚大,但是,由唐鋼、邯鋼等合并到一起的河北鋼鐵,幾無(wú)競(jìng)爭(zhēng)力,連續(xù)虧損。這時(shí)候,需要政策方面有更好的引導(dǎo),由中央主導(dǎo)的產(chǎn)業(yè)基金牽頭,加快并購(gòu)整合進(jìn)程。最近,中民投的成立,有不少的探路性質(zhì),反倒國(guó)有的基金運(yùn)作太慢。其實(shí),此前的成功案例并不少,如中國(guó)建材、海螺水泥牽頭整合中國(guó)水泥產(chǎn)業(yè)。
第二,加大長(zhǎng)期基礎(chǔ)產(chǎn)業(yè)投資。讓市場(chǎng)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的內(nèi)涵到底是什么?市場(chǎng)失效的地方,怎么辦?這時(shí)候政府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應(yīng)該更大。一些長(zhǎng)線項(xiàng)目的投資,沒(méi)有一家會(huì)為未來(lái)10年的收益提前埋單,恰恰需要加大基礎(chǔ)性投入。比如,一條芯片生產(chǎn)線,哪怕是28nm的,其成本都上升到百億美元級(jí),這種投資必須政府參與、企業(yè)牽頭,共同努力。像中國(guó)芯國(guó)際這樣的企業(yè),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實(shí)現(xiàn);幾年前,京東方、華星光電也面臨類似的問(wèn)題,但是,通過(guò)政策扶植、股市融資等手段,它們已經(jīng)從丑小鴨變成了準(zhǔn)天鵝。
第三,進(jìn)一步投資人力資本。中國(guó)是一個(gè)人均自然資源高度稀缺的國(guó)家,也是一個(gè)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追趕者,這時(shí)候,除了挖掘人的潛力,沒(méi)有任何別的辦法可以幫助中國(guó)的發(fā)展提速。而在人力資源培育上,中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lái)都依靠中國(guó)的家庭投入,雖然中國(guó)家庭高度重視教育,彌補(bǔ)了財(cái)政的不足,但是,一旦到了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必須由政府加大投資。在經(jīng)濟(jì)逆周期時(shí),政府加大投資人力資源,可以說(shuō)是最有價(jià)值的選擇。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把解決問(wèn)題的著眼點(diǎn)放在貨幣政策上,結(jié)構(gòu)性問(wèn)題根本難以舒解,為了刺激經(jīng)濟(jì)、又不帶來(lái)副作用,甚至是長(zhǎng)期的紅利,應(yīng)該有更大的視角;不應(yīng)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