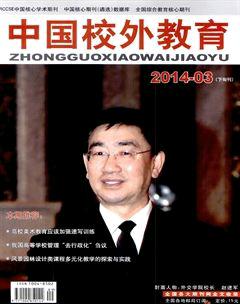《問題的核心》中“他者”話語解讀
佘丹
從后殖民主義的理論視角解讀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問題的核心》,特別是對文本的殖民話語的分析,可以看到格林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作品中時,是以西方人的目光來注視殖民地的。因此,《問題的核心》中的“他者”是作者潛意識中西方中心主義作用下的主觀性產物。
《問題的核心》殖民話語他者作為享有國際聲譽并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和各種重要文學獎項的作家,英國文壇泰斗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被評論界公認為現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英語文學作家之一。他一生創作成果豐碩,包括十七部小說,九部“消遣文學”作品,五部短篇小說集,七個劇作,九個電影劇本,兩本游記,三本自傳和一本詩集,廣泛的記載了他對宗教、人性、社會政治和人的生存問題的思維和探索。他的作品暢銷全世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贊譽。威廉?高登盛贊他為“二十世紀人類自我意識與內心焦慮最卓越的記錄者”。格林一直致力于探討社會道德問題,因此他的小說具有濃重的人文主義傾向和現實主義情結,同時他對20世紀人類的前途與命運的關注也體現了一位現實主義作家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的確,《問題的核心》是對人類社會中人的精神困境和社會道德問題的反思。同時,筆者覺得小說《問題的核心》也是一部對了解格林的殖民地敘事很有幫助的文本。
后殖民的理論家們將殖民地的人們稱之為“殖民地的他者”。顧名思義,西方的殖民者則被稱為自我。“他者”這一概念,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薩特的定義,是指“主導性主體以外的一個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為他的存在,主體的權威才得以肯定”。自我意識只有通過對自己的對方或差異者設定為“非存在”——即“他者”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西方之所以自視優越,正是因為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沒有力量、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思考和統治的能力的結果。”著名的后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在他的代表作《東方主義》也指出,西方關于東方的知識話語充滿了作為“他者”的東方的想象。著名學者王寧還對賽義德的“他者”概念作了闡釋:“按照后殖民主義的觀點,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其文學的價值與傳統,甚至包括各種后現代主義的形式,都貫穿著一種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總是被認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導地位。與之相對照的是,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東方的傳統被排擠到了邊緣地帶,或不時地扮演一種相對于西方的‘他者的角色。”另一學者崔少元也認為,賽義德的“東方學”理論從‘話語—權利的角度分析了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文化二元對立關系。賽氏認為在這種對立的權利話語模式中,宗主國處于中心地位,而殖民地國家則處于邊緣的位置。邊緣國往往僅僅作為宗主國神話的陪襯,被置于從屬的境地。”的確,很多西方文學文本呈現出來的非西方的第三世界,都表現為西方人為了確認“自我”而構建起來的“他者”。西方人總是被塑造成積極的自我形象,西方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沒有生氣、被物化”的“他者”形象出現,在“他者”形象的陪襯下,西方“自我”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顯。本文通過對小說《問題的核心》中“他者”話語的解讀,可以看出作者格林在“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也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優越感。
格林1904年出生在英國中部波肯斯特的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查爾斯?亨利?格林是當地中學的校長。他的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從昔日帝國分享到的利益和特權,都使他難以徹底超越殖民視角。正如著名學者張中載所言,“生活在長期進行殖民主義擴張的英國的反殖民主義斗士同樣難以不受殖民主義思想、白人優秀論和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歐洲中心的思想在他們身上早已根深蒂固。”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也指出:“我發現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之一就是,我素常敬仰的許多英法藝術家也認可‘隸屬或‘劣等民族這類被那些統治印度和阿爾及利亞的官員認為是理所當然并努力把它們付諸實踐的觀念。”由于無法擺脫長期積淀下形成的集體意識,格林對于英國殖民地及其人民的描寫仍難擺脫殖民主義話語。他在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創作視野時,正如賽義德所言,“是以一個西方人的目光注視殖民地的”。在這樣的情形下,殖民地及其人民是作為西方宗主國相對的“他者”而存在。因此,對《問題的核心》中“他者”話語解構表明:“他者”的確立是對殖民地文化文本化的過程。維多利亞時代西方意識中的“他者”是歐洲中心論和種族優越感雙重作用下的產物。
一、殖民自我的復制
西方的自我包含有理性、文明、高級等內涵。西方殖民者沉醉在這一有力量的能動的自我之中,反復向自己再現關于自我的信念。這種力量在不斷地自我復制中逐漸強化,建構中的自我因此演化成了實體性的存在。
這種自我的復制過程在《問題的核心》明顯的表現出來。主人公斯考比就通過泛濫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把自我復制為像上帝一樣的救世主。作為英屬西非殖民地上的一名警官,斯考比已經在此任職15年。殖民地環境的骯臟和腐敗,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身體和心靈上的創傷,讓斯考比憐憫世間所有的苦難,總想要去承擔起幫別人解除痛苦,獲得幸福的責任。他甚至不能理解上帝為什么會眼睜睜看著人類受痛苦,因此他決定令自我取代上帝的位置,去拯救萬物的痛苦,以人類的憐憫去代替上帝演繹神的仁慈。盡管與妻子之間早已沒有了愛的愉悅和甜蜜,但他仍然對妻子懷有無限的同情和憐憫。他把妻子的日漸衰老、多愁善感、人緣不佳和精神苦悶都歸咎于自己的責任。他認為自己既沒能給妻子創造好的生活環境,也沒有以事業上職位的高升給她帶來社交生活的自信。所以為了送精神苦悶的妻子去度假,盡管無力籌措巨額費用,但他仍然在對妻子的憐憫和責任感驅使下假裝強大,鋌而走險向走私販借債,結果落入對方的圈套。妻子走后,他同情并愛上了因所乘船只被敵方潛水艇擊沉而流落該地的年輕寡婦海倫,并且在私情被妻子發現后,仍舊無法舍棄對海倫的責任。海倫在斯考比的眼中是流落到該地孤獨無助的弱者,一想到她從海上死里逃生遭受的痛苦,上岸后流落異地的無助,被壞男人調戲的危險以及充滿風險的未來,斯考比就感到對她的生存負有無法舍棄的責任。在他眼中,照顧海倫是“承擔起了上帝沒有承擔的責任”。他的這種少見的過度的憐憫和責任感被有些評論稱為“自負”的責任感。作為一個警官,憐憫本是與履行公務不相容的性格。但憐憫之所以成為斯考比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應該與他的工作環境有關。正如著名學者韓加明先生所指出,15年的警官生涯一定使斯考比看到無數不公正、不合法的事,接觸到無數在正當與不正當的法律面前無能為力的人,正是這些經歷使他的性格中憐憫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一切弱小無援、或陷于困境的人。但同時斯考比的憐憫也是其“傲慢”的表現,因為他作為殖民地高級官員,處在居高臨下的地位,憐憫他人是表現這種地位的手段,而這種地位只有大權在握的殖民者才能享有。
二、斯考比與仆人阿里的友誼的不可能性
斯考比的仆人阿里是當地非洲人的代表。他正直誠實、心地善良,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地服侍了斯考比15年。在斯考比度假期間,很多人都想把他搶走,但每次回來阿里都在碼頭上等著他。當斯考比的手被門上的木刺劃破的時候,阿里細致地為他清洗和包扎傷口,他的手像女孩子一樣輕巧,動作像醫生一樣熟練。當斯考比去班巴出差途中害了黑水病而發高燒時,阿里一直站在他身旁照顧他,為他支好吊床和蚊帳,手里端著熱茶和餅干,隨時送到他嘴邊,還一直滿臉堆笑的點頭,回答他的話。他給了斯考比“所需要的全部愛情和友誼”。
endprint
但對于這樣十五年忠誠盡職的仆人,斯考比也從未把他看作是自己生命中可信賴的伙伴,而僅僅是可以操控利用的,為自己提供服務的被物化了的對象而已。當阿里無意間發現了斯考比的私情和與商人尤塞夫的私下交易時,斯考比沒有首先跟阿里交流溝通,來消除彼此心中的顧慮,而是直接選擇對他的不信任,把他視為對自己的威脅(盡管阿里從未有過不可信任的表現),轉而向尤塞夫求助。結果阿里在沒有任何辯解的機會下,被尤塞夫指派的人殘忍的殺害了。
阿里的悲慘結局印證了作家魯德亞德?吉卜林說過,“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遠不會交匯。”殖民者永遠不可能把被殖民者當作朋友來看待。友誼是建立在不涉及物質利益的平等基礎之上的,是心與心的交流。而殖民者只把被殖民者看作臣屬于自己的“他者”。因此,被殖民者是不可能成為白人的朋友的。“‘他者的存在是為了證明‘我們的優越性,證明西方所走的科技理性道路的正確性……嚴格說來,他者是拯救的對象,是幫助的對象也是掠奪的對象。”
除此之外,小說中對阿里的形象描述也體現出典型的“他者”范式。阿里遠不是一個復雜的、具有自主性的人物。作為主人公斯考比生活中最親近的伙伴,作者卻沒有對他進行太多的、深層次的刻畫。對他的外表簡單描述為“身材矮壯,生著一張丑陋卻討人喜歡的扁闊的面孔”。盡管小說中阿里發出了聲音,與殖民地小說中高度模式化的黑人形象有所不同,但是他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圓形人物”,擺脫不了象征的使命。他在小說中幾乎沒有情感變化和內心需求的表達,讀者對于阿里的心理也一無所知。在小說中他只是一個被物化的人物,一個威脅著殖民者命運的“他者”。
三、“停滯、落后”的東方和“無知、野蠻”的“他者”
殖民話語的邏輯基礎是白人殖民者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感。從某種程度上,由于種族文化身份的羈絆,格林無法超越殖民話語的制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之形成某種共謀關系。在傳統殖民主義的話語中,作家往往通過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的塑造來實現對殖民“他者”的塑造。非西方地區總是作為為“野蠻、落后、專制、腐敗”的“他者”形象出現。在《問題的核心》中,故事的發生地——英屬某西非殖民地就是這樣一塊骯臟、破落、腐敗的大陸。這里的氣候潮濕燠熱,低沉的云,漂浮的霧,“密不透風的雨簾”。皮膚所觸之處汗珠就會流淌出來。皮膚上的傷口在一個小時之內不處理就會腐爛發綠。櫥柜需要終日開著電燈,靴子很快就發了霉。住宅前的空地在旱季里是沼澤,在雨季里是汪洋。禿鷲像火雞似的在團堆的垃圾堆上悠閑踱步。到處糜集著老鼠、蟑螂、蒼蠅、蚊子和野狗。醫院里滿是瘧疾和黑水熱的病人。黑水熱會讓人高燒、精力枯竭,甚至送命。這樣骯臟,破敗的環境讓很多在此工作的英國官員脾氣暴躁,情緒糟糕,身體因不適而生病。他們把這塊殖民地稱作“荒蠻、遙遠的叢林”,甚至是“白人的墳墓”。
而塑造殖民地當地人的“他者”形象來映襯西方的白人統治者,是格林殖民話語的另一敘述手段。在小說中,白人始終占據文本敘事的中心,白人世界和白人形象都被塑造得富于飽滿的現實感,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被“單質化”的當地黑人形象。格林較多地使用褒義詞來刻畫白人形象,如身軀挺拔的區專員;較多地用贊賞的語氣評價白人,如遭遇了海難仍然要對船主負責的有擔當的蘇格蘭輪機長;很少對白人進行批判,就算批判也表現出明顯的包容,比如身為英國政府的派來的間諜,年輕官員威爾遜仍然被描述為“毫無防范能力”,像孩子一樣弱小,不具備“成人臉上的線條”。而在對黑人的描寫上,格林則使用了符號化的語言。落后、愚昧、不文明是非洲黑人的代名詞,在小說中,當地的小孩子們在碼頭性高采烈地領著水手去警察局附近的妓院。當地的一些十六七歲的青年,被稱作“碼頭耗子”,用刮臉刀和玻璃瓶碎片作武器,成群結隊地在貨棧周圍游蕩,一發現容易撬開的木箱,就把東西偷得一干二凈;看見喝醉酒的水手腳步踉蹌的走過來,他們就像一群蒼蠅似地蜂擁而上。而當地的商人,則多是鉆石走私販和高利貸主。為了壟斷當地的生意,他們相互攻擊,并敲詐勒索阻礙他們的人。其他成年人,主要的形象就是兩種:女的做娼妓,男的做仆人。斯考比的貼身仆人阿里,應該是小說里主人公生活中最親近的人物,也應是用墨較多的豐富而飽滿的形象。然而,在格林筆下,這樣一個關鍵性人物卻游走于書寫的邊緣,沒有實在的內涵而被“他者”化。阿里對斯考比忠誠盡責地服侍了15年,從未有過任何不可信任的表現,但卻因為無意中知悉了主人的私情和與中間商的勾結而成了對主人的威脅,從而被殺害。小說中僅僅對阿里最后的被害結果作了一些描述,而阿里作為一個被懷疑被傷害的黑人應有的心理活動完全沒有出現,這也印證了流行于殖民地的白人對黑人的普遍意義上的看法:黑人是低劣的人種,他們缺乏復雜的心理活動和情感需求,只配受到白人的奴役充當機器。而當地黑人女性甚至比男性更低等,她們承受著殖民主義、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三重壓迫,被符號化為“他者”中的“他者”。威爾遜去妓院時的遇到的性伴侶,“穿著骯臟的汗衫躺在包裝箱上,活像扔在柜臺上的一條死魚”,“身上散發出發霉的味道”“正躺在那里等待主顧”。她與威爾遜的對話中唯一的一句就是“要基格基格嗎,親愛的?十先令。”可見當地的女孩多么的廉價和卑賤。而與敘利亞商人尤塞夫有情愛關系的婦女們,在尤塞夫眼中的形象就是“我高興跟誰睡就跟誰睡,不跟我睡就滾開”,結果她們還“總是跟你睡”。人類學者維克多?特納指出:“邊緣‘他者的身份,可能表現為一無所有……只穿很少的衣服甚至裸體,已表明他們沒有地位、財產、標志……好像是正在被貶低成統一的模式……以使他們能夠應付生活中的新低位。”
四、結語
綜上所述,格林作為一名生活在大英殖民擴張的黃金時期的小說家,他的思想難免不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難免不帶有明顯的“文化優越感”。因此,他的小說《問題的核心》也就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傳統的英國殖民意識,出現了典型的殖民話語的書寫。小說中對非西方“他者”的邊緣化,使小說多少留下了“殖民性”的印記。
參考文獻:
[1]Graham Greene.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M] .New York:Penguin Books(U.S.A.),2004.
[2]愛德華?W?賽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東方學 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3]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M].盛寧,韓敏中 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4]張中載.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小說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5]韓加明.漫談格林的小說《問題的核心》[J].外國文學,1996.
[6]王寧.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批判——愛德華?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剖析[J].大學學報,1995.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