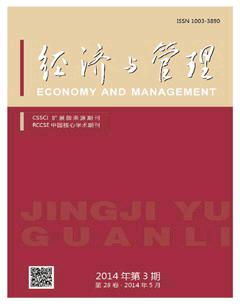中國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決策的個(gè)案訪談分析
摘要:文章通過實(shí)地訪談,深入分析了家庭遷居的決策過程、家庭不同遷居行為的依據(jù),以及家庭成員在決策過程中的互動關(guān)系。結(jié)果表明,家庭的遷居決策是在整體資源配置下實(shí)現(xiàn)的,遷居的地點(diǎn)一般由家庭在流入地的經(jīng)濟(jì)因素、發(fā)展因素與社會資本因素共同決定,不同批次遷移的家庭成員進(jìn)行遷居的時(shí)間間隔多以經(jīng)濟(jì)條件為標(biāo)準(zhǔn)。最終,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家庭會做出在城市定居或者返鄉(xiāng)的遷居決定。最后,本文將家庭遷居決策過程總結(jié)為“五階段”,即商議期、配置期、決策期、跟隨遷居期、遷居結(jié)果期。
關(guān)鍵詞: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家庭決策;遷居行為
中圖分類號:C92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4-0065-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7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ased on the Deep Interview
SHENG Yin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 analysis the basis of different migration behaviors, and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of family members during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interview.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realized by allocation the human resources in the family. The immigrant area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apital factors of the family. Time lags between the foregoers and the other family members are determined by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tage of the familys lifecycle and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will affect the familys migration decision.It is concluded as five phase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negotiation, allocation, decisionmaking, following migration and decision results phase.
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migration, family decisionmaking, migration behavior
我國舉家外出農(nóng)民工的規(guī)模正在逐年遞增,2012年已經(jīng)達(dá)到3375萬人[1]。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的規(guī)模不斷增加,開始引發(fā)研究者的討論與關(guān)注。對我國鄉(xiāng)-城人口流遷過程中家庭化遷居的研究與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家庭化遷居的研究框架超越了個(gè)人的范疇,以家庭這一基本的人類組織和社會單位作為研究對象。以往對流動者個(gè)人流動或遷移的研究多側(cè)重于個(gè)體的行為和特征;但是家庭化遷居的研究基礎(chǔ)更為復(fù)雜,家庭的成員關(guān)系、家庭結(jié)構(gòu)、家庭稟賦等層面都可能對家庭的遷居決策產(chǎn)生影響。本文的目的是研究鄉(xiāng)-城人口流遷過程中的家庭遷居決策行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拓展以家庭為主體的最優(yōu)化決策的研究,也可以對人口遷移理論進(jìn)行拓展與延伸。
已有對家庭遷移決策的研究多從靜態(tài)視角,探討在人口流動行為發(fā)生之前家庭成員間的協(xié)商機(jī)制。從決策主體而言,家庭的主要決策者一般是父母或者男性戶主[2~3],丈夫與妻子會衡量整個(gè)家庭在遷移后的經(jīng)濟(jì)收益和損失,當(dāng)丈夫在遷移后收入的提高能夠彌補(bǔ)家庭的損失時(shí)就會決定家庭遷移[4~5]。王春超等認(rèn)為中國農(nóng)村家庭戶的經(jīng)濟(jì)決策模式是“男女共商”型[6]。譚深認(rèn)為單一的家庭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并不能解釋家庭遷移的決策與動機(jī)的復(fù)雜性,家庭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成員間的互動在家庭策略的形成過程中更為重要[7]。孫朝陽對家庭策略下勞動力遷移的性別選擇進(jìn)行分析,認(rèn)為家庭對成員流動的決策是按照性別勞動分工而進(jìn)行的安排[8]。除了對家庭遷移決策中成員協(xié)商機(jī)制的研究,還有學(xué)者建立起家庭遷移決策模型來分析家庭遷移的決策行為。蔡昉較早地建立了家庭遷移決策經(jīng)濟(jì)學(xué)模型,對農(nóng)戶的遷移決策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9]。馬瑞等建立了農(nóng)村勞動力職業(yè)流動和家屬隨遷的決策模型,其基本假設(shè)認(rèn)為,農(nóng)村勞動力的決策是依據(jù)一定風(fēng)險(xiǎn)水平下對預(yù)期收益與成本的比較[10]。
總的來看,現(xiàn)有研究多為靜態(tài)研究,集中于對流遷行為的某一個(gè)特定時(shí)段的決策研究,例如先行人向外流動的決策,或者配偶、子女跟隨流動的決策,缺乏對家庭遷居行為全過程的動態(tài)研究。此外,現(xiàn)有研究多將家庭的特征作為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之一,而不是作為流動或遷移決策的主體。本文將在家庭遷居理性程度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分析不同理性程度下的家庭決策行為和家庭作為遷移主體在遷居決策鏈條中的作用機(jī)制,利用實(shí)地訪談資料對家庭遷居全過程中的決策行為進(jìn)行分析,包括家庭協(xié)商模式、先行者的選擇、遷居方式、家庭遷居地點(diǎn)、遷居時(shí)滯的權(quán)衡和對最終遷居結(jié)果的抉擇等,力求對現(xiàn)有研究進(jìn)一步拓展。
一、 家庭遷居的理性程度假設(shè)
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中以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作為理論基礎(chǔ)。隨著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的不斷拓展,理性人假設(shè)開始受到置疑,尤其是來自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與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對有限理性的研究。有限理性指出,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使個(gè)人無法獲得完全信息,而人的計(jì)算和認(rèn)識能力又是有限的,不能無所不知。然而,理性與非理性并非絕對對立的兩個(gè)方面。西蒙整合了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心理學(xué)領(lǐng)域?qū)硇匝芯康臉O端傾向,將理性的程度劃分為直覺理性、行為理性與完全理性;在心理學(xué)領(lǐng)域,哈耶克也將經(jīng)濟(jì)人決策的理性程度劃分為理性不及、理性無知、理性非理性等。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派也不反對對理性程度進(jìn)行分類[11]。我國學(xué)者何大安將行為人的理性狀態(tài)劃分為高、中、低三種程度,并將時(shí)間作為理性實(shí)現(xiàn)程度的重要因素[12]。本文建立家庭遷居的理性程度假設(shè),將家庭作為遷居決策的行為主體,并將遷居決策的理性程度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
一是理想理性程度,即無限接近完全理性的理性程度。在完全理性階段,家庭能夠最大化地發(fā)揮認(rèn)知能力,充分地搜集信息,環(huán)境中的不確定信息幾乎為零,這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情況有所差別。家庭可以精確地計(jì)算遷移系統(tǒng)為家庭帶來的收益和成本。
二是實(shí)際理性程度。家庭受到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不確定信息和因素的干擾,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盡量地搜集可能獲得的信息,盡可能地發(fā)揮可能達(dá)到的認(rèn)知能力,按照滿意原則做出遷居決策。家庭在遷居過程中除了受經(jīng)濟(jì)因素的影響之外,還可能受到許多非經(jīng)濟(jì)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制度與文化因素、家庭的社會資本與農(nóng)村社區(qū)狀況,以及家庭的人力資本和個(gè)體發(fā)展等因素。這種理性程度是最貼近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真實(shí)情況的。
三是直覺理性程度。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家庭難以對外界環(huán)境進(jìn)行有效的判斷,很容易受到干擾,使認(rèn)知和判斷產(chǎn)生偏差。在人口流動的初期,由于農(nóng)村人口獲得遷移信息的途徑比較閉塞,一般依靠農(nóng)村社區(qū)中其他流動人口的示范效應(yīng)實(shí)現(xiàn)。家庭遷居決策多屬于直覺理性,使人口流動表現(xiàn)出極大的盲目性和趕潮流式的集中性。隨著人口流動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政府對人口流動的有序管理降低了流動的盲目性和無序性,而農(nóng)村家庭對流動的認(rèn)識也更加深入,減少了家庭決策的直覺理性程度。
本文將家庭作為決策主體,在家庭實(shí)際理性程度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分析家庭化遷居的決策過程和行為方式。這里,家庭遷居的決策機(jī)制是指農(nóng)村家庭戶作為主體,對人口流動與遷居過程中所需的信息進(jìn)行搜集、分析和判斷,對內(nèi)部資源進(jìn)行配置,并隨家庭的發(fā)展或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調(diào)整決策的機(jī)制。
本文按照家庭化遷居的過程,將家庭遷居決策劃分為遷居起始決策、遷居過程決策和遷居結(jié)果決策(見圖1)。在第一階段,即家庭化遷居的起始期,家庭會做出個(gè)人或部分人外出流動的決定,其前提是個(gè)人的流動行為對家庭整體利益有所提升,或者至少不會降低整個(gè)家庭的福利。那么,家庭對福利上升的判斷將成為遷居決策的主要?jiǎng)右颉T诩彝セw居的過程階段,家庭可能對先行者、遷居地點(diǎn)等進(jìn)行選擇,并通過階段性流動的方式逐步將其他成員帶到城市中,也有可能舉家遷居到城市中。從第三階段,最終的遷居結(jié)果來看,家庭可能選擇長期居住,甚至在城市中定居成為城市家庭,但也可能最終決定返回原居住地。
在家庭的實(shí)際理性程度下,家庭會在衡量遷移的成本和收益之外,綜合考慮影響家庭遷居的各種因素,其中可能包含傳統(tǒng)文化因素、社會學(xué)因素、制度背景因素等。為了準(zhǔn)確地展現(xiàn)家庭遷居的決策過程和作用機(jī)制,筆者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結(jié)合了部分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進(jìn)行說明。本文在河北省保定市展開了深度訪談,并應(yīng)用了中國人民大學(xué)2012年“北京市非正規(guī)就業(yè)人口調(diào)查”的部分訪談資料,調(diào)查對象均為在城市中居住三個(gè)月以上的流動人口。研究數(shù)據(jù)應(yīng)用了原國家人口和計(jì)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監(jiān)測數(shù)據(jù)2010年下B卷,調(diào)查地區(qū)為北京、鄭州、成都、蘇州、中山、韓城6個(gè)城市,總樣本量為8200人。
二、 家庭遷居起始階段的決策
1. “協(xié)商共議”是家庭化遷居的主要決策模式
康奈爾(Connell)等認(rèn)為家庭遷移決策有兩種決策方式,即戶主做出遷移決策,家庭中的遷移者接受戶主的決定;或者所有家庭成員達(dá)成共識[13]。中國傳統(tǒng)家庭權(quán)力的中心以父權(quán)制為主要制度形式,父系、父權(quán)、從夫居制構(gòu)成了父權(quán)制家庭的規(guī)則體系。遷移方式以一家之主的意見為絕對地位,其他家庭成員自上而下共同行動,執(zhí)行遷移行為。可見,中國歷史上的家庭遷移一般以康柰爾研究中的前者為主要決策形式。
家庭現(xiàn)代化理論認(rèn)為,家庭現(xiàn)代化進(jìn)程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家庭轉(zhuǎn)為核心家庭,個(gè)人的價(jià)值高于家庭,更加傾向于性別平等,壓制傳統(tǒng)和習(xí)俗等[14]。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家庭的權(quán)力中心發(fā)生轉(zhuǎn)變,父權(quán)在家庭中的絕對地位受到削弱[15]。家庭商議模式由“唯父命是從”向“協(xié)商共議”的決策方式轉(zhuǎn)變:一方面,女性通過流動行為提高了經(jīng)濟(jì)收入,在家庭的經(jīng)濟(jì)活動中占據(jù)更為重要的地位,妻子與丈夫“議價(jià)”的能力不斷增強(qiáng)。另一方面,人口的流遷行為促進(jìn)了家庭現(xiàn)代化變遷,帶來了性別間的重新協(xié)商。絕大多數(shù)的被訪者表示,家庭在面臨流動等對家庭會產(chǎn)生重大影響作用的事件時(shí)比較民主,家庭成員之間會互相商議。如果流動者堅(jiān)持向外流動,其他家庭成員不會特別反對。即使其他家人最初有反對意見,但是通過相互商議、妥協(xié),能夠最終達(dá)成共識。家庭一般會重新配置家庭內(nèi)的勞動力資源,進(jìn)行有序分工,以確保外出務(wù)工的家庭成員沒有后顧之憂。例如:
C03(女,28歲):我老公先決定要出來打工(家庭遷居的先行者),當(dāng)時(shí)我們家里面都是反對的。因?yàn)榧依锩婀ぷ鞫纪Ψ€(wěn)定的,收入也還可以。但是他說想出來闖一闖、看一看,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在這邊打工。現(xiàn)在家里都支持我們出來打工。(問:為什么現(xiàn)在他們支持了?)因?yàn)樵谕饷媸杖脒€可以,家里面公公婆婆現(xiàn)在還年輕,他們也還照顧的過來。家里的土地都被承包了,每年收一些租金(家庭進(jìn)行協(xié)商,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
2. 對家庭的整體收益與個(gè)人的追求進(jìn)行權(quán)衡
家庭做出遷居決策的最重要的動因是獲取更高的經(jīng)濟(jì)收入。家庭在衡量流動的收益與成本時(shí)會考慮不同的因素,使遷居行為可能表現(xiàn)為三種基本類型。
一是追求經(jīng)濟(jì)收入或預(yù)期經(jīng)濟(jì)收入的滿意,例如C02(男,25歲):“老家的收入太低了,每個(gè)人分得的土地只有幾分,根本不夠生活。我們那基本都靠出來打工賺錢。”
二是追求成本與收益的滿意,如C01(男,43歲):“我已經(jīng)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了,現(xiàn)在在N大食堂里面工作。這邊的收入雖說不算高,但也還可以,總是比在老家的收入要高,不好也不會過來。跟這邊相比,我們老家的消費(fèi)水平更高。在這邊工作容易攢錢。”
三是追求門檻的最低化(最滿意),如C03(女,28歲):“我們兩個(gè)人在老家的收入也不錯(cuò)……但是老家的消費(fèi)和收入都比在這邊高,在家主要是花的比較多,朋友也比較多,用(錢)的(方面)比較多。我們兩個(gè)人在這邊,相比之下更容易攢錢。”
年輕的流動人口更加注重個(gè)人發(fā)展因素。不少年齡在35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在決定向外流動時(shí),會聽取家人的意見,但更加顧及個(gè)人的追求。他們認(rèn)為,年輕時(shí)期外出闖蕩、打拼,了解家鄉(xiāng)外面的世界十分重要。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他們重視自身的未來發(fā)展,有意愿融入城鎮(zhèn)成為市民。同時(shí),對土地的依賴性較低,很多人從未從事過務(wù)農(nóng),也不想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例如:
C08(女,26歲):我以前在N大上學(xué),學(xué)的是物流專業(yè)。畢業(yè)之后,經(jīng)過朋友介紹在這里工作。我以前在家就不干農(nóng)活,所以也不想回家種地。
3. 對閑暇與收入進(jìn)行比較,達(dá)到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
在家庭生產(chǎn)理論中,家庭將時(shí)間分為兩個(gè)部分,一部分時(shí)間用于在市場中工作獲得經(jīng)濟(jì)收入,另一部分時(shí)間用于閑暇,即個(gè)人用于在市場工作和家庭工作之外的時(shí)間。家庭將有限的時(shí)間在閑暇與收入之間進(jìn)行分配,使兩者之間呈現(xiàn)替代效應(yīng)。類似地,農(nóng)村家庭會對遷居后的閑暇與收入進(jìn)行比較,進(jìn)而影響到遷居決策。在家庭整體收入尚未達(dá)到某一水平時(shí),家庭成員會為了獲得更多的經(jīng)濟(jì)收入而選擇外出(或不外出)流動,放棄閑暇。如C01(男,43歲):“像我們在老家里干活時(shí),都沒什么事可做,比較輕松。在這邊工作,每天要起早貪黑的,還是比較累。”
反之,當(dāng)經(jīng)濟(jì)收入達(dá)到某一水平后,收入對家庭整體效用的提高作用開始遞減,相反,閑暇的增加能夠使家庭的效用得到顯著地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流動人口會更傾向于選擇閑暇,而非經(jīng)濟(jì)收入。如C10(男,32歲):“在老家的收入更高。如果包二十畝地,一畝地就能掙千八百的,就是太累。在這(城里),一個(gè)月才能掙一千多塊錢,買房也買不起。但是在城里打工輕松多了,在老家種地比較累。所以我現(xiàn)在還是會留下來打工。”
三、 家庭化遷居過程中的決策
1. 家庭資源配置下的先行者流動
先行者一般是家庭中的壯年勞動力。他們是獲得經(jīng)濟(jì)收入的中堅(jiān)力量,肩負(fù)著通過外出流動來增加家庭整體福利的責(zé)任。一旦先行者決定外出流動,整個(gè)家庭就會進(jìn)行資源的分配與整合,例如,長輩幫助照看孩子,兄弟姐妹幫助代為耕種土地、看管房產(chǎn)等。這些安排可以保證家庭生活在成員流出后不會受到影響,使家庭平穩(wěn)度過成員的外出流動階段。
C06(女,34歲):家里最先是我丈夫決定出來打工,正好有朋友在N大食堂工作,他介紹我們過來工作。后來我和我老公同時(shí)出來打工,現(xiàn)在在城里做餐飲。我們現(xiàn)在還年輕,想出來見識見識,這邊的收入更高。現(xiàn)在家中還有孩子和公公婆婆……公婆照顧孩子,家里的房子、土地讓弟弟照看,種地的收入也歸他。
2. 遷居地點(diǎn):經(jīng)濟(jì)因素、發(fā)展因素與社會資本因素
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流動人口對遷居地點(diǎn)進(jìn)行選擇時(shí),首先考慮經(jīng)濟(jì)因素:如工作機(jī)會、經(jīng)濟(jì)收入,分別列選擇流入地原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次是發(fā)展因素:學(xué)習(xí)技能、增加眼界、孩子的教育,分列原因的第三、第五和第七位。最后是社會資本因素:親朋好友、家人在流入地等,也會吸引流動人口后續(xù)流動(見表1)。這說明,經(jīng)濟(jì)因素和發(fā)展因素是家庭在實(shí)際理性程度的過程中首要考慮的因素。
社會資本對家庭選擇遷居地點(diǎn)的影響較為復(fù)雜。費(fèi)孝通曾提到,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的親屬關(guān)系會形成差序結(jié)構(gòu),最內(nèi)層是直系血緣關(guān)系,其次是旁系血緣關(guān)系,最外層是地緣關(guān)系[16]。流動人口對遷移地點(diǎn)的選擇也呈現(xiàn)差序結(jié)構(gòu)的現(xiàn)象。從其就業(yè)聯(lián)系的網(wǎng)絡(luò)來看,有直系親屬的地方是遷居地點(diǎn)的首選,其次是有旁系親屬的地點(diǎn),最后是熟人和老鄉(xiāng)的聚集地。從社會網(wǎng)絡(luò)的支持來看,親友、老鄉(xiāng)能夠?yàn)榱鲃尤丝谔峁┕ぷ鳈C(jī)會、住房,以地緣為特征的老鄉(xiāng)間的幫助則更為常見。流動人口自身也依據(jù)差序結(jié)構(gòu)將其他親友帶到現(xiàn)居住地。如C17(男,30歲):“我最早跟著老婆的表哥來北京做打印,幫他打工。老板包吃包住,老婆有時(shí)來北京的打印店里幫忙,有時(shí)在家看孩子、種田。”
鄉(xiāng)土秩序在城市環(huán)境下不斷延續(xù),但也在人口流動過程中發(fā)生了嬗變。一些流動人口不再將老鄉(xiāng)作為雇傭員工的首選。流動人口礙于鄉(xiāng)土之情,對老鄉(xiāng)的雇傭成本會增加,如果老鄉(xiāng)工作不夠積極、努力,也不方便直言。因此,流動人口在社會交往領(lǐng)域更多的是接近自己的老鄉(xiāng),但是在勞動關(guān)系領(lǐng)域,他們卻不愿意選擇老鄉(xiāng)。
C14(男,23歲):我來北京是因?yàn)橛H戚(舅舅)在北京開裝修公司,而且可以提供住的地方,自己就跟著過來了……在R大學(xué)校賣涼菜。我還叫了表弟來幫忙賣。表弟是親戚,剛開始做比較方便,成本低。店開大以后不想雇老鄉(xiāng),主要看能力和頭腦。我個(gè)人比較注重人際關(guān)系,老鄉(xiāng)做得不好反而不太好相處。
C15(男,21歲):老鄉(xiāng)都是干這個(gè)的(賣廢品),親戚也在這,他們都做得不錯(cuò)。過來(打工)可以有住宿,認(rèn)識的人互相幫忙,成本就比較低,投資大就賺得多。現(xiàn)在覺得請外地人干活比找老鄉(xiāng)要好,可以給工資低一些。
3. 遷居時(shí)間間隔:以經(jīng)濟(jì)條件為標(biāo)準(zhǔn)
遷居時(shí)間間隔是考察家庭化遷居傾向的重要指標(biāo)[17]。如果后續(xù)到來的家庭成員的時(shí)間間隔較短,說明家庭“舉家遷居”的趨勢更為明顯。訪談資料表明,對于有意愿將其他家庭成員帶到城市的流動人口,遷居的間隔一般不是具體的年限,而是抽象的經(jīng)濟(jì)條件。如C08(女,25歲)表示:“我打算等自己結(jié)婚成家,收入比較穩(wěn)定可以養(yǎng)家,而且弟弟結(jié)婚可以獨(dú)立生活以后,就把父母接出來,(讓他們)享受比較好的生活。”根據(jù)移民網(wǎng)絡(luò)理論,流動人口在帶動其他親友流動的過程中,可能需要提供諸如住房、工作機(jī)會等幫助,這要求先行人有足夠的能力在城市中立足。而這就需要一定的時(shí)間來實(shí)現(xiàn)。已有研究顯示,各批次家庭成員流動到城市的平均時(shí)間間隔大約在3~4年[18]。這說明,分批次的家庭成員向城市的遷居并不是某個(gè)倉促的決定,而是一個(gè)審慎的過程,其判斷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一般是經(jīng)濟(jì)條件。
四、 家庭遷居結(jié)果的決策
1. 依據(jù)家庭生命周期階段判斷遷居決策
家庭遷居決策會受到家庭成員關(guān)系和生命周期階段的影響,但家庭關(guān)系的利益序列卻有很大差別,撫養(yǎng)和贍養(yǎng)的地位并不平等。傳統(tǒng)代際關(guān)系中的“反哺模式”盡管在延續(xù),但是受到了弱化。
從家庭勞動力配置的角度來說,當(dāng)流出地家庭中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幫助時(shí),對上一代人養(yǎng)老的壓力就得到了分解。如C01(男,43歲)表示:“我有個(gè)弟弟在家里面。弟弟和弟妹都在縣城上班,他們每到節(jié)假日都會回家照顧父母,所以我在外面也不擔(dān)心老人養(yǎng)老的問題。”從時(shí)間角度來看,對父母的贍養(yǎng)在短時(shí)間內(nèi)不是流動家庭考慮的重點(diǎn)。如果父母無人照顧,那么直到父母年事已高時(shí)才將他們接到城里,或者考慮返鄉(xiāng)照顧父母。C10(男,32歲)說:“等父母老了,自己不能照顧自己,生活無法自理的時(shí)候,就接來住到一起。”顯然,傳統(tǒng)家庭制度中的輩分等級關(guān)系也受到人口流動的沖擊,日漸式微。
相對而言,孩子居于家庭關(guān)系利益序列中的首位,許多家庭的遷移決策以孩子的教育和發(fā)展為中心。例如,C19(女,26歲)表示:“現(xiàn)在主要考慮的是孩子的教育問題。等以后有了孩子,孩子的教育應(yīng)該由父母自己來,不能長期和爺爺奶奶一輩的人在一起,隔代人對孩子教育不好。孩子將來大了之后沒辦法在北京參加高考,必須回老家(重慶)讀中學(xué),那時(shí)候我可能會回家陪孩子。”有些家庭舉家遷居,就是為了讓孩子接受城市中更好的教育。例如,C09(女,39歲)說:“我是和老公同時(shí)出來打工的。出來打工就是為了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城里的教學(xué)條件比老家好。現(xiàn)在家就在孩子學(xué)校周圍不太遠(yuǎn)的地方。”
當(dāng)流出地家庭中沒有孩子,并且父代人還有能力獲得經(jīng)濟(jì)收入時(shí),流動人口向農(nóng)村家庭的匯款相對較少,其經(jīng)濟(jì)收入一般用于在城市的生活。與傳統(tǒng)的代際財(cái)富流動相比,流動人口的子代向父代的代際財(cái)富流有所減少。特別是剛剛外出務(wù)工的年輕人,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尚不牢固,所得收入大都留在本地消費(fèi),不會向流出地匯款。例如,C04(男,26歲):“現(xiàn)在剛就業(yè),不會往家里匯錢,家里也知道我的情況。家里的收入還可以,不會向我要錢。我現(xiàn)在的工資基本上足夠自己在城里生活的花銷。”而中年人的經(jīng)濟(jì)收入一般以孩子為中心進(jìn)行積累,在父母不提出需求時(shí)一般不會匯款,以便能盡快地在城市中積累財(cái)富。例如,C10(男,32歲)說:“父母有地,還有一些退休金,現(xiàn)在能自己照顧自己,所以沒給他們寄錢,在這邊賺的錢先顧著孩子,是給孩子留下的。”
2. 根據(jù)相對剝奪感差異調(diào)整遷居決策
新遷移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認(rèn)為,相對剝奪感是影響家庭遷居的重要因素[19~20]。本次訪談發(fā)現(xiàn),家庭感受的相對剝奪感與參照群體有關(guān)。家庭將農(nóng)村中其他家庭作為參照群體時(shí),當(dāng)感受到與其他家庭的差距時(shí)就會做出流動決策。但是,相對剝奪感的參照對象會在流動之后發(fā)生改變。流動家庭融入城市生活之后,他們會將參照群體改變?yōu)槌鞘屑彝ァ2⑶遥鲃蛹彝サ南鄬儕Z感不僅來源于城鎮(zhèn)人口,同樣來自于相同身份的農(nóng)民工中的成功者,如“老板”這一群體。
流動家庭在大城市與參照群體相比,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方面會感受到強(qiáng)烈的相對剝奪感。因此,大城市中的許多流動家庭會放棄在城市流動,選擇返鄉(xiāng)。如C17(男,30歲)表示:“在北京畢竟不是長久之計(jì),這里沒有根,而且生活成本太高,孩子上學(xué)就是燒錢,老板的孩子上個(gè)幼兒園就得交十幾萬,老板交得起我們交不起,大孩子曾經(jīng)也在北京上過兩個(gè)月幼兒園,太貴了就沒繼續(xù)上,還是回老家上比較便宜。房價(jià)也貴得很,工作個(gè)十年也只夠交首付。以后肯定會回家。”
中小城市的流動家庭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相對較弱。例如,C01(男,43歲)認(rèn)為:“這幾年的收入感覺還可以。打工以后,感覺我們家與一般的城市家庭相比也不差什么。”C06(女,34歲)也認(rèn)為:“在這里掙得多,消費(fèi)也不算太高。我們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車有房了(沒有戶口),感覺跟城里人經(jīng)濟(jì)狀況比也差不多。”當(dāng)流動人口有在中小城市長期定居的意愿時(shí),會考慮購買住房等,就會將城市人口作為參照對象,相對剝奪感也會相對增強(qiáng)。盡管能夠感受到這種差距的現(xiàn)實(shí)存在,但是大多數(shù)人并不會因此而選擇返鄉(xiāng),仍然愿意在城市中繼續(xù)工作。換言之,在流動家庭的預(yù)期中,他們認(rèn)為在城市中通過一段時(shí)期的努力,是能夠達(dá)到城市人的經(jīng)濟(jì)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例如:
C10(男,32歲):現(xiàn)在感覺城里的孩子家境是不錯(cuò)的,住房不是問題,最起碼爺爺輩兒有房子,父母親有房子,他自己就會少奮斗好幾年,家里也能給安排工作,生活基本保障是沒問題的。但是從農(nóng)村進(jìn)城的人首先就需要為自己奮斗一套房子,每月工資三千左右買套房子是很困難的。現(xiàn)在能維持生活還是在這里上班吧,找一份這樣有養(yǎng)老保險(xiǎn)的工作也不容易,慢慢攢錢買房。
C12(男,34歲):目前我家在城市里的問題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問題是買房買不起。掙錢的速度沒有房價(jià)上漲的速度快。我現(xiàn)在就是五十多平米的房子,我想換成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但每年賺的錢只夠消費(fèi)的,沒太多積蓄。這一點(diǎn)不如城里家庭。打算按揭慢慢還房款吧。
3. 遷居的最終結(jié)果具有不確定性
城市的就業(yè)、教育等對流動人口具有很強(qiáng)的吸引力,但是他們對未來的目標(biāo)還不明確。有些舉家遷居的家庭,他們在城市中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戶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對長期定居持有疑慮。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會關(guān)系,使流動人口懷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歲),甚至“我們兩個(gè)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養(yǎng)老”(C10,男,32歲)。幾乎所有參與訪談的流動人口都表示不會放棄在家鄉(xiāng)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僅具有“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的意義,也是流動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歲):現(xiàn)在在當(dāng)?shù)兀ǔ鞘校┮呀?jīng)買了房,也有了車,生活過得還可以。但就是沒有戶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現(xiàn)在都在身邊,在老家的房產(chǎn)、土地現(xiàn)在都讓弟弟照看,收入也歸他。以后在城里更穩(wěn)定一點(diǎn),可能會把老家的房子賣掉。不過等我和老公年齡大一些之后,我們還可能回老家蓋房,在老家養(yǎng)老。
C12(男,34歲):孩子在這上中學(xué),生意在這里發(fā)展,經(jīng)濟(jì)收入都已經(jīng)投入在這里,不能輕易就放棄這邊的生活。眼下自己還年輕,還想把自己的事業(yè)做起來。短期內(nèi)都會在這里生活,現(xiàn)在不會考慮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體不好了,肯定會回家照顧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還得留著,以后我們老了也許還要回去呢。
流動家庭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的期望也體現(xiàn)了遷移結(jié)果的不確定性(見表2)。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需要“看經(jīng)濟(jì)條件再定”和“沒想過”的比例共計(jì)43.12%。這表明,絕大多數(shù)流動人口對未來在城市中長期生活還持觀望態(tài)度。除此之外,選擇返回戶籍所在地農(nóng)村的居首位,占31.84%,顯示了家庭回遷決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階段性。而回到戶籍所在地城鎮(zhèn)的約占10.21%。相對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鎮(zhèn)的消費(fèi)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動家庭與農(nóng)村家庭密切聯(lián)系。在戶籍所在地的小城鎮(zhèn)養(yǎng)老,成為流動人口的另一種選擇。“以后是不是要長期留在北京,還要看情況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學(xué)了就回老家去做個(gè)小生意。我們濮陽的房價(jià)今年六千一平米,這還是當(dāng)?shù)刈钯F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過得比在北京強(qiáng)多了。”(C17,男,30歲)
五、 小結(jié)
本研究將家庭遷居決策總結(jié)為五階段的決策鏈條。五階段是指家庭遷居決策的商議期、配置期、決策期、跟隨遷居期、遷居結(jié)果期全過程。
家庭的決策起始于家庭的內(nèi)部商議,因此,第一階段是商議期。在商議期中,家庭成員通過商議決定家庭是否遷居,以及確定外出流動的人數(shù)、地點(diǎn)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家庭更多地體現(xiàn)出協(xié)商共議的協(xié)商模式。傳統(tǒng)的家庭制度與家庭成員關(guān)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動的沖擊,降低了父權(quán)的絕對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樣擁有議價(jià)的權(quán)力。家庭遷居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較高的經(jīng)濟(jì)收入,或花費(fèi)相對較少的成本(中小城鎮(zhèn)),來獲得家庭整體收入——成本的最滿意。
當(dāng)家庭做出向外遷居的決策后,家庭會對內(nèi)部的勞動力資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個(gè)家庭會成為一個(gè)相互配合、協(xié)調(diào)運(yùn)作的整體,通過對家庭成員進(jìn)行重新分工,保證在外流動的人口能夠順利生活、工作,以維持整個(gè)家庭的穩(wěn)定。
決策期是指家庭通過衡量閑暇與收入效用、流動的預(yù)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階段等因素,對遷居人數(shù)進(jìn)行選擇;按照人口流動的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的差序結(jié)構(gòu),即按照直系血緣關(guān)系、旁系血緣關(guān)系以及地緣關(guān)系由近至遠(yuǎn)的順序,選擇遷居地點(diǎn)。
在跟隨遷居期,家庭會對留守的家庭成員是否遷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員與首批遷居人口的時(shí)間間隔進(jìn)行決策。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是判斷遷居間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當(dāng)首批遷居的人滿足一定的經(jīng)濟(jì)條件后,才會將其他家庭成員帶到城市中。
遷居結(jié)果期,流動家庭會對定居或回流進(jìn)行決策。流動人口對返鄉(xiāng)或定居的選擇與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關(guān),同時(shí)也體現(xiàn)著傳統(tǒng)代際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孩子的教育問題將成為影響流動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額的教育成本會促使流動家庭返鄉(xiāng)。對老年人的贍養(yǎng)會通過家庭內(nèi)部資源的重新分配來解決,當(dāng)老年人需要照料時(shí),流動人口可能會選擇回流,或者將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從當(dāng)前我國家庭化遷居的情況來看,戶籍制度的制約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為流動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難,流出地的家庭稟賦是流動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們的心理寄托。這使得遷移的最終結(jié)果體現(xiàn)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xiàn):
[1] 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2年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報(bào)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張文新.近十年來美國人口遷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國流動人口帶眷系數(shù)及其影響因素[J].人口與經(jīng)濟(jì),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張靜.中國農(nóng)戶勞動力流動就業(yè)決策行為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湖北農(nóng)戶跟蹤調(diào)查的研究[J].經(jīng)濟(jì)前沿,2009,(10).
[7] 譚深.家庭策略,還是個(gè)人自主?——農(nóng)村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式的性別分析[J].浙江學(xué)刊,2004,(5).
[8] 孫朝陽.家庭策略視角下農(nóng)村已婚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性別選擇[J].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09,(1).
[9] 蔡昉.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馬瑞,徐志剛,仇煥廣,白軍飛.農(nóng)村進(jìn)城就業(yè)人員的職業(yè)流動、城市變換和家屬隨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1,(1).
[11] 陳宇峰.有限理性實(shí)現(xiàn)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05,(4).
[12] 何大安.行為經(jīng)濟(jì)人有限理性的實(shí)現(xiàn)程度[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燦.家庭現(xiàn)代化理論及其發(fā)展的回顧與評述[J].社會學(xué)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動的父權(quán):流動農(nóng)民家庭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0,(4).
[16]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農(nóng)民工的家庭遷移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7,(6).
[18] 盛亦男.中國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陽.遷移的雙重動因及其政策含義——檢驗(yàn)相對貧困假說[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2,(4).
3. 遷居的最終結(jié)果具有不確定性
城市的就業(yè)、教育等對流動人口具有很強(qiáng)的吸引力,但是他們對未來的目標(biāo)還不明確。有些舉家遷居的家庭,他們在城市中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戶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對長期定居持有疑慮。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會關(guān)系,使流動人口懷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歲),甚至“我們兩個(gè)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養(yǎng)老”(C10,男,32歲)。幾乎所有參與訪談的流動人口都表示不會放棄在家鄉(xiāng)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僅具有“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的意義,也是流動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歲):現(xiàn)在在當(dāng)?shù)兀ǔ鞘校┮呀?jīng)買了房,也有了車,生活過得還可以。但就是沒有戶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現(xiàn)在都在身邊,在老家的房產(chǎn)、土地現(xiàn)在都讓弟弟照看,收入也歸他。以后在城里更穩(wěn)定一點(diǎn),可能會把老家的房子賣掉。不過等我和老公年齡大一些之后,我們還可能回老家蓋房,在老家養(yǎng)老。
C12(男,34歲):孩子在這上中學(xué),生意在這里發(fā)展,經(jīng)濟(jì)收入都已經(jīng)投入在這里,不能輕易就放棄這邊的生活。眼下自己還年輕,還想把自己的事業(yè)做起來。短期內(nèi)都會在這里生活,現(xiàn)在不會考慮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體不好了,肯定會回家照顧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還得留著,以后我們老了也許還要回去呢。
流動家庭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的期望也體現(xiàn)了遷移結(jié)果的不確定性(見表2)。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需要“看經(jīng)濟(jì)條件再定”和“沒想過”的比例共計(jì)43.12%。這表明,絕大多數(shù)流動人口對未來在城市中長期生活還持觀望態(tài)度。除此之外,選擇返回戶籍所在地農(nóng)村的居首位,占31.84%,顯示了家庭回遷決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階段性。而回到戶籍所在地城鎮(zhèn)的約占10.21%。相對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鎮(zhèn)的消費(fèi)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動家庭與農(nóng)村家庭密切聯(lián)系。在戶籍所在地的小城鎮(zhèn)養(yǎng)老,成為流動人口的另一種選擇。“以后是不是要長期留在北京,還要看情況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學(xué)了就回老家去做個(gè)小生意。我們濮陽的房價(jià)今年六千一平米,這還是當(dāng)?shù)刈钯F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過得比在北京強(qiáng)多了。”(C17,男,30歲)
五、 小結(jié)
本研究將家庭遷居決策總結(jié)為五階段的決策鏈條。五階段是指家庭遷居決策的商議期、配置期、決策期、跟隨遷居期、遷居結(jié)果期全過程。
家庭的決策起始于家庭的內(nèi)部商議,因此,第一階段是商議期。在商議期中,家庭成員通過商議決定家庭是否遷居,以及確定外出流動的人數(shù)、地點(diǎn)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家庭更多地體現(xiàn)出協(xié)商共議的協(xié)商模式。傳統(tǒng)的家庭制度與家庭成員關(guān)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動的沖擊,降低了父權(quán)的絕對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樣擁有議價(jià)的權(quán)力。家庭遷居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較高的經(jīng)濟(jì)收入,或花費(fèi)相對較少的成本(中小城鎮(zhèn)),來獲得家庭整體收入——成本的最滿意。
當(dāng)家庭做出向外遷居的決策后,家庭會對內(nèi)部的勞動力資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個(gè)家庭會成為一個(gè)相互配合、協(xié)調(diào)運(yùn)作的整體,通過對家庭成員進(jìn)行重新分工,保證在外流動的人口能夠順利生活、工作,以維持整個(gè)家庭的穩(wěn)定。
決策期是指家庭通過衡量閑暇與收入效用、流動的預(yù)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階段等因素,對遷居人數(shù)進(jìn)行選擇;按照人口流動的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的差序結(jié)構(gòu),即按照直系血緣關(guān)系、旁系血緣關(guān)系以及地緣關(guān)系由近至遠(yuǎn)的順序,選擇遷居地點(diǎn)。
在跟隨遷居期,家庭會對留守的家庭成員是否遷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員與首批遷居人口的時(shí)間間隔進(jìn)行決策。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是判斷遷居間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當(dāng)首批遷居的人滿足一定的經(jīng)濟(jì)條件后,才會將其他家庭成員帶到城市中。
遷居結(jié)果期,流動家庭會對定居或回流進(jìn)行決策。流動人口對返鄉(xiāng)或定居的選擇與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關(guān),同時(shí)也體現(xiàn)著傳統(tǒng)代際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孩子的教育問題將成為影響流動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額的教育成本會促使流動家庭返鄉(xiāng)。對老年人的贍養(yǎng)會通過家庭內(nèi)部資源的重新分配來解決,當(dāng)老年人需要照料時(shí),流動人口可能會選擇回流,或者將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從當(dāng)前我國家庭化遷居的情況來看,戶籍制度的制約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為流動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難,流出地的家庭稟賦是流動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們的心理寄托。這使得遷移的最終結(jié)果體現(xiàn)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xiàn):
[1] 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2年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報(bào)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張文新.近十年來美國人口遷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國流動人口帶眷系數(shù)及其影響因素[J].人口與經(jīng)濟(jì),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張靜.中國農(nóng)戶勞動力流動就業(yè)決策行為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湖北農(nóng)戶跟蹤調(diào)查的研究[J].經(jīng)濟(jì)前沿,2009,(10).
[7] 譚深.家庭策略,還是個(gè)人自主?——農(nóng)村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式的性別分析[J].浙江學(xué)刊,2004,(5).
[8] 孫朝陽.家庭策略視角下農(nóng)村已婚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性別選擇[J].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09,(1).
[9] 蔡昉.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馬瑞,徐志剛,仇煥廣,白軍飛.農(nóng)村進(jìn)城就業(yè)人員的職業(yè)流動、城市變換和家屬隨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1,(1).
[11] 陳宇峰.有限理性實(shí)現(xiàn)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05,(4).
[12] 何大安.行為經(jīng)濟(jì)人有限理性的實(shí)現(xiàn)程度[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燦.家庭現(xiàn)代化理論及其發(fā)展的回顧與評述[J].社會學(xué)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動的父權(quán):流動農(nóng)民家庭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0,(4).
[16]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農(nóng)民工的家庭遷移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7,(6).
[18] 盛亦男.中國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陽.遷移的雙重動因及其政策含義——檢驗(yàn)相對貧困假說[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2,(4).
3. 遷居的最終結(jié)果具有不確定性
城市的就業(yè)、教育等對流動人口具有很強(qiáng)的吸引力,但是他們對未來的目標(biāo)還不明確。有些舉家遷居的家庭,他們在城市中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但可能因戶籍、生活成本等原因,對長期定居持有疑慮。家庭在流出地的宅基、耕地、社會關(guān)系,使流動人口懷有故土感情,想“有空就回去看看”(C08,女,26歲),甚至“我們兩個(gè)人(丈夫和妻子)都想回家養(yǎng)老”(C10,男,32歲)。幾乎所有參與訪談的流動人口都表示不會放棄在家鄉(xiāng)的宅基和耕地。宅基、耕地不僅具有“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的意義,也是流動人口心理上的寄托。
C09(女,39歲):現(xiàn)在在當(dāng)?shù)兀ǔ鞘校┮呀?jīng)買了房,也有了車,生活過得還可以。但就是沒有戶口。目前父母和孩子現(xiàn)在都在身邊,在老家的房產(chǎn)、土地現(xiàn)在都讓弟弟照看,收入也歸他。以后在城里更穩(wěn)定一點(diǎn),可能會把老家的房子賣掉。不過等我和老公年齡大一些之后,我們還可能回老家蓋房,在老家養(yǎng)老。
C12(男,34歲):孩子在這上中學(xué),生意在這里發(fā)展,經(jīng)濟(jì)收入都已經(jīng)投入在這里,不能輕易就放棄這邊的生活。眼下自己還年輕,還想把自己的事業(yè)做起來。短期內(nèi)都會在這里生活,現(xiàn)在不會考慮回家。但是,如果老人身體不好了,肯定會回家照顧老人。家里的老宅子也還得留著,以后我們老了也許還要回去呢。
流動家庭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的期望也體現(xiàn)了遷移結(jié)果的不確定性(見表2)。對未來養(yǎng)老地點(diǎn)需要“看經(jīng)濟(jì)條件再定”和“沒想過”的比例共計(jì)43.12%。這表明,絕大多數(shù)流動人口對未來在城市中長期生活還持觀望態(tài)度。除此之外,選擇返回戶籍所在地農(nóng)村的居首位,占31.84%,顯示了家庭回遷決策在生命周期中的階段性。而回到戶籍所在地城鎮(zhèn)的約占10.21%。相對大中城市而言,小城鎮(zhèn)的消費(fèi)水平更低,也便于流動家庭與農(nóng)村家庭密切聯(lián)系。在戶籍所在地的小城鎮(zhèn)養(yǎng)老,成為流動人口的另一種選擇。“以后是不是要長期留在北京,還要看情況再做打算。等孩子上小學(xué)了就回老家去做個(gè)小生意。我們濮陽的房價(jià)今年六千一平米,這還是當(dāng)?shù)刈钯F的,所以回老家去,日子過得比在北京強(qiáng)多了。”(C17,男,30歲)
五、 小結(jié)
本研究將家庭遷居決策總結(jié)為五階段的決策鏈條。五階段是指家庭遷居決策的商議期、配置期、決策期、跟隨遷居期、遷居結(jié)果期全過程。
家庭的決策起始于家庭的內(nèi)部商議,因此,第一階段是商議期。在商議期中,家庭成員通過商議決定家庭是否遷居,以及確定外出流動的人數(shù)、地點(diǎn)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家庭更多地體現(xiàn)出協(xié)商共議的協(xié)商模式。傳統(tǒng)的家庭制度與家庭成員關(guān)系模式受到人口流動的沖擊,降低了父權(quán)的絕對控制地位,未婚的女性也同樣擁有議價(jià)的權(quán)力。家庭遷居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較高的經(jīng)濟(jì)收入,或花費(fèi)相對較少的成本(中小城鎮(zhèn)),來獲得家庭整體收入——成本的最滿意。
當(dāng)家庭做出向外遷居的決策后,家庭會對內(nèi)部的勞動力資源重新整合和配置,即為配置期。在先行者外出后,整個(gè)家庭會成為一個(gè)相互配合、協(xié)調(diào)運(yùn)作的整體,通過對家庭成員進(jìn)行重新分工,保證在外流動的人口能夠順利生活、工作,以維持整個(gè)家庭的穩(wěn)定。
決策期是指家庭通過衡量閑暇與收入效用、流動的預(yù)期收入和成本、家庭生命周期階段等因素,對遷居人數(shù)進(jìn)行選擇;按照人口流動的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的差序結(jié)構(gòu),即按照直系血緣關(guān)系、旁系血緣關(guān)系以及地緣關(guān)系由近至遠(yuǎn)的順序,選擇遷居地點(diǎn)。
在跟隨遷居期,家庭會對留守的家庭成員是否遷居,以及留守家庭成員與首批遷居人口的時(shí)間間隔進(jìn)行決策。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是判斷遷居間隔的最主要因素。一般而言,當(dāng)首批遷居的人滿足一定的經(jīng)濟(jì)條件后,才會將其他家庭成員帶到城市中。
遷居結(jié)果期,流動家庭會對定居或回流進(jìn)行決策。流動人口對返鄉(xiāng)或定居的選擇與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關(guān),同時(shí)也體現(xiàn)著傳統(tǒng)代際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孩子的教育問題將成為影響流動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高額的教育成本會促使流動家庭返鄉(xiāng)。對老年人的贍養(yǎng)會通過家庭內(nèi)部資源的重新分配來解決,當(dāng)老年人需要照料時(shí),流動人口可能會選擇回流,或者將老人接到城市中共同生活。從當(dāng)前我國家庭化遷居的情況來看,戶籍制度的制約以及大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成為流動家庭定居的最大困難,流出地的家庭稟賦是流動家庭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他們的心理寄托。這使得遷移的最終結(jié)果體現(xiàn)出“走一步、看一步”的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xiàn):
[1] 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2年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報(bào)告[EB/OL].[2013-05-27]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
[2] 張文新.近十年來美國人口遷移研究[J].人口研究,2002,(7).
[3] 王志理,王如松.中國流動人口帶眷系數(shù)及其影響因素[J].人口與經(jīng)濟(jì),2011,(6).
[4] Jacob Mincer.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
[5] Steven H. Sandell.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7,59(4).
[6] 王春超,張靜.中國農(nóng)戶勞動力流動就業(yè)決策行為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湖北農(nóng)戶跟蹤調(diào)查的研究[J].經(jīng)濟(jì)前沿,2009,(10).
[7] 譚深.家庭策略,還是個(gè)人自主?——農(nóng)村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式的性別分析[J].浙江學(xué)刊,2004,(5).
[8] 孫朝陽.家庭策略視角下農(nóng)村已婚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性別選擇[J].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09,(1).
[9] 蔡昉.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征[J].人口研究,1997,(3).
[10] 馬瑞,徐志剛,仇煥廣,白軍飛.農(nóng)村進(jìn)城就業(yè)人員的職業(yè)流動、城市變換和家屬隨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1,(1).
[11] 陳宇峰.有限理性實(shí)現(xiàn)程度的新古典批判[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05,(4).
[12] 何大安.行為經(jīng)濟(jì)人有限理性的實(shí)現(xiàn)程度[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4,(4).
[13] Connell John, Dasgupta Biplab, Laishley Roy, Lipton Michae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he Evidence from Village Studies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4-25.
[14] 唐燦.家庭現(xiàn)代化理論及其發(fā)展的回顧與評述[J].社會學(xué)研究,2010,(3).
[15] 金一虹.流動的父權(quán):流動農(nóng)民家庭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0,(4).
[16]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17] 洪小良.城市農(nóng)民工的家庭遷移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7,(6).
[18] 盛亦男.中國流動人口家庭化遷居[J].人口研究,2013,(7).
[19] Stark Oded, D.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0] 蔡昉,都陽.遷移的雙重動因及其政策含義——檢驗(yàn)相對貧困假說[J].中國人口科學(xué),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