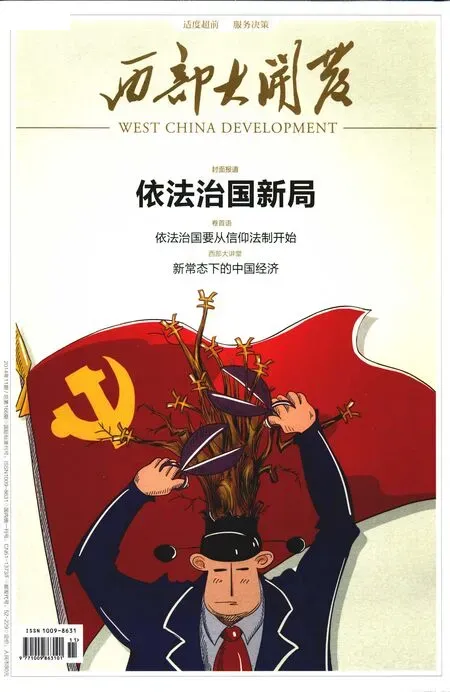厲以寧:經(jīng)邦濟(jì)世 詩(shī)化人生
(本文由本刊記者張靜根據(jù)資料整編)
“我的一生分三個(gè)階段: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經(jīng)歷了逃難、轟炸;新中國(guó)成立后,經(jīng)歷了各種運(yùn)動(dòng),特別是在‘文革’時(shí)勞動(dòng)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動(dòng),但沒(méi)有太大影響了。一個(gè)人受些磨難是有意義的,能鍛煉人。回首過(guò)去,無(wú)論什么境遇下,我都堅(jiān)持自己的觀(guān)點(diǎn)。可以不說(shuō)話(huà),但不要說(shuō)假話(huà)。”
——厲以寧
被稱(chēng)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界泰斗的厲以寧今年已經(jīng)85歲高齡,他有很多頭銜,也獲得了很多經(jīng)濟(jì)學(xué)界的最高獎(jiǎng)項(xiàng)。被評(píng)選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jiǎng)”,又被尊稱(chēng)為“厲股份”等等,種種的成就已經(jīng)不能再替代厲老為這個(gè)國(guó)家在經(jīng)濟(jì)學(xué)界所做的貢獻(xiàn),更無(wú)法衡量這一份難以評(píng)說(shuō)的舉人成就,這樣優(yōu)秀的一位大家,你想去讀些什么呢?年少的青年抱負(fù)?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還是感人至深的“16字情書(shū)”?
青年時(shí)代的文學(xué)造詣
厲以寧并非出身書(shū)香門(mén)第。他的父親是糧店店員,母親沒(méi)念完小學(xué),17歲就嫁入?yún)柤摇?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長(zhǎng)子厲以寧,“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是南京的簡(jiǎn)稱(chēng)。兩年后,厲以寧弟弟出生,父親開(kāi)始經(jīng)商,家境得以改善。
厲以寧4歲時(shí)舉家遷往上海,住在租界內(nèi),6歲入學(xué)讀書(shū)。太平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日軍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隨家人遷往湖南沅陵,就讀于湖南名校雅禮中學(xué)(當(dāng)時(shí)它由長(zhǎng)沙遷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厲以寧遠(yuǎn)眺山水,醉心文學(xué),“總是把沈從文的小說(shuō)當(dāng)成枕邊的讀物”,還以“山外山”的筆名寫(xiě)小說(shuō),為日后在詩(shī)詞方面的造詣打下基礎(chǔ)。
抗戰(zhàn)勝利后,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進(jìn)入金陵大學(xué)附中,對(duì)自然科學(xué)產(chǎn)生濃厚興趣。高中畢業(yè)前,全班同學(xué)去參觀(guān)一家化工廠(chǎng)時(shí),他有如此感慨:“如果全國(guó)每一座城市都擁有這樣陣容齊備的化工企業(yè),國(guó)家能集中全國(guó)的財(cái)力物力投入到工業(yè)建設(shè)上,那么,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就不會(huì)淪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厲以寧決定走“工業(yè)救國(guó)”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學(xué)時(shí),他選擇了化學(xué)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厲以寧決定參加國(guó)家建設(shè)。年底,他回到沅陵參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當(dāng)會(huì)計(jì)。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經(jīng)把湖南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直到花甲之年,他還填詞抒懷:“山城一別幾多秋,少年游,夢(mèng)中留……”
1951年,厲以寧決定參加高考,并委托雅禮中學(xué)的同學(xué)、在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讀書(shū)的趙輝杰代他報(bào)名。趙輝杰覺(jué)得厲以寧做過(guò)會(huì)計(jì),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報(bào)了北京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系。7月,厲以寧在長(zhǎng)沙參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經(jīng)濟(jì)系的錄取通知書(shū)。他就這樣陰差陽(yáng)錯(cuò)地被命運(yùn)推上了經(jīng)濟(jì)理論的研究道路。
當(dāng)時(shí),北大經(jīng)濟(jì)系和中國(guó)各行各業(yè)一樣,一切以前蘇聯(lián)為權(quán)威,講授的是傳統(tǒng)的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厲以寧談到,“羅志如教授開(kāi)設(shè)的《國(guó)民經(jīng)濟(jì)計(jì)劃》課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覺(jué)到,在蘇聯(lián)式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西方傳統(tǒng)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之間,還存在著第三條道路。”
大學(xué)4年,8個(gè)寒暑假,厲以寧都沒(méi)有回家,全部泡在圖書(shū)館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著作中。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系代理系主任陳振漢稱(chēng)贊他“成績(jī)優(yōu)異,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厲以寧畢業(yè)留校。他說(shuō),“我認(rèn)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從事經(jīng)濟(jì)系資料室編譯工作。”沒(méi)想到,兩年后,反右運(yùn)動(dòng)開(kāi)始,陳振漢、羅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科學(xué)繁榮的意見(jiàn)書(shū)》,遭到嚴(yán)厲批判,他們的得意門(mén)生厲以寧也被認(rèn)為是有問(wèn)題的,一直被扔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這20年的冷板凳,讓厲以寧受益匪淺。面對(duì)資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經(jīng)濟(jì)學(xué)原著和幾十種國(guó)外經(jīng)濟(jì)學(xué)期刊,他一頭扎了進(jìn)去,接觸各種經(jīng)濟(jì)學(xué)觀(guān)點(diǎn),還翻譯了一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原著和論文。
更難得的是,逆境之中,幾位教授繼續(xù)對(duì)厲以寧言傳身教。陳岱孫、趙迺摶教授教會(huì)他“鬧中取靜”的學(xué)習(xí)習(xí)慣;羅志如教授跟他談世界經(jīng)濟(jì)、談經(jīng)濟(jì)學(xué)新的發(fā)展方向;研究經(jīng)濟(jì)史的周炳琳、陳振漢教授不顧旁人非議,照舊和厲以寧來(lái)往,讓他幫忙收集和整理資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開(kāi)始,厲以寧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徑驟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難防卷地風(fēng)。狂風(fēng)過(guò)處,催老青山多少樹(shù)。今夜難眠,萬(wàn)戶(hù)千家一個(gè)天。”這是厲以寧當(dāng)時(shí)心境的真實(shí)寫(xiě)照。
1969年,厲以寧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yú)洲農(nóng)場(chǎng)勞動(dòng)。那里曾是血吸蟲(chóng)病的疫區(qū),據(jù)說(shuō)連勞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環(huán)境,不斷逃跑。在一張發(fā)黃的舊照片上,可以看到當(dāng)時(shí)的厲以寧瘦得顴骨凸起,肩上扛著一把鋤頭,腿上沾滿(mǎn)泥水,褲腿一邊高一邊低。他不再是詩(shī)人,更不是經(jīng)濟(jì)學(xué)者,而是一個(gè)正被極度疲勞折磨著的人。
1971年秋,厲以寧被轉(zhuǎn)到北京大興農(nóng)場(chǎng)。此后4年里,他又不斷在北京郊區(qū)“邊勞動(dòng)、邊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徹底在學(xué)校里安定下來(lái)。
20年的動(dòng)蕩中,厲以寧記了大量讀書(shū)筆記,寫(xiě)了許多無(wú)法發(fā)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鋪下。改革開(kāi)放后,正是憑借“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他擔(dān)起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界領(lǐng)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厲以寧出名太容易了,把過(guò)去那些壓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來(lái)發(fā)表就夠了。一句玩笑,幾多辛酸。
這20年的坎坷也讓厲以寧的經(jīng)濟(jì)觀(guān)點(diǎn)發(fā)生了劇烈變化。厲以寧說(shuō)到,“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nóng)村的貧困和城鄉(xiāng)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fā)現(xiàn)自己在大學(xué)階段所學(xué)的那套東西同現(xiàn)實(shí)的距離是那么大。中國(guó)要富強(qiáng),人民要過(guò)上好日子,看來(lái)不能再依靠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模式了。”厲以寧下決心探尋一條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個(gè)研究都能經(jīng)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厲以寧在一次新書(shū)發(fā)布會(huì)上說(shuō):“文章發(fā)表得再多,不聯(lián)系中國(guó)實(shí)際,對(duì)中國(guó)的改革沒(méi)有用處。”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gè)研究都能“經(jīng)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鄉(xiāng)”,上千萬(wàn)返城知識(shí)青年的就業(yè)一下子成了大問(wèn)題。1980年4月,中共中央書(shū)記處研究室和國(guó)家勞動(dòng)總局聯(lián)合召開(kāi)勞動(dòng)就業(yè)座談會(huì)。會(huì)上,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認(rèn)為“可以號(hào)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yè),企業(yè)也可以通過(guò)發(fā)行股票擴(kuò)大經(jīng)營(yíng)解決就業(yè)問(wèn)題”。3個(gè)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會(huì)議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學(xué)者贊同這個(gè)大膽的想法,國(guó)務(wù)院副總理萬(wàn)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對(duì)者仍占多數(shù),更有甚者,說(shuō)厲以寧“明修國(guó)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cāng)”。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qǐng)?bào)》上發(fā)表了《我國(guó)所有制改革的設(shè)想》一文,此后又多次為國(guó)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此得了個(gè)“厲股份”的稱(chēng)號(hào)。質(zhì)疑聲一直伴隨左右,但他不卑不亢,他認(rèn)為,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謂“爭(zhēng)論”,正常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是學(xué)術(shù)繁榮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來(lái)。“首鋼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帶領(lǐng)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鋼凈利潤(rùn)年均增長(zhǎng)45%。”但厲以寧認(rèn)為,承包制具有本質(zhì)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權(quán)和剩余索取權(quán)交給承包者后,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發(fā)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雙方更容易發(fā)生侵權(quán)的行為。1995年,首鋼因過(guò)度擴(kuò)張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職。隨后,首鋼走上股份制道路。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國(guó)工業(yè)普查結(jié)果出爐,39個(gè)大行業(yè)中,有18個(gè)是全行業(yè)虧損,股份制改革勢(shì)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寫(xiě)入十五大報(bào)告。厲以寧說(shuō),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對(duì)傳統(tǒng)所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從此,石油、電力、電信、民航、銀行等領(lǐng)域的國(guó)有企業(yè)紛紛轉(zhuǎn)變成股份制企業(yè)。
如何當(dāng)好一名老師
“我從來(lái)不想當(dāng)官,只想做一個(gè)學(xué)者。”30余年教書(shū)生涯里,厲以寧培養(yǎng)了大批學(xué)生,其中不乏李克強(qiáng)、李源潮、張茅、陸昊等政界要人和許多商界精英。
厲以寧說(shuō),他現(xiàn)在還在給本科生上大課,聽(tīng)課的學(xué)生擠滿(mǎn)教室。據(jù)一位大三學(xué)生回憶:“厲老師講課大多數(shù)時(shí)間不用講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綱。講課時(shí),他或站,或坐,或走動(dòng),臉上掛著輕松的笑容,一雙眼睛閃閃發(fā)光。他會(huì)忽然注視著某個(gè)同學(xué),請(qǐng)他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講完一段后問(wèn)大家:‘你們看有沒(méi)有道理?’”
厲以寧批改學(xué)生的論文非常認(rèn)真。1988年至1991年,李源潮攻讀北大管理學(xué)碩士學(xué)位。2009年,李源潮回憶說(shuō):“我當(dāng)厲老師學(xué)生的時(shí)候只是一個(gè)名不見(jiàn)經(jīng)傳的干部,而厲老師已經(jīng)是很有影響、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審閱我的碩士論文時(shí),從題目、結(jié)構(gòu)、觀(guān)點(diǎn)到打印格式,都給予細(xì)心指導(dǎo),花費(fèi)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錯(cuò)的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他都發(fā)現(xiàn)并向我指出來(lái)。厲老師這種扶持后生、誨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都十分感動(dòng)。”
滕飛是北京大學(xué)光華管理學(xué)院黨委副書(shū)記,2000年至2010年間師從厲以寧。他回憶道:“有一次跟厲老師到貴州畢節(jié)去調(diào)研,厲老師婉拒了當(dāng)?shù)卣才诺膮⒂^(guān)活動(dòng),主動(dòng)提出:‘我們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兒,就直接跟那兒的農(nóng)民聊天,獲得第一手資料。”
滕飛說(shuō),厲以寧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也像學(xué)者那樣觀(guān)察生活。“厲老師沒(méi)請(qǐng)保姆,自己做飯,還常去菜市場(chǎng)買(mǎi)菜,老百姓感受到的東西就是厲老師感受到的東西,所以他能真實(shí)了解目前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得到底怎么樣,非常有質(zhì)感。”
2004年,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董輔礽重病在床,無(wú)法繼續(xù)輔導(dǎo)博士生,便懇請(qǐng)厲以寧將這幾位博士生收入門(mén)下。厲以寧欣然答應(yīng):“我和董老師是多年好友,董老師的學(xué)生就是我的學(xué)生。”現(xiàn)任中國(guó)鋁業(yè)國(guó)際貿(mào)易公司副總經(jīng)理的程志強(qiáng)就是這幾位博士生之一。
為妻書(shū)寫(xiě)“世間最短的情書(shū)”
學(xué)術(shù)之外,厲以寧對(duì)家庭充滿(mǎn)了柔情。他與夫人何玉春的緣分始于湖南沅陵。當(dāng)時(shí),厲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厲以寧與何玉春的哥哥何重義是雅禮中學(xué)的同學(xué),但7歲的何玉春對(duì)厲以寧并沒(méi)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從華中工學(xué)院電力系畢業(yè),分配到遼寧鞍山鋼鐵公司發(fā)電廠(chǎng)工作,她去探望隨哥哥定居北京的母親,和厲以寧重逢。兩人一見(jiàn)鐘情,開(kāi)始了“異地戀”。
一天,何玉春接到厲以寧的信,信中只有16個(gè)字:“春:滿(mǎn)院梨花正惱人。尋誰(shuí)去?聽(tīng)雨到清晨。”這首《十六字令》被同學(xué)們稱(chēng)為“世間最短的情書(shū)”。當(dāng)時(shí),厲以寧是“有問(wèn)題的人”,工資比何玉春還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選擇了他。1958年春節(jié),兩人在北京結(jié)婚。婚后第五天,厲以寧要去京郊勞動(dòng),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厲以寧滿(mǎn)懷離愁:“昨夜頻頻雙舉杯,今朝默默兩分飛,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淚爐前備早炊。”
從此是13年的兩地分居,每年只有兩周探親時(shí)間。1958年底,女兒厲放出生;1963年,兒子厲偉出生。1969年,厲以寧下放江西,將一雙小兒女留在北京,交給自己的母親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棄一切調(diào)到江西。夫妻倆住在放農(nóng)具的茅草房里,房間一角還有黃鼠狼做的窩,但能在一起,已經(jīng)讓厲以寧無(wú)比滿(mǎn)足:“往事難留一笑中,離愁十載去無(wú)蹤。銀鋤共筑田邊路,茅屋同遮雨后風(fēng)。朝露冷,晚霞紅,門(mén)前夜夜稻香濃。縱然汗?jié)n斑斑在,勝似關(guān)山隔萬(wàn)重。”
改革開(kāi)放后,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競(jìng)相邀請(qǐng)厲以寧講學(xué)、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厲以寧身兼多項(xiàng)社會(huì)職務(wù),何玉春就當(dāng)“秘書(shū)”。在收發(fā)室,學(xué)生們經(jīng)常看到何師母替厲老師取信件,有時(shí)多得拿不動(dòng);在家里,她是厲以寧著作的第一讀者,厲以寧說(shuō):“她是電氣專(zhuān)業(yè)的高級(jí)工程師,經(jīng)濟(jì)學(xué)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閱讀書(shū)稿時(shí),感到這兒或那兒還不夠簡(jiǎn)明,不易被人們看懂,我就進(jìn)行修改,直到她滿(mǎn)意了為止。”
2008年,在金婚50年時(shí),厲以寧寫(xiě)道:“攜手同行五十秋,雙雙白了少年頭,凄風(fēng)苦雨從容過(guò),無(wú)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師無(wú)不感慨:何老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厲以寧有多大名氣,而在于厲以寧為她寫(xiě)詩(shī),從青春年少寫(xiě)到了滿(mǎn)頭白發(fā),從新婚燕爾寫(xiě)到了兒孫滿(mǎn)堂。
厲以寧的學(xué)生程志強(qiáng)說(shuō):“厲老師不僅在治學(xué)上是個(gè)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個(gè)大家。”夫妻兩地分居13年,厲以寧既當(dāng)?shù)之?dāng)媽?zhuān)馀囵B(yǎng)孩子的進(jìn)取心。他曾說(shuō):“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錢(qián)給他們,因?yàn)樗麄冇心芰ψ约簰辏蝗绻⒆記](méi)有能力,留錢(qián)給他又有什么用呢?”
記者手記:
往往人們說(shuō)起厲老,都被“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稱(chēng)謂所傾注,毫無(wú)疑問(wèn),他是中國(guó)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之一。他年事已高,卻依然帶著沙啞的嗓音去講課,他的每次亮相、每次發(fā)言,都會(huì)引起人潮涌動(dòng)、各界關(guān)注;他的觀(guān)點(diǎn)嚴(yán)謹(jǐn)、獨(dú)到、鮮明;從“厲股份”到“厲民營(yíng)”等從他學(xué)術(shù)觀(guān)點(diǎn)中提煉出的名號(hào),總代表著當(dāng)時(shí)討論的焦點(diǎn)。
然而他的故事卻為他的諸多成就增添了很多色彩!這些色彩也充溢著這位值得我們憧憬的老人的精彩人生!我們除了為他喝彩外,更多的是要敬仰他!學(xué)習(x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