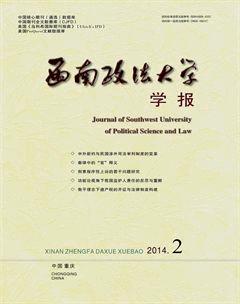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與重申
作者簡介:馬榮春(1968-),男,江蘇東海人,揚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與重申
摘 要:作為罪刑關系的一種特性,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應在刑事一體化的領域得到拓展。若聯(lián)系刑事理念和刑事實踐的最新發(fā)展,則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應在當下拓展出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并且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在相互滲透和相互說明之中“拱舉”著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由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來充實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是對罪刑關系本身的肯定,不僅有著深刻的人權意義,而且有著基本的刑事政策意義。罪刑關系是刑事法理論的一個制高點。
關鍵詞:罪刑關系;寬和性;當事人性;可合作性;可暫緩性
中圖分類號:DF61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2.04
一、問題的提出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是筆者在博士學位論文中論證的關于罪刑關系特性的一個概念,而與其相對的是罪刑關系的強制性。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罪刑關系論》共論述了罪刑關系的六組特性:內(nèi)容特性包括客觀性與主觀性、效力特性包括強制性和寬和性、存在特性包括靜態(tài)性和動態(tài)性、層次特性包括一般性與個別性、規(guī)模特性包括相適應性與不相適應性、經(jīng)濟特性包括經(jīng)濟性與非經(jīng)濟性。(參見:馬榮春罪刑關系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62-107.)何謂罪刑關系的強制性?“罪刑關系的強制性是指有罪必有刑的搭配狀態(tài),即犯罪與刑罰搭配狀態(tài)之‘實。罪刑關系的強制性首先體現(xiàn)于刑法立法之中,即法定之罪必引法定之刑,法定之刑必隨法定之罪;罪刑關系的強制性再就是體現(xiàn)為刑法司法之中的實刑裁判與執(zhí)行。”[1]當初,筆者論證罪刑關系的強制性主要是立于兩個“根據(jù)”:一是刑法的過程根據(jù),即刑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先罪后刑的過程;二是刑法的價值根據(jù),即罪刑關系的強制性符合著刑法懲罰犯罪的報應價值和預防犯罪的功利價值[1]69-71。那么,又何謂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是指因制度規(guī)定而形成的刑不附罪或暫時虛置的情況,即犯罪與刑罰搭配狀態(tài)之‘虛。”[1]72當初,筆者論證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也主要是以刑法懲罰犯罪的報應價值和預防犯罪的功利價值為價值論根據(jù)[1]73,即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也是“虛中有實”。在當初的論證中,筆者提出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意味著罪與刑可以有條件地相互分離,是一種“刑法不典型”[1]74。而在總體上,“罪刑關系的強制性賦予刑法以原則性,而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則賦予刑法以靈活性。顯然,罪刑關系的強制性和寬和性之間所構成的是對立統(tǒng)一的辨證關系。但是,此兩種特性皆可以報應正義和功利正義為存在根據(jù)。或者說,強制性和寬和性只是為罪刑關系實現(xiàn)刑法報應正義和功利正義兩個方面的價值提供必要的不同方位而已。”[1]75而罪刑關系的強制性與寬和性的緊密結合便是“寬嚴相濟”。
筆者當初對罪刑關系的強制性與寬和性的對照性論證現(xiàn)已顯示出罪刑關系寬和性視野的明顯不足:一是局限于刑法學領域,僅從刑法關于免除處罰、緩刑的制度規(guī)定和赦免制度來考察罪刑關系的寬和性[1]72;二是遠遠滯后于刑事理念與刑事實踐的最新發(fā)展;三是對罪刑關系寬和性的把握顯得狹窄而淺薄。筆者對罪刑關系寬和性的以往考察不僅存在前述不足,而且前述不足之間又“層層相因”。于是,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問題應走出刑法學的領域局限并緊隨刑事理念和刑事實踐的最新發(fā)展而“登高望遠”。作為罪刑關系的一種特性,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是否能夠得到新的拓展?如果能夠得到新的拓展,則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又可得到怎樣的重申?
二、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之一: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在筆者看來,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在當下首先應拓展出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并且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可以視為其寬和性的主體性拓展,即從主體角度對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所作的拓展。
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本應是罪刑關系的天然屬性或與生俱來的屬性。為何這樣說呢?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從康德的等量報應,還是從黑格爾的等價報應,我們都可以看出,犯罪與刑罰這對具有否定之否定關系的范疇代表著一正一反,即能量對等或相互抗衡的“兩極性”事物。那也就是說,罪刑關系本來就是一種正反關系、對等關系和抗衡關系。那么,當犯罪人與被害人或代表被害人與社會的國家司法機關同時走進前述關系,則前述關系就演變成了具有平等性的當事人關系,或曰具有當事人性。然而,在人類歷史各階段的刑事訴訟模式中,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都被塵封起來了:在糾問式的刑事訴訟模式中,犯罪人是處于被糾問的地位,故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無從體現(xiàn),即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既無名,也無實;在對抗式的刑事訴訟模式中,犯罪人因與國家司法機關的能量懸殊而自然難以進行真正的對抗,故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也無從體現(xiàn),即有名而無實。為何糾問式的刑事訴訟模式和對抗式的刑事訴訟模式會將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予以塵封?在筆者看來,在糾問式的刑事訴訟模式中,人權觀念幾乎蕩然無存,而這里的人權既包括犯罪人的人權,也包括個案中被害人的人權。而在對抗式的刑事訴訟模式中,由于雙方力量的懸殊即對抗本身的“名不副實”,故人權觀念往往也是“名不副實”,或曰往往只是個“虛像”。因此,人權觀念是不同刑事訴訟模式下的罪刑關系是否具有當事人性的最終決定因素。那么,我們一想便知,令人權觀念淡薄的是秩序主義與整體主義的興盛。而在秩序主義與整體主義興盛之下,罪刑關系便很難閃爍出當事人性的光芒。時下,人權觀念日益受到重視,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亦將日益閃爍出應有的人權光彩或人文光彩,并對應著相應的刑事訴訟模式。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馬榮春: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與重申理論得以挖掘的資源永遠是實踐本身,罪刑關系理論也是如此。而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的強調(diào)及其可接受性,正是以活生生的刑事實踐本身為強有力的助推。學者指出:“從侵權之源的角度來看,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最大威脅來自國家,被害人的權利則往往受到犯罪人的侵害,并受到國家司法機關不作為的消極影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幾乎所有國家的憲法都只強調(diào)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而很少提及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問題。但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問題就是在人權保護問題上走了很多彎路,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在強調(diào)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同時,忽略了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問題。西方國家興起的被害人國家賠償運動和恢復性司法運動,就著重強調(diào)解決被害人的民事賠償和精神賠償問題。中國近年來出現(xiàn)的刑事和解運動和被害人國家司法救助改革,體現(xiàn)了解決被害人賠償問題的動向;最近興起的量刑程序獨立化的改革動向,則顯示出被害人獲得刑罰正義的需要開始得到鄭重對待。”[2]在此,筆者首先要強調(diào)的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的民事賠償和精神賠償問題、被害人獲得刑罰正義需要問題,甚至被害人對罪名確定的意見問題,都是罪刑關系的內(nèi)容。而正視和解決這些問題,是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的題中之義。那么,對于刑事和解而言,“和解”二字直接說明了刑事案件處置的當事人性,因為在沒有當事人性的訴訟法律關系之中,“和解”是沒有空間與可能的;對于在理論上可預期的辯訴交易而言,“交易”二字更是直接說明了刑事案件處置的當事人性,因為在沒有當事人性的訴訟法律關系之中,“交易”更是沒有空間與可能的。可以這么說,刑事和解所體現(xiàn)的是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一種當事人性,而辯訴交易所體現(xiàn)的則是犯罪人與國家機關及其所代表的社會之間的一種當事人性。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在新中國的刑事訴訟立法中經(jīng)歷了有目共睹的可喜變化: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言,雖然其地位剛開始就被定位為訴訟當事人,但刑事和解運動已經(jīng)使其訴訟當事人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可以想見,當可預期的辯訴交易在我們的法治土壤生根發(fā)芽,則其訴訟當事人地位將顯得更加“正統(tǒng)”;對被害人而言,刑訴法的修改頒行將其地位由訴訟參與人提升至訴訟當事人,而如今,刑事和解運動使其訴訟當事人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而其訴訟當事人地位的更進一步強化的體現(xiàn)便是對被告人刑罰正當性的意見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所經(jīng)歷的前述變化,表面上與罪刑關系無關,而實質(zhì)是罪刑關系的樣態(tài)變化在訴訟領域的一種“投射”。易言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的當事人化,是罪刑關系的當事人化的一種“投射”。對于刑事訴訟,則肯定乃至強化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便意味著肯定乃至強化罪刑關系的平等性和對等性。而只有通過此平等性和對等性,則罪刑關系才有公平正義可言,進而才有所謂恢復性刑事司法可言。當然,在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中,罪刑關系也便同時呈現(xiàn)民事化或民事性色彩,但這更能烘托出罪刑關系的主體平等性。
任何違法犯罪,其實質(zhì)都是一種關系沖突。而只有聯(lián)系關系沖突,“當事人”這個概念才有實際意義。犯罪是一種關系沖突,刑罰是一種關系沖突,罪刑關系更是一種關系沖突。那么,當事人性理應成為罪刑關系的一種特性。而如果否認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則等于否認罪刑關系本身。之所以要在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之下討論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多少有那么一點“按圖索驥”的思路,因為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問題與其當事人性問題之間構成了上位問題與下位問題的關系,也構成了體現(xiàn)與被體現(xiàn)的關系。
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反映了刑事訴訟“諸法合體”的情狀,即作為當事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被害人以及代表被害人和社會的國家司法機關雙方之間,不僅要面對著刑事事項本身,還要面對著民事事項,亦即雙方要“當著”諸多事項。
而下文將要論述的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則是罪刑關系寬和性問題繼其當事人性之后的一種邏輯延伸。
三、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之二: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在筆者看來,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在當下就是應拓展出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并且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可以視為其寬和性的內(nèi)容性拓展,即從內(nèi)容角度對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所作的拓展。
對于刑事和解,有學者指出:“刑事和解運動的出現(xiàn),使得被害方可以與被告方面對面地進行協(xié)商,被害方不僅獲得了被告人的賠禮道歉,獲得了相對高額的賠償,而且這種賠償可以得到即時履行,根本不存在執(zhí)行難的問題。而被告人在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的基礎上,獲得了被害人的諒解,要么被免除刑事責任,要么被判處緩刑或者適用顯著輕微的刑罰。……毫無疑問,刑事和解運動促成了一種各方利益兼得的局面,具有比傳統(tǒng)的對抗性司法模式更為明顯的優(yōu)勢。”[2]115于是,“刑事和解運動的興起,意味著一種新的建立在合作和協(xié)商基礎上的司法模式在逐漸顯現(xiàn),這種模式可以被稱為‘私力合作模式。”[2]116在筆者看來,以刑事和解為標志的刑事訴訟合作模式在根本上所牽涉的是罪刑關系,而此牽動則使我們對罪刑關系的屬性獲得了一種與時俱進的發(fā)現(xiàn),即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任何法律關系都是一種關系,而凡是關系,都可以進行合作或曰具有可合作性。罪刑關系亦如此,在和諧發(fā)展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時代背景下,罪刑關系或許更應具有可合作性,因為此屬性會帶來犯罪人與被害人及社會之間沖突關系的緩和與調(diào)整,即由“對抗”走向“合作”或“對話”,而“合作總比對抗好”。
不僅刑事和解,或許不久將成為刑事法學領域熱門話題的辯訴交易所體現(xiàn)的也包括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即犯罪嫌疑人與公訴機關及其所代表的社會之間謀求“雙贏”的一種合作。如果我們把刑事和解視為一種“私力合作”,則辯訴交易可以視為一種“公私合作”。在刑事和解的“私力合作”中,和解對于被害一方意味著財產(chǎn)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修復,對于加害一方意味著人身危險性的消減,而對雙方的“意味”又意味著作為罪刑關系一極的“罪”在客觀危害和人身危險性等內(nèi)在構成的“縮水”,從而使得作為另一極的“刑”作出“等量等價”的對應,從而使得罪刑關系實現(xiàn)一種“水落船低”般的動態(tài)均衡。可見,刑事和解這種“私力合作”所最終影響的是罪刑關系,但不是破壞罪刑關系,而是在促進罪刑均衡之中動態(tài)地維系罪刑關系。
那么,辯訴交易呢?在筆者看來,“盡管是出于獲得不被指控或者減輕指控或者減少指控的個人動機,但辯訴交易中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辯過程仍然是一個悔罪或自我矯正的過程,即辯訴交易中的有罪答辯也有使犯罪人融入社區(qū)或社會的功效即所謂‘重新融入的功效。”[3]可見,辯訴交易的過程也是犯罪人人身危險性得到消減的過程,或曰也是“犯罪人的恢復過程”。而此人身危險性的消減或正常人格的恢復過程是在控辯雙方的合作即“交易”之下得以進行的。那么,當答辯方的人身危險性的消減直接影響著作為罪刑關系一極的“罪”,則勢必引起罪刑搭配即罪刑關系的動態(tài)調(diào)適即在動態(tài)中達致平衡。其實,辯訴交易的有罪答辯更容易帶來“對被害人的修復”包括物質(zhì)修復和精神修復。如果這樣看問題,則辯訴交易之中的罪刑關系更具可合作性。而反過來說,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不僅可以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關系范疇的佐證,而且更可以為辯訴交易制度提供關系范疇的佐證。據(jù)統(tǒng)計,現(xiàn)在美國所有刑事案件中大約90%都是通過辯訴交易解決的[4]。那么,其背后是否隱藏著對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的一種廣泛認知?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罪刑關系是一種“活性關系”,而可合作性或許正是其“活性因子”。
無論是刑事和解,還是辯訴交易,都已經(jīng)牽涉刑事訴訟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刑事訴訟模式。對于刑事訴訟模式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帕克教授提出并論證了刑事訴訟的兩大模式理論,即犯罪控制和正當程序。犯罪控制和正當程序兩大刑訴模式理論具有跨越時空的代表性,其貢獻在于揭示了實踐中的兩個難題:一是國家要打擊犯罪,要有效地控制犯罪;另一個則是要維護正當程序,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防御權。形象地說,犯罪控制模式是一種接力比賽模式,正當程序模式則是一種跨欄賽跑模式。在此兩種模式之下,刑事訴訟要么是打擊犯罪的工具,要么是保障人權的手段。于是,耶魯大學的格里菲斯教授隨后提出了專門針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訴訟模式即家庭模式。在家庭模式理論面前,無論是犯罪控制模式,還是正當程序模式,都是對抗制訴訟的產(chǎn)物,都是對抗模式或“爭斗模式”[2]152。而家庭模式意味著在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之外還有第三種價值體系,即以關愛、挽救和治療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2]112。家庭模式的提出意味著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已經(jīng)面臨著要“淡出”刑事領域的命運。那么,要逐漸取代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的模式,或曰即將“淡入”的刑事訴訟模式是什么呢?有學者指出,在目前的法庭審判中,只有20%左右的被告人作無罪辯護或者當庭翻供,80%以上的案件中被告人當庭作出了有罪供述,放棄了無罪辯護的權利。在這些案件中,還有多少對抗性司法存在的空間?在這樣的法庭審判中,無罪推定、程序正義還有多少可適用的制度空間?于是,在對抗性司法模式之外,應該存在著適用于大多數(shù)案件的刑事訴訟程序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即以被告人認罪、雙方達成協(xié)議為基礎的合作性司法。其中,被告人與檢察官的合作是“公力合作”,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合作是“私力合作”。那么,對抗性司法理論對大多數(shù)刑事案件的刑事訴訟不具有解釋力[2]125。這就意味著只有合作性司法理論對大多數(shù)刑事案件的刑事訴訟才具有解釋力。
由刑事訴訟模式問題“迂回”,筆者要說的是,無論是糾問式刑事訴訟模式,還是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還是合作式刑事訴訟模式,其背后所隱藏的是罪刑關系的不同樣態(tài),而只有在合作式刑事訴訟模式的背后,罪刑關系才可獲得其應然樣態(tài),即可合作性樣態(tài)。在糾問式刑事訴訟模式下,罪刑關系毫無可合作性,因為糾問本身就意味著國家一方意欲實現(xiàn)對被糾問者的完全壓制;而在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之下,罪刑關系亦無可合作性,因為對抗所欲走向的也只是那通常很難達致的“訴訟均勢”。而只有在合作式刑事訴訟模式之下,才能對應出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
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體現(xiàn)了罪刑關系的一種對話性,從而也是刑法的對話性。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樣態(tài)在前文所論述的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和下文將要論述的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之間,構成了一種“承上啟下”。
四、罪刑關系寬和性的當下拓展之三: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在筆者看來,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在當下還應拓展出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并且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可以視為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的效力性拓展,即從效力角度對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所作的拓展。
在實踐中,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可以暫緩起訴和暫緩判決作為典型體現(xiàn)。暫緩起訴和暫緩判決在有的國家的刑事實踐中已經(jīng)很常見,而在我們這個國度則處于謹慎試行狀態(tài),并且尚無“堂而皇之”的法律依據(jù)。就暫緩起訴和暫緩判決在我國的試行來看,有學者指出,一些地方的檢察院較早就對暫緩起訴制度進行了試點。所謂暫緩起訴制度,是指對實施了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設定一定的考驗期,發(fā)布社會服務令,如果考驗期結束以后符合條件就不再提起公訴的制度。暫緩起訴制度使得檢察官在起訴和不起訴之間有了第三種程序選擇。這一制度在10多年的試行之中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與暫緩起訴制度相類似的,是很多法院在10多年前試行的暫緩判決制度。暫緩判決制度的適用對象是在校學生,其與暫緩起訴制度異曲同工:設定一個考驗期,附條件地暫緩判決。考驗期內(nèi),讓被告人在所在地勞動,勞動結束后符合條件就不再宣告判決,或宣告定罪免刑[4]27-28。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暫緩起訴,還是暫緩判決,都可以視為是將罪刑關系暫時予以虛置,即將罪刑關系的實際“兌現(xiàn)”予以暫緩。而在罪刑關系的暫緩狀態(tài)之中,附條件的考驗可以使得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或犯罪人格得到消減或重塑。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暫緩起訴和暫緩判決通過使得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或犯罪人格得到消減或重塑而在時間的延長線上,動態(tài)地調(diào)適著罪刑關系,即別樣地實現(xiàn)著罪刑關系的動態(tài)均衡。
“一切皆有可能”。既然已有暫緩起訴和暫緩判決,則暫緩行刑不是沒有可能。所謂暫緩行刑,是指附條件地暫不執(zhí)行已判刑罰而讓受到罪刑宣告者在一定時期內(nèi)接受考驗。符合相應條件者,所宣告刑罰不再執(zhí)行;不符合相應條件者,則所宣告刑罰便付諸執(zhí)行。在筆者看來,暫緩行刑,更是可以理解為在時間的延長線上通過附條件考驗來消減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或重塑其犯罪人格,從而動態(tài)地調(diào)適著罪刑關系,最終更加別樣地實現(xiàn)著罪刑關系的動態(tài)均衡。
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意味著我們今天應謹慎對待被譽為刑法學之父的貝卡利亞曾經(jīng)所主張的刑罰的必定性與及時性。在筆者看來,貝卡利亞曾經(jīng)所主張的刑罰的必定性與及時性分別對應著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貝卡里亞曾說:“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因為,即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5]而“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受到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5]110可見,刑罰的必定性就是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而罪刑關系的必定性直接關聯(lián)著刑法的預防效果,包括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貝卡里亞又曾說:“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lián)系就越突出、越持續(xù),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5]47-48而“只有使犯罪和刑罰銜接緊湊,才能指望相關的刑罰概念使那些粗俗的頭腦從誘惑他們的、有利可圖的犯罪圖景中猛醒過來。推遲刑罰盡管也給人以懲罰犯罪的印象,然而,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懲罰,倒像是表演。”[5]48可見,刑罰的及時性就是罪刑關系的及時性,而罪刑關系的及時性也直接關聯(lián)著刑法的預防效果,包括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正如羅伯斯庇爾所說:“拖延審理訴訟案件,等于不處理犯罪;處罰不堅決,就是鼓勵一切犯罪者。”[6]無論是罪刑關系的必定性,還是罪刑關系的及時性,其所能發(fā)揮的預防效果都是通過強化人們對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心理連接,從而達到抑制犯罪意念和強化禁忌意識來實現(xiàn)的。在當下,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仍應得到肯定,但正如罪刑關系的強制性應為其寬和性留下空間,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也應為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留下空間,而這又是由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的合理性所決定的。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的合理性是在與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的對比中顯現(xiàn)出來的: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意味著犯罪人在“刑罰圈”面前只進不出,即罪刑關系構成了對犯罪人絕對不能打開的“枷鎖”,而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意味著罪刑關系構成了對犯罪人尚可有條件打開的“枷鎖”,即在刑事法律關系中還架設著為犯罪人“浪子回頭”即重新做人的“黃金橋”,且此橋是暫緩起訴、暫緩判決和暫緩執(zhí)行所連環(huán)而成的“多孔黃金橋”。顯然,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的合理性主要是體現(xiàn)在預防犯罪上。而在預防犯罪上,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在相當程度上是消極的和“事后性”的,即采用刑罰手段的,而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在相當程度上則是積極的和“事前性”的,即采用非刑罰手段的。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的合理性還體現(xiàn)在報應犯罪上,而其在報應犯罪上的合理性則體現(xiàn)為遲緩的報應和謹慎的報應。那么,將預防犯罪和報應犯罪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則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最終體現(xiàn)為罪刑關系的一種克制性,從而也是刑法本身的一種克制性。
在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中,所能得到暫緩的是對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人不利的刑事后果,但暫緩是以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人必須接受相應考驗且考驗要有效果,即其人身危險性或犯罪人格有所消減,甚至同時要對被害方給予相當?shù)奈镔|(zhì)賠償與精神撫慰為前提條件的,故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中蘊含著罪刑關系的一種敦促性,而其可暫緩性及其所蘊含的敦促性對于加害與被害雙方又都具有著恢復性功能。
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是相互滲透和相互說明的。具言之,沒有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則無其可合作性,亦即罪刑關系的可合作性是以其當事人性為前提并構成其直接體現(xiàn),而罪刑關系的可暫緩性則是其可合作性的直接體現(xiàn)和其當事人性的進一步體現(xiàn)。其中,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是其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的“根基”,而其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則是其體現(xiàn)和進一步的體現(xiàn)。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在相互滲透和相互說明之中“拱舉”著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并且在對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的“拱舉”之中,當事人性與可合作性呈現(xiàn)出“積極作為”的色彩,而可暫緩性則呈現(xiàn)出“消極不作為”的色彩。如果說刑法的謙抑性在以往是一個空洞的說教,那么罪刑關系的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及其所“拱舉”著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便將刑法的謙抑性在某個方面落到了實處。
五、罪刑關系寬和性拓展后的重申首先,拓展后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并非背反罪刑關系本身,而是罪刑關系本身存在乃至不斷獲得新生的一種體現(xiàn)或說明。換句話說,強調(diào)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并用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來充實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似乎是在削弱罪刑關系乃至使之蕩然無存,而實際上,這種做法是在肯定和運用罪刑關系。貝卡利亞通過刑罰的必定性和刑罰的及時性所設定的罪刑關系顯得僵硬而冷酷,有著貝卡利亞那個時代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正如有人指出,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的成書時代是產(chǎn)業(yè)革命剛剛開始,同時又是司法黑暗和政治黑暗的時代[7]。在筆者看來,罪刑關系的必定性與及時性既迎合著資本主義發(fā)展對客觀性和確定性的要求,又能抵御當時的司法黑暗與政治黑暗,并又反過來助益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但時代發(fā)展變化了,罪刑關系的具體樣態(tài)應該有另一種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的說明。而在社會轉型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當下,罪刑關系應取但不是只取寬和性樣態(tài),因為社會的發(fā)展最終是為了人的發(fā)展并體現(xiàn)為人本身的發(fā)展,而人的發(fā)展需要一種寬和的社會環(huán)境包括法治環(huán)境,而寬和的罪刑關系正是寬和的刑事法治環(huán)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罪刑關系只有采取能夠迎合時代發(fā)展需要的相應樣態(tài),罪刑關系才能不斷獲得新生。強調(diào)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并用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來充實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不僅是在肯定和運用罪刑關系,而且是在維系罪刑關系的動態(tài)平衡即罪刑均衡或罪刑相稱,因為在筆者看來,罪刑關系在寬和性之下是一個信息開放,謀求共識,達致均衡的信息系統(tǒng)。在寬和性之下,罪刑關系是一種當事人關系,是一種可合作性關系,是一種可暫緩性關系,因而是一種活性關系或彈性關系,進而是一種超越了預防功能的恢復性關系。因此,罪刑關系是一種功能關系和價值關系,而其功能性與價值性正是其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所滋生的信息開放性所賦予的。由此可見,罪刑關系并非在行為成立犯罪之時便即刻成立且“一錘定音”的刑事法律關系,而是在行為成立犯罪之后的時間延長線上,在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的協(xié)同運作之下,反復、交錯相關信息,以最終達致共識與平衡的刑事法律關系。由此也可見,罪刑關系不僅僅是一種關系,而且也是一種動態(tài)運作的和開放的信息系統(tǒng)。日本著名刑法學家團藤重光曾經(jīng)提出運動刑罰觀,即將萬物流動原理引入刑法學,他認為:“犯罪和刑罰的關系也決不是靜止的、固定不變的現(xiàn)象”[8],并提出在起訴、審判和行刑三個階段給予犯罪人不同待遇的設想,即“我不滿足于對新派的立場和舊派的立場簡單地加以折衷的做法,兩者應該在動的過程得到統(tǒng)一。在面對過去時,應該強調(diào)客觀主義和一般預防,在面向未來時卻應該強調(diào)主觀主義和特殊預防。在犯罪論中前者的色彩濃,在刑罰論中后者的色彩濃。因此,對同一事件,作為公訴方的檢察官的立場,就應該是客觀主義和一般預防主義,作為法官應該是所謂中間立場,而進入行刑階段時,刑務官的立場應該是主觀主義和教育刑主義。”[8]354團藤重光的運動刑罰觀隱含著“運動罪刑關系觀”。只有是運動的,罪刑關系才可以是信息開放的。因此,“運動罪刑關系觀”也可稱為“信息開放罪刑關系觀”。只有是運動的和信息開放的罪刑關系,才有可能是寬和的罪刑關系,而運動的和信息開放的罪刑關系必須先是當事人性的、可合作性的和可暫緩性的罪刑關系。可見,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從根本上牽扯到罪刑關系的品性與格調(diào)。
其次,拓展后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有著深刻的人權意義。一個普遍而明顯的事實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在使“技術理性”盛行起來并大有占主導地位之勢。與此同時,作為“技術理性”的副產(chǎn)品,關注因技術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安全的“目的理性”也“成長”并“壯大”起來。而正是在“技術理性”和作為其副產(chǎn)品的“目的理性”之下,人已經(jīng)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危險之中,這就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道德風險”和“道德缺陷”所在。現(xiàn)代科學技術以一只“萬能”的手影響乃至“主宰”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道德生活領域。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道德風險”和“道德缺陷”在刑法學領域的直接影響便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德國著名刑法學家駱克信的目的論犯罪論體系中的“安全刑法”觀念和雅各布斯純粹規(guī)范論犯罪論體系中的“仇敵刑法”觀念。可想而知,“安全刑法”和“仇敵刑法”容易走向“暴虐刑法”乃至“殺戮刑法”,其輕視和踐踏人權的沖動是難以克制的,正如有學者指出:“‘安全刑法的概念與‘罪責刑法相對,認為刑法的目的不在于對個人的譴責,而在于保證社會的安全。‘安全才是對刑法的最高指引”[25],而“安全刑法在雅各布斯看來仍顯不夠。為了直接維護‘刑罰本身,他提出了更加極端的‘仇敵刑法,認為既然將行為人區(qū)分為‘市民和‘仇敵,則刑法也應當區(qū)分為‘市民刑法與‘仇敵刑法。……而那些‘仇敵已非普通犯罪人,對于這些‘仇敵,不應再發(fā)動刑事訴訟程序來保證他們的訴訟權利,直接以‘戰(zhàn)爭的形式對付即可。”[9]287因此,在“技術理性”盛行的當下乃至日后,強調(diào)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對于抵制“安全刑法”、“仇敵刑法”乃至“暴虐刑法”和“殺戮刑法”,從而保障人權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時代意義。易言之,我們當下重視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問題,并用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來充實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則等于是給“安全刑法”、“仇敵刑法”乃至“連帶刑法”設置了一道障礙,從而等于是給人權構筑了一道屏障,因為罪刑關系寬和性視野的拓展,同時意味著罪刑關系強制性的觀念必然要發(fā)生調(diào)整與更新,因為罪刑關系的寬和性與強制性所構成的是對立統(tǒng)一的辨證關系,而罪刑關系強制性觀念的調(diào)整與更新包括:罪刑關系的強制性只能是一種相對的強制性,或曰接納寬和性的強制性,從而罪刑關系的強制性未必就一定要體現(xiàn)為康德曾主張的等量報應和黑格爾曾主張的等價報應,也未必就一定要體現(xiàn)為貝卡利亞曾主張的刑罰的必定性、刑罰的及時性,即未必體現(xiàn)為“嚴刑峻法”。顯然,只有在罪刑關系的強制性的相對性而非其絕對性之中,刑事訴訟當事人的人權方可獲得最起碼的保障。而牽制罪刑關系的強制性的絕對性的,只能是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并且是用當事人性、可合作性與可暫緩性來充實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
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的人權性即其人道性。有學者強調(diào):“刑罰人道主義是刑法適用的一項基本價值觀,強調(diào)司法寬容、謙抑和慎刑。”[10]顯然,在罪刑關系的寬和性里面,所謂寬容、謙抑和慎刑都有,故其有著厚實的人道性。古人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罪刑關系的寬和性也是一種“惻隱之心”和“辭讓之心”,從而也是一種特別的人道之心。
最后,拓展后的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有著基本的刑事政策意義。罪刑關系的寬和性符合“以柔克剛”的易經(jīng)原理此處的“剛”近者為罪刑關系的強制性,遠者為犯罪人格。,故其寬和性應在社會轉型和風險多元的特殊歷史時期的刑事理念和刑事實踐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和“重用”。可以這么說,人類社會一開始便是關系社會,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便是社會關系的越發(fā)多樣化、復雜化和由其所導致的越發(fā)沖突化與緊張化。作為人類社會關系的一種規(guī)范性縮影,同時也是作為一種極端的人類社會關系,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或寬和化能夠“平抑”社會發(fā)展中社會關系的沖突化與緊張化,從而能夠助益于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由此可見,在社會轉型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中被叫得越來越響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終離不開罪刑關系的相關特性包括其寬和性的“本源性”和“依托性”說明。有學者指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質(zhì)就是寬和化,寬和化又為刑罰人道主義的勃興提供了基本注腳。”[10]96那么,罪刑關系的寬和性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落實與體現(xiàn)。《寬容原則宣言》宣稱:“寬容是個人、群體和國家所應采取的態(tài)度。”而有學者指出:“包括寬容在內(nèi)的人道是一種規(guī)則貫徹過程的態(tài)度,是一種道德責任。”[10]101那么,罪刑關系的寬和性即罪刑關系的寬容性,而罪刑關系的寬容性便是國家、社會乃至被害人個人對犯罪人所應采取的態(tài)度,是罪刑關系的貫徹所應采取的態(tài)度,是刑法的一種道德責任。當這種態(tài)度和責任影響了并滲透到刑事政策中去,所形成和提倡的便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結語雖然犯罪與刑罰是刑法學中的一對基本范疇,但我國刑法學對這對范疇之間的關系即罪刑關系的研究似乎早已陷入了“一潭死水”。然而,任何一個刑法理論問題都可以“老哥新唱”。回應本文開頭,對罪刑關系的研究若想走向全面和深入,則必須切中時代發(fā)展的脈搏,并在刑事一體化的視野中緊密聯(lián)系刑事司法理念的更新發(fā)展。一種理論的偉大不在于是否正確,而在于是否能被繞得過去。在筆者看來,至少到目前為止,刑事法學領域的新動向和新發(fā)展包括刑事和解,乃至以后可能也要成為熱門話題的辯訴交易,最終都繞不開罪刑關系,亦即罪刑關系有著我們目前能夠想見到的“理論輻射力”。具言之,無論是特殊群體的刑事實踐(包括少年立法、少年司法,也包括老年立法和老年司法),還是方興未艾的刑事和解,還是可預期的辯訴交易,都可憑借罪刑關系的寬和性而得到解釋與獲得支持。由此,筆者要強調(diào)的是,法學理論包括刑法學理論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可能最忌諱以新概念、新范疇和新命題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冒進”,而準確切中時代發(fā)展的脈搏和緊密聯(lián)系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而對基礎理論進行“生發(fā)”或許是最為穩(wěn)妥的途徑。或可這樣說,能夠對新的實踐動向擦肩而過并在前面引領的“舊理論”或許比以新概念、新范疇和新命題面目出現(xiàn)的“新理論”更有生命力,因為這樣的“舊理論”實質(zhì)上是一種“元理論”。罪刑關系理論或許正是這樣的一種“元理論”,因為犯罪與刑罰是刑事法學的一對“元范疇”,而罪刑關系便是一種“元關系”。我們可以熱衷于刑事和解,我們也可以再憧憬一下那似乎可預期的辯訴交易,但我們不要以為罪刑關系與我們漸行漸遠,而事實上罪刑關系一直是刑事法理論的一個制高點。如果說我們感覺不到這一點,那只能說明活躍在我們眼前的理論與實踐更是在其“高瞻遠矚”之下。罪刑關系似乎是一條“紅線”始終貫徹著刑事理念和刑事實踐的發(fā)展變化全過程。 JS
參考文獻:
[1]馬榮春.罪刑關系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69.
[2]陳瑞華.論法學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71-172.
[3]馬榮春.從恢復性刑法司法到辯訴交易[J].揚州大學學報,2012,(3):36.
[4]張智輝.辯訴交易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9:2.
[5]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2.
[6]羅伯斯庇爾.革命法制與批判[M].趙涵輿,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78.
[7]姜敏.對貝卡利亞刑法思想的傳承與超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10.
[8]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353.
[9]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285.
[10]孫萬懷.罪刑關系法定化困境與人道主義補足[J].政法論壇,2012,(1):104.
The Current Expansion and Reaffirmation of Tolerance and
Kin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MA Rongchun
(Law Schoo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As a kind of special characteristic, tolerance and kin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should be expanded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integration. If it is related to the newest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concept and practice, it should include involvement, collaboration and respite, which supports and enhances tolerance and kin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through mutual infilt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olerance and kin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substantiated in involvement, collaboration and respite is the confirmation of such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ignificance of not only human rights but also criminal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a commanding height of criminal law theory.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tolerance and kindness; involvement; collaboration; respite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2014年4月第16卷 第2期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pr.,2014Vol16 No.2 法學論壇
文章編號:1008-4355(2014)02-00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