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暗面:新媒介的“科學危機”
○ 齊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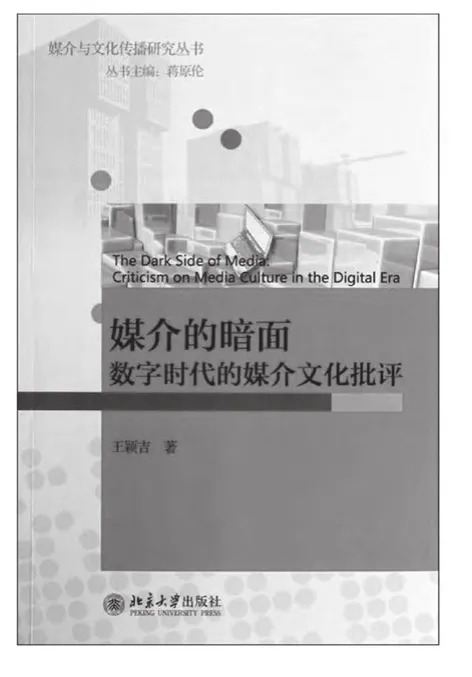
《媒介的暗面:數字時代的媒介文化批評》王穎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版50.00元
胡塞爾在其學術生涯晚期,曾經對歐洲的科學危機作出這樣一番論述:近代歐洲的危機就在于,科學的客觀主義范式盛行,科學只關心技術問題,卻不再反思自己的現世基礎,變成了某種與生活無關的觀念物,人們通過這些觀念物將世界規定為某種范式,一切都要以這種范式為基礎進行思考,個體的主體性因此遭到破壞。思慮至此,胡塞爾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觀念,提倡人們直面所在的現實世界,這與近來出版的《媒介的暗面:數字時代的媒介文化批評》中提到的觀點不謀而合。
作者王穎吉在該書第二章談到,新媒介在帶來某些方面的明顯進步的同時,總是伴隨著人類文化在某些方面的退化。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媒介即訊息”,媒介總是向人們傳遞著某種信息,包含著媒介自身的價值取向,但媒介的這種影響是人們難以察覺到的。新媒介的危險也正在于此,它看似中立無害,使用某種“障眼法”使人們只看到它美好的那一面,卻忽略了它的種種弊端。但是,正所謂“福禍相依”,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其兩面性。作者舉了三個例子說明新媒介帶來的“福”與“禍”:
便利與麻煩、高效與低效。或許有人會好奇,新媒介帶來的高效與便利有目共睹,所謂的麻煩與低效從何而來呢?毫無疑問,新媒介確實增加了人們工作、學習的效率,尤其是從有紙辦公到無紙辦公的飛躍,大大節省了人們的時間。然而,人們節省下來的時間又用來做什么呢?實際上,還是用來勞作。被節省下來的時間沒有用來進行生命存在意義上的休整,而是被用來追求更高的產量。這是因為,我們必須適應技術更新帶來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快速變化,并且技術為我們重新構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總是僅僅符合技術演化邏輯的。新媒介技術的高效率反而造成了生命存在意義上的低效率。
溝通與隔絕。書中提到了兩種關系的演變:首先是親密關系,比如家庭和婚姻,人際關系復雜化帶來的猜忌與嫌隙、媒介非常態的倫理和價值呈現使親密關系變得淡薄;其次,借用里斯曼的術語,人們的自我意識、即基于本能或者感性經驗的自我認知增強,但其自主性、即一種比較成熟的理性自我控制和調節能力卻下降、甚至消失了,這導致新媒體人群深深陷于一種孤獨之中——既明確的察覺到自我的存在,卻無法與人群締結和諧的關系。
自由與控制。新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確實為網民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它使信息可以更廣泛地傳播,一些以往不便發布、不能發布的信息得到了“公之于眾”的機會,而貪腐等負面消息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樣的情況等于所受控制的減少嗎?答案是否定的。互聯網在為公民實現民主監督提供便利的同時,實際上也把網民自己放置在了同樣的監控下——普通網民的一舉一動同樣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下。況且,正如作者所說,真正的自由應該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其核心要點尤其是指對于自己的某些“自由”的適度放棄和犧牲,沒有這樣的利他主義精神的自由永遠都不會變成真正的自由,以技術為手段對他人進行控制的做法是與真正的自由背道而馳的。在新媒體環境下,人們彼此監控,產生自由的幻想,卻終將被互聯網所桎梏。
總之,新媒介和它固有的價值取向不僅讓我們選擇了新的生活方式,并且還向我們灌輸了另一種思考的方式。假如誰不按照新媒體的方式生活、思考,比如反對無紙辦公或聲稱無紙辦公是有害生活的,那這個人一定會被視為頑固或者奇怪的人。新媒介和科學的客觀主義范式一樣,都讓人們以某種公式化的思維思考事物,如果有什么東西不符合這個公式,那一定是這個東西出了什么問題。
這樣一來,我們實際上就脫離了自己身處的現實世界。舉例來說,在新媒介環境下,人們可以輕易地接觸到西方普世價值觀,很大一部分人還會接受它,哪怕其中有某些觀點是與我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現狀格格不入的。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我們都知道,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一切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在思考、生活的時候,也應當以我們的生活世界為出發點,而不是盲目地生搬硬套某種觀點,更不是不加反思隨波逐流。要想使新媒體多利少害,也必須從生活世界出發對其進行反思。
那么,這種反思該如何進行呢?
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傳統的力量,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學習。這是因為,正是傳統構建了我們生活的家園,構建了我們目前的社會狀態。錢穆先生曾經說:“欲考較一國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層首當注意其‘學術’,下層則當注意其‘風俗’。學術為文化導先路……風俗為文化墊深基。”就學術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最有影響的恐怕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推崇“仁愛”的君子之道,道家則推崇的是“有道無為”的豁達境界。不難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一大共同點就在于,主張修身而不損人,都崇尚一種個人和社會和諧安定的狀態,只不過儒家的和諧更為世俗,而道家的和諧更為飄逸。這似乎和我們現在的主流價值觀正好相悖,舉例來說,老子提倡“小國寡民”,認為理想的傳播應當是有限度的,而反對大規模的社會聯結,人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然而如果誰在當下的生活中放棄使用任何新媒介,那這個人就無法融入社會了,哪怕他只是希望逃避一種聲色犬馬的生活。現在的我們,比起自身的德行和社會的穩定,追求的似乎更是利益的最大化和欲望的滿足。我們已經習慣了媒介之中展現的那一套非常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新媒介中,常態化的生活被看做是不值得展現的,而被展現的東西越特殊越好,久而久之,人們就會更多地尋求刺激和“變態”,視傳統、平靜、安寧的生活為“異端”。
其次,要在生活世界里反思,還要關注個體的主體性。雖然傳統在我們產生之前就對我們的生活世界產生了作用,但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的所作所為總會對它產生影響,因此生活世界也是由我們共同構造的。每個人都是世界的創造者,因此每個人都值得尊重。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尊重不僅僅是個人權利的尊重,更應當是生命意義上的尊重。所謂生命意義上的尊重,即是對生命發展過程的尊重,換言之,我們需要把人看做是能夠不斷進步的人,看做是不斷健全的人。舉例來說,就“理性”方面,我們要想尊重人就必須把人看作是能夠正確認識世界的主體,他們能夠對世界進行思考的同時也能夠對自己進行思考,從而不斷改正自己,而這些思考正源于他們生活的實踐經驗。如此來看,新媒介對人們思想模式的限制確然使人們遠離了生活世界和自我反思,是對人主體性的破壞。
總而言之,新媒介固然是技術的進步,但其帶來的種種問題卻不容忽視。無論是新媒介還是新媒介上的內容,我們在接觸時都需要警惕起來,保持一種清醒的態度,回歸反思,回歸主體,回歸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