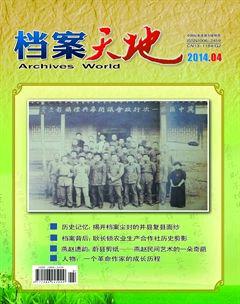蔡鍔病死探究
蔡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也是我的老鄉。如今在邵陽市郊區有一個蔡鍔鄉,我是他隔壁的隔壁鄉的。蔡鍔16歲遠渡日本求學,始學經濟,立志實業救國。一年后回來參加唐才成領導的自立軍起義,起義失敗后又走日本,投筆從戎入日本陸軍成誠學校,后入日本陸軍軍官學校,21歲時以全校第二名畢業。29歲領導云南重九起義,光復云南。33歲率領護國軍將士“再造共和”,34歲為四川督軍。蔡先生之成在此我就不多說了,只不過先生之死,確為我中華之一大損失也,此乃絕對爾。其在人生的最高峰啞然去世,不僅在當時,就算在今日也讓人叩足嘆,仰天長嘆先生英年早逝。
先生死于1916年11月8日,其在1915年底即已發病。其在1915年11月22日呈袁世凱文中有,“自今年入秋,復覺脾胃不舒,飲食減少,時作咳嗽,也不成眠。近復感受秋燥,虛火上炎,以致喉痛失音,發熱盜汗,諸癥并作”。有人或說這是先生為了迷惑袁世凱使其批準其休假三個月到日本就醫的謀計,其實不然。先生是真的病了,這可以從他自己及好友的記述中證明。如其在1916年6月28日致梁啟超的電文中有,“鍔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無療治之余裕,念已成頑性,非就專門醫院速為調治似難奏效”。1916年4月29致潘蕙英函(潘蕙英為蔡鍔妻子)中有,“此病起自去冬,因國事奔馳,遷延未治,遂至纏綿,其來也漸,則醫治亦難急切奏效也”。先生具體起病原因又見蔣百里的《蔡公行狀略》“一日深秋,早起渡南海,欲疾風而喉痛劇,遂病”。這里所說的南海,應該是中南海的南海,而不是南中國海。這段話的真偽,無法考之,有可能為蔣百里杜撰,但也可能是蔡鍔和蔣百里聊天通信時說起過,依蔣百里中國近代軍神的名氣和他與蔡鍔的好友關系,這還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咳嗽、失音、飲食減少、腫痛、痰多,發病一年即死。當時的一般記錄是喉疾之死,但具體死因可能是由于當時的醫療水平及信息所限,也有可能是喉癌所致。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說是傳染病(即喉結核),見于1916年11月份石陶鈞致張孝準函:“松坡系傳染病,火車船運載均其不便,且有損國體,請運動政府用兵船來接,如何?”石陶鈞是當時陪同松坡在日本治病的好友,他的話有一定的可信性,但也有可能是為了讓政府派船來接的托詞。根據當時日本的醫療水平來看,也不見得能查出松坡的具體病因。但到底是喉結核還是喉癌?這兩個病的癥狀確實差不多,如能找到1916年日本福岡醫院的病歷記錄就知道了,不過其實這都是悲劇。
先生病情最重的時候也是其成就最大之時,當時先生帶著有病之體,輾轉到云南發起護國運動,開始時帶領2000余云南護國軍將士進攻袁世凱的爪牙陳宦的四川,于3萬北洋軍隊戮戰瀘州、納溪三月有余。雖然沒有徹底擊潰北洋軍占領瀘州,但使得北洋軍最精銳的第7師8師龜縮于城內不敢出擊。即便沒被擊潰,但也可說是被打殘了。在此情景下,廣西、廣東、福建、江西、湖南、黑龍江等省才敢陸續宣布獨立,脫離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使得袁世凱被迫放棄帝制,后又羞愧致死。先生的病也是在納溪與袁軍作戰時勞累過度,環境艱難,心力憔悴無暇療治疾病而致病情越發厲害,這可從先生的電文中查得。先生在1916年3月25日致潘蕙英(潘蕙英是蔡鍔的妻子)函中有“予近來身體健適,第喉病尚未全愈。”,這說明先生的病還沒好。又見4月29日致潘蕙英的函中有“予近月來頗為病所苦,兩星期內喉病加劇,至不能發音,每至夜中,喉間癢痛,隨而大咳”,從這可以得知先生的病已很嚴重。又見5月16日致潘蕙英函中所說,“予以喉病加劇,暫回永寧調養”。5月26號致潘蕙英函中有“予喉病忽松忽劇,自覺體質不如前數年之健”。這段時間先生的病情可能加重了很多,已不能在前線指揮,回到了后方修養(其實永寧離前線也不過幾十公里),一段時間后,可能病情又有所好轉,在5月30日致唐繼堯等電文中有“鍔喉病稍痊,痛楚已除,但發音尚低耳”。但沒好多久,從六月十幾號開始,病情一直加劇,見6月21致梁啟超電文有“喉病日劇,殊痛楚,幾于不能發音”。6月26日致梁啟超電“鍔喉中痛楚,入夜頗劇,就醫診治,當可望痊”。先生病情加重后,一直想東渡日本好好養病,因為他自己也清楚病情很嚴重了,也感到非常痛苦,但無耐混亂的中國情形讓他無法脫身不管,這從他很多的電文中可以看出來。如在6月21致梁啟超中有“旬日來,力求脫卸,東渡養疴,而未能韌然撒手”。六月二十幾日梁啟超為蔡鍔從上海聘請了一位德國醫生阿密思到四川瀘州給蔡鍔治療。七月二日德國醫生對蔡鍔進行了治療,但效果并不好,治療后病情比原先更加嚴重,見7月5日致梁啟超文中有“德醫阿密思到瀘后,連日診治,砭藥兼施,日來不惟無效,反覺痛楚加劇,食量頓減”。但直到此時蔡鍔也沒有真正認識到這個疾病的嚴重危險性,見7月11日致梁啟超文中有“自度癥候已由慢性而成頑固性,若再荏苒不治,縱無性命之虞,亦必成啞廢”。7月28號致劉顯世文有“第之思退,一以償夙愿,一以病軀難勝繁劇,亟需趁時療治,避免啞廢”。此時先生認為最多可能也就是變啞巴,并沒有意識到了生命危險。即便認識到了,也不一定能痊愈,但如果早日到醫院去好好療養,當不至于死得那么快。可惜四川一片混亂,中國一片混亂,這讓先生不得不勉強留下來收拾局面。見7月12日致梁啟超文“鍔病必須轉地療養,已佚電辭職”。此時先生已被眾人推為四川督軍,但此時,先生已病入膏肓,半個月來“靜居舟中”調養身體,見7月20號致梁啟超文。蔡鍔在萬辭不就的情況下,拖著嚴重生病的身體于7月29日到達成都,但他已不能承擔繁重的工作。半個月后,在將事情稍加安排妥當之后,蔡鍔才請假3個月到上海或日本就醫,九月初到達上海。不知道是在當時的哪家醫院,但療治幾日,效果并不好,且醫療條件有限。幾日后蔡鍔即東渡日本求醫,九月十四號到達日本福岡醫院。見于9月22號致黎元洪電文中有“自到大學醫院后,費久保,早稻兩位博士醫術精細,治療懇切,調養適宜,當可速痊”,但先進的日本醫療水平也不能挽回蔡鍔的生命,不到兩個月后,就不治而亡。誠可嘆也。
蔡鍔去世時的詳細情況,可見于石陶鈞致張孝準函中有“初五、初六即呈險癥,乃六日晚行注射后,初七日精神頓爽,并自謂前數日頗險,今日大快矣。夜間猶囑寫信上海買杏仁露。十時傾,氣喘母直視,注射后稍安息。至八日午前一時,又因痰塞,喉斷呼吸,繼痰出,有呼吸,已極微弱。行人工呼吸法。靜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囑書遺電時,精神尚一絲不亂也,無一語及家事”。在蔣百里的蔡公行狀略里也有記載:“十一月四日,食眾人以瓜,且曰各人在,其一分也。語詳遺電中。七日之早,望飛機,猶欣欣然有喜色,曰:今日愈矣。傍晚,命索食餌于湘中,十時,氣益促。八日午前二時×”。石陶鈞和蔣百里都是當時在蔡鍔身邊的人,張孝準和蔣百里及蔡鍔都是同級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這兩段話應該都是可信的。先生在十一月初五初六,病情就出現了很危險的情況,初六晚上打吊水或者也可能是打針了,具體打什么針那可能還得看100年前日本福岡醫院的資料了。但初七可能感覺好了一點,早上看了飛機“欣欣然有喜色”“精神頓爽”,晚上還寫信給上海的朋友買杏仁露。但在蔣百里的文中,卻說“索食于湘中”想吃我們湖南的什么食物,可能是家鄉邵陽的豬血丸子,又或者是長沙的臭豆腐。這也無從查證了,他臨死之時,到底是想吃上海的杏仁露呢,還是家鄉的特產?但我想初七可能是回光反照。八日上午,情況真是不好了,先是被痰堵住了喉管,通后呼吸已極微弱,行人工呼吸法,也未能得救,死于午前一時,大概也就是12點左右。
附錄:蔡鍔遺電,1916年至12月8號至國會和黎元洪等,鍔病恐不起,謹口授隨員等遺電陳:(一)愿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爭權利,愿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 (三)此次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墾殤羅督軍、戴省長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臨電哀鳴,伏乞慈鑒。四川督軍兼省長蔡鍔叩。庚。
蔡鍔于民國六年4月12日國葬于長沙岳麓山,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第一個享受國葬的人物。湖南還有一個名人,黃興。也是死于當年,就在蔡鍔死之前的四天,也就是1916年11月4號黃興在上海去世,也是病死,不過是胃病,但也有說法是胃穿孔和胃出血。幾天之間,湖南失去兩位如此重量級的人物,不能不說是湖南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不過有意思的是,雖然黃興先于蔡鍔4天去世,但并沒有享受國葬,可見黃興在當時的社會影響確實不如蔡鍔。如今在長沙的中心城區有兩條路一條路被命名為蔡鍔路,一條路叫黃興路,兩條路緊挨著并排著呈南北走向,黃興路端塑黃興著西裝提衣跨立像,蔡鍔路端塑蔡鍔戎裝騎馬挎刀指揮塑。
作者簡介:姚鵬,筆名:耕夫,湖南邵陽人,30歲,從事文史研究。02年至今,在《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等多家知名報刊雜志發表百余篇散文、雜文、影評、書評等各類文章,主要是文史類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