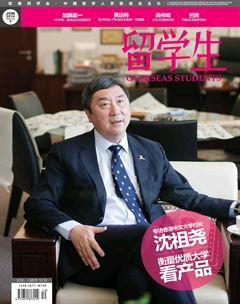出國去,了解中國
《留學生》雜志記者采訪的留學生并不算少。起初,我們聚焦于那些剛剛改革開放初期出國的學生,他們會談自己第一眼看到外國景觀時內心的震撼,他們痛感國家的落后,他們苦學,回國后發揮聰明才智,然后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隨著采訪人物的增多,我們發現上面的思路其實有可補充之處。比如說日本問題專家吳偉明在回答《留學生》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是喜歡中國才去念日本歷史。”為什么呢?他說:“當時在中國是看不清楚中國的,我希望透過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日本對中國很了解,文化上有接近性,它對中國的看法也不一樣,雖然觀點不一定對,但多一個參照物。我真正的興趣是日本和中國文化的關系。”
這個很新奇的看法其實宋代的蘇軾早就說過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歸國的留學生往往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在發達國家學到了某些先進理念或技能之后,在國內未必能夠馬上實行。
通常的想法是改變國情來適應新技術,但漸漸我們發現,中國與西方是不同的。這些“不同”的地方,以往并沒有得到準確的認識和理解。有時真的需要留學生出國開了眼界之后,才能對這些“不同”進行恰當的判斷。
然而,真正的開眼界談何容易?弄清楚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就不簡單。比如說,美國人一度用“傅滿洲”和“陳查理”這兩種人物看待中國人,而中國人對這兩個人物完全不了解。榮獲2014年度美國古根海姆獎的作家黃運特寫了新書《陳查理傳奇:一個中國偵探在美國》,評論認為這是“中國人看美國人看中國人”,在全球化的今天,認識、理解自己或對方,都不是一件已經完成了的事情。黃運特在接受《留學生》雜志采訪的時候說:“你以為陳查理是中國人的代表,但他其實是美國人創作的中國人,所以這個相互之間的態度一直是流動的。”
這種“流動”的確是“相互”的。曾經名噪一時的北大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以他日本學生會會長的身份,俊朗的外形,流利的漢語一度成為中國媒體的寵兒。但其實年僅18歲的加藤嘉一來到中國時幾乎一無所有。沒有錢,沒有人脈,不會一句中文。而他面對的第一位的問題是:生存。他回憶那段時期的生活時對《留學生》記者說:“到北大留學是一個好的選擇,我們全家都對此有共識,因為在中國留學能更省錢。”
白巖松曾這樣評價他:“現在,我們就可以夸獎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價值。”加藤嘉一看到這句話后“全身都發抖了。我感謝他對我有這樣的評論。我知道,中國對我的評論很大程度上,過于抬高了我。”
留學,的確能加深留學生對中國的理解。只有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了中國,才能更好地完善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