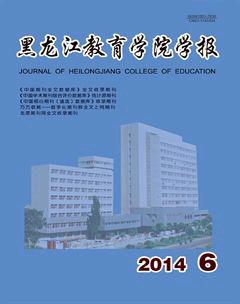零度的誘惑
葉玉潔
摘 要:“零度寫作”是羅蘭·巴爾特在其著作《寫作的零度》一書中提出的著名文藝觀點。“零度寫作”是指一種直陳式的白色寫作,或者說是一種非語式寫作、新聞式寫作。法國新小說代表者之一阿蘭·羅伯—格里耶的小說突破了當時普遍的寫作模式,他和巴爾特同屬于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的實踐者,一個是以文藝理論的方式深入,一個是從寫作實踐出發。基于此,從文本細讀的角度來分析《窺視者》中的“零度寫作”方式,以期使讀者對這一寫作方式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關鍵詞:零度寫作;直陳式;白色;無感情;《窺視者》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7836(2014)06-0139-03
一、“零度寫作”之理論源流
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一書中提出“零度寫作”的文藝觀。對于此觀點的提出,巴爾特有嚴密的邏輯思維推理過程,他首先從“什么是寫作”入手,繼而步入到“政治的寫作”、“小說的寫作”、“資產階級寫作”,否認了布爾喬亞的工具寫作方式,然后,在“寫作與沉默”一節中正式提出“零度寫作”的觀點,繼而深入到總結性的言語:寫作是語言的烏托邦。
“零度寫作”:“比較來說,零度的寫作根本上是一種直陳式寫作,或者說,非語式的寫作。可以正確地說,就是一種新聞式寫作,如果說新聞寫作一般來說未發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傷的形式)的話。……于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毫不動心的寫作,或者說一種純潔的寫作。”[1]
在這里,巴爾特提出的“零度寫作”是這樣一種直陳式的、新聞式的、毫不動心的、白色的寫作。這種“零度”是相對而言的:“假設或命令句型,是特別的所指形式,且為不同意義,在這里,所指就是我的意愿或者我的要求。這就是為什么相對于假設或命令句型,一些語言學家將直述語定義為零度狀態或程度。”這種寫作方式是巴爾特為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工具性寫作方式,支持當時流行的新批評的文藝觀點而提出的。他從語言學的角度發現了第三項,即在虛擬式和命令式之間的一種非語式的直陳方式,也就是一種中性的或者零度的方式。巴爾特認為,真正的文學活動應該是文學自身的語言活動,這一點,巴爾特深受索緒爾的影響,將文學研究的視角轉向了語言學,進而突破了界限,發展到符號學的領域,而這些才是真正關乎文學自身的東西。因此,巴爾特提出的“零度寫作”是一種關于語言的寫作方式,一種在文學內部的寫作方式,這才是將寫作轉回到了文學內部,是真正的寫作。
巴爾特“零度寫作”的提出反對了當時布爾喬亞的寫作方式,對新批評給予了有力的支持。誠然,巴爾特的“零度寫作”具有開創性的價值,但是也存在很明顯的局限性,即真正的“零度寫作”并不存在,無風格的寫作方式在定型之后也會成為一種風格,寫作的“零度”只是一種傾向,將寫作中的情感降至冰點。
二、“零度寫作”之于文本
羅伯—格里耶在其代表作《窺視者》這部作品中實踐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即將人物縮到寫作的背后,讓客觀的環境和行為登場,自行“言說”。這種寫作方式一直成為了他的寫作風格,作為法國新小說的代表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一直踐行著這種寫作方式,并影響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的寫作。文本敘述了一個旅行推銷員回到以前居住過的小島上推銷手表,并殺害行為不端的牧羊女雅克蓮,最后離開小島,逍遙法外的故事。書名《窺視者》,系指窺見馬弟雅思犯罪,卻又不告發的于連,而且還指向了馬弟雅思在兜售手表過程中對別人生活的窺視。
(一)直陳式的環境描寫
《窺視者》一書的顯著特點就是活動的人物退居到幕后,場景和事件成為了主體,自行前進,組建文本,這正是“零度寫作”的核心觀念的體現,即直陳式的寫作。在文本中,這種場景的敘述可以各自組建起許多的畫面,這些畫面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深層結構上的連接,只有從文本的整體上才能得到把握。
在小說的一開篇,就有這樣的場景:
一排排固定的、平行的、緊張而且幾乎帶點焦急的視線,正在超過——或者說竭力企圖超過——那一片海間隔在它們和它們的目標之間的逐漸縮小的空間,旅客們一個挨一個,以同樣的姿勢昂著頭。輪船毫無聲息地噴出最后一股煙;這股煙很濃,在人們的頭上構成蘑菇狀的羽飾,可是馬上就消散了[2]4。
在這個開篇的場景中,構建了一副圖畫,即輪船上的眾生相。在羅伯—格里耶這里,場景的描繪并不是作為人物行為的襯托,而是事件的主角,人物及其行為只是填充在這個框架之中的。在整個文本中,幾乎通篇都是如上述場景一樣的描寫,只是變換了場景的客觀內容而已:
紀念碑的周圍有很高的鐵欄桿圍著,這鐵欄桿是由許多等距離的直線型垂直鐵條構成的一個圓圈;欄桿的周圍還有長方形的石板鋪成的人行道,和整個雕像合成一個整體。他沿著鐵欄走的時候,發現腳下的石板鋪道上出現了那個石頭雕像的影子。這影子被投射得變了樣子,已經難以辨認,但是線條十分清晰;和旁邊布滿灰塵的路面比較,影子的顏色十分深黑,而且輪廓那么鮮明,使得他產生了錯踏在一個結實的物體上的感覺。他本能地把腳一縮,避開了當前的障礙物[2]18。
在這一系列的場景描繪中,表面上是主人公馬弟雅思的行為的前行引領著讀者的目光,其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用一個攝像機拍攝,隨著鏡頭的切換,展現出不同的場景,在這些顯現出來的場景中,是一種直接的錄入,是一種紀錄片式的播放,在寫作之中也就是一種直陳式寫作。無論是碼頭的諸多物象,還是廣場上的雕像、欄桿、石板路、影子等,都是一種直陳式的描寫,這些場景以其原有的特點和色彩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和判斷。在巴爾特看來,正是這種直陳式的寫作才能夠達到一種客觀,而不是現實主義創作那樣充斥著主觀的價值判斷和說教功能。
(二)行動的“白色”寫作
《窺視者》中的“零度寫作”不僅體現在大量的場景的直陳式描寫中,還體現在了人物行動的描寫之中。在這里,“零度”的行動是主人公在無意識之中進行的,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人物行動的無邏輯,按照平常的思維方式來看,主人公的行為是荒謬的,不可理喻的;但是,用一種反理性的方式來思考,理性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那又何來正常可言。因此,在這里,這種人物行為的白色寫作也是一種達到真實的方式。不管是人物行動的外部行為還是人物的內心活動,都成為了一種中性的寫作。在作者這里,即這樣一種寫作方式。
1.人物外部行動的中性寫作
在文本中,人物外部行動的中性寫作有很多的體現,有動態的外部行為、靜態的外部行為和人物的對話等方面。
在動態的外部行為中,主要是馬弟雅思回到家鄉兜售手表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情形,這里取其一加以說明:
馬弟雅思喝光了那杯苦艾酒。他忽然覺得夾在兩腿間的小手提箱沒有了,他低頭一看,小皮箱不見了。他把手伸進短襖的口袋,想把手指上的油污指在那卷小繩子上,同時抬頭來張望著旅行推銷員。……于是他轉過來對著那個胖女人,或者那個女人,或者那個姑娘,或者那個年輕的侍女,然后放下小皮箱,以便拿起那只小箱子,這時那個水手和那個漁民偷偷地擠進,混進,插進了馬弟雅思和旅行推銷員之間[2]88……
這個外部的行為是主人公馬弟雅思在兜售手表的過程中走進一家酒吧的情形:他喝著苦艾酒,突然間的感覺和手插進短襖的口袋以及女店主的一系列反映都是很隨意的,在這里,他們的行為不是為了某一個重要的事件來進行的,也不是為了下一個行為作前后的連接,這是一個隨意,也是突兀的行為,出現在這里只是為了說明主人公馬弟雅思進入了這一個酒吧,有這樣一個毫無重要性的行為。在敘事方式上,也是一種毫不動心的敘述,一種中性的寫作。
endprint
另一個外部行為的中性寫作體現為一種對靜態的外部行為的描寫,這種“靜態”是以一種動態的筆觸來描畫的,主要體現在一些對畫面的描述之中:
那幅畫是用強烈的色彩畫成的廣告畫,畫著一個魁梧高大的漢子,身穿文藝復興時代的服裝,抓住一個穿著白色長睡袍的年輕女子;他的一只手把她的兩手腕緊緊地抓住,勒在她的背后,另一只手扼住她的咽喉。她的上身和臉稍向后傾,盡力想從劊子手的掌握中掙扎脫身,她的修長的金發一直垂到地上。后面的背景是一張寬大的有床柱的床,床上鋪著紅色的被單[2]19。
在此,這個外部行為的靜態描寫中,也是一種中性的寫作,在這里,主要是對一幅畫的描寫,這幅靜態的畫采用的是一種動態的描寫方式:“抓”、“勒”、“扼”、“后傾”、“掙扎”、“垂”這幾個動詞表現的是一種動態的行為,即,一個女子被殺害的過程和情境,但跳出這種動作的描述,這是一幅靜態的畫面。
在此,這是一個對靜態畫面的動態行為的靜態描寫。沒有任何的價值判斷,這動態和靜態的交織使行為的意義自動顯現。這也預示著小說后文中主人公馬弟雅思謀殺雅克蓮的行為動作。
還有一個外部行為的中性描寫體現在人物的對話之中:
“船主人是我的一個朋友,”店主人說,“他愿意為您效勞。”
“謝謝您。可是我買的來往票仍然有效,我不愿意把它浪費掉。”
……
“別費心了,孩子,”店主人對他說,“人家不要乘你的破船。”
……
“我并不過分急于離開這兒,您知道。”他說。
“我倒以為您急于離開這兒。”店主人說[2]96。
按常理看來,這段對話中應該體現馬弟雅思被揭發后的驚惶,但在這個對話場景中,文字記錄的只是對話人說出的言語,簡單的對話和沒有深意的推理,不會有深刻的意蘊推理,讓讀者自己去揣度文本的意義。也指示出馬弟雅思在犯罪之后的心理狀況的變化。在這里,其實是可以看出主人公的一種心理變化的,但羅伯—格里耶將其處理成了一種盡量客觀的表現方式。
2.無感情的人物內心活動
人物活動的白色寫作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在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中的無感情。人物的外部行為必然要帶著心理活動的變化,心理活動的變化在一般情況下是充滿了感情色彩和濃烈的情緒的,但在阿蘭·羅伯—格里耶這里,人物的內心活動卻是沒有感情色彩的,但是這種無感情不是純粹的,只是他將這種感情的涌動程度降至了最低點。盡力排除了作者的主觀情感對于文本的強加。在文本中:
仔細回想起來,他懷疑自己聽到的是否只是含糊不清的呻吟聲,現在他相信聽到的是可以分辨的說話,雖然他已經記不起是些什么話了。這喊聲是悅耳的,而且不含有任何憂愁;從喊聲的音色判斷,發出喊聲的人大概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女人,或者是一個女孩子。她靠著一根支撐著甲板一角的鐵柱站著;雙手緊握在一起,操在背后腰眼上,兩腿僵直,稍稍分開,腦袋倚在柱子上。她的兩只大眼睛睜得十分大(而這時所有的乘客因為陽光開始照射,都或多或少地眨著眼皮),她繼續向前直視,態度就像剛才她凝視他的眼睛時那么平靜[2]12。
這個片段的內心活動是馬弟雅思在兜售手表的過程中路過一個房屋,聽到的聲音,然后在他的腦海中產生的畫面和想象。關于喊聲的“悅耳”,還有他判斷是一個女孩子,以及之后的各種動作都是他在聽到呻吟聲之后產生的內心活動,也預示著后來馬弟雅思的殺害行為。但在這里,他沒有驚奇,沒有害怕,沒有興奮,只是將這種想象的畫面刻畫出來了,沒有情感的過度描寫。
(三)敘事語式的“零度”
《窺視者》中的“零度寫作”不僅僅體現在以上兩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在敘事方法之上的“零度”,稱為敘事語式上的“零度”。敘事語式是指敘事者向我們陳述、描寫的方式。敘事語式上的零度在這個文本中主要體現為一種倒敘的敘述方式和片段式的組合方式,這種打亂邏輯的寫作方式能將文本組建成一個新的文本,而意義則在這種片段之中具有了張力[3]。
從倒敘這個方面來看,文本中有諸多的體現,比較顯著的一點便是:馬弟雅思將雅克蓮殺害的過程在文本中并沒有直接敘述,而是在后來雅克蓮的男友于連指出馬弟雅思撒謊后,他與于連的辯論對話中體現出來的,于連一直提出馬弟雅思犯罪留下的糖紙和衣服,而馬弟雅思則用其他的諸多可能來搪塞。在這樣的敘述中,將之前的犯罪行為置于之后的對對話的敘述之中。
另一個在敘事語式上的“零度”表現為片段式的組合方式,這在文本中有很多。馬弟雅思回到那個島上兜售手表的過程中,他的所見所聞是沒有邏輯聯系的,而且這些見聞所引發的他的心理活動則是更加瑣碎。他經常聽到一些聲音,產生許多的幻象和幻覺,其實這些都不是真實的,是他的思維活動,但敘述者在敘述之中是將這種片段作為一種看作真實來寫作的,就是為了擺脫時間的連續性所體現出來的主觀性。有多個片段都是關于馬弟雅思的“窺視”行為,他進入到很多家庭之中去兜售手表,敘述者的敘述是以一種鏡頭式的方式來轉換進行文本的寫作的,就可以將事實作為一個個的“塊”進行組建,也就形成了諸多的片段,貫穿在文本之中[4]。
(四)意識形態的零度
最后一個方面是指在意識形態上的“零度”的體現,這是從整個文本來講的。羅蘭·巴爾特在提出“零度寫作”的觀點的時候,就首先指出了反對布爾喬亞的寫作方式,即一種工具性的寫作方式,因為在這種寫作方式之中,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浸染,文本不是關于文學的,而是文學外部的東西。因此巴爾特指出,寫作要“零度”,要關于文學本身的東西,這樣就將文本中的意識形態降至冰點。
在《窺視者》中,這種意識形態的“零度”主要體現在從整體上來觀照的“法律的失效”[5]。在整個小說中,都是一種“反道德”的“窺視”,馬弟雅思兜售手表,進入到各個家庭之中,首先都是以一種“窺視”的態度和目光去觀察事物和人,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方式。在馬弟雅思殺害雅克蓮的時候,于連也“窺視”了他的整個行為過程。但是,在最后,于連沒有揭發馬弟雅思的犯罪行為,馬弟雅思最后乘輪船離開小島,逍遙法外。在這里,法律是完全失效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任何束縛力的。這正是達到了一種意識形態的“零度”。
三、結語
綜上所述,阿蘭·羅伯—戈里耶的《窺視者》這一小說可以說是一部“零度”的小說,從上述的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零度”的傾向。而讀者只有深刻地理解這一寫作方式,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相關的文學作品。
參考文獻:
[1][法]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55-65.
[2][法]阿蘭·羅伯—格里耶.窺視者[M].鄭永慧,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7.
[3][瑞]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61.
[4][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帝國[M].孫乃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94:159.
[5][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24. 2014年6月第33卷第6期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