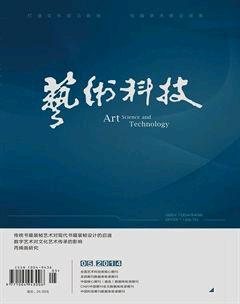“參禪”與“頓悟”
摘 要:禪宗詩性哲學深深地影響著蘇軾的人生態度,也滲透于他的書法實踐和書法美學取向中。蘇軾書論中以禪喻書,寓禪于書,提供給后世的是一種比“尚法”更高妙的學書法則。這種對“通其意”的重視與肯定,既構成宋代尚意書風的主流形態,同時也為后世書風的深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參禪;頓悟;寓禪于書;蘇軾
1 蘇軾禪宗思想之淵源
作為宋代尚意書風的代表,蘇軾的藝術觀一直是書學研究的重點。從其藝術實踐我們不難得知,他的藝術觀受儒、道、禪影響很深,尤其是晚年禪學思想對他的影響更深。這里面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也有蘇軾個人的選擇。
(1)歷史淵源。中國書法美學崇尚“中和”之美,以古典的和諧美為最高審美理想,它要求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等因素樸素而和諧的統一,從而實現書法藝術的審美價值。書法藝術審美領域所追求的自然、率真,它與禪宗主張的“回歸自然”“無意識”觀點有著想通之處,這是書法家對禪宗這種充滿哲學思辨的宗教產生興趣的根本原因。他們依據禪宗思想創作,注重表現“禪宗式”心靈,從而形成特有的“禪式書法”。禪式書法經魏晉南北朝萌芽,逐步形成,到唐代獲得了長足發展,至宋,以蘇軾等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將其繼續發揚光大。
(2)社會背景。北宋是禪宗思想鼎盛發展時期,文人士大夫參禪、論禪成一時之風。蘇軾曾自豪地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據后人考證,時與蘇軾有過交往的禪僧不下百余人。蘇軾不但與禪僧們往來密切,且確實地篤信禪旨,并將這種禪旨與禪思融入藝術創作與藝術理論之中。盡管蘇軾的有關書法的言論多為短句和隨筆,但是我們從中還是可以看到禪學思想在他的書論中的影響。
(3)個人選擇。蘇軾家學淵源,在他幼年時即以接觸佛教。他的故鄉佛教就甚為發達,其父兄都是虔誠的佛教信仰者,蘇軾從小就對佛教耳濡目染。正當躊躇滿志的蘇軾想施展自己人生抱負時,卻卷入北宋統治集團的黨爭中,被貶黃州,他自稱:“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達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地。其原來的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輔以佛道,變了以佛教思想為主導,以儒家思想為輔,“外儒”的一面漸隱,“內釋”的一面凸顯出來。故而,隨緣自適,隨遇而安,曠達超然便成為蘇軾生活態度的基調與主旋律,而構筑這一基調與主旋律的文化基因則是佛家和老莊思想,尤其是禪宗的詩性哲學。
2 禪宗思想在蘇軾書法藝術中的作用與表現
(1)藝術觀。禪學對蘇軾的藝術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蘇軾用禪宗的思想方式對書法藝術作哲學思考。蘇軾書論中提出的“法無定法”的觀點顯然是受禪學“無住”思想的影響,蘇軾在《小篆般若心經贊》一文中說:“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可知,蘇軾視書道如禪道,意重在妙悟。他對李氏小篆的贊揚即說明了這一點。李氏所書小篆表現出 “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的境界,真是進入“忘我”狀態的真實寫照。因此,蘇軾論書,強調創作者的自由閑適的“忘我”心態與藝術精神,不為規矩所范,則是禪宗思想滲入的結果。正是由于對禪宗的參悟,使其書法思想達到如此脫胎換骨,大徹大悟的地步。
(2)學書過程。禪宗分南、北二宗,即頓悟派與漸悟派。蘇軾以南宗為宗,強調頓悟對藝術的重要性。然,我們亦不能否認:“蘇軾的學書過程是經漸悟之后達到了頓悟。反觀蘇軾的學書歷程,從早年的學習“二王”,中年以后學習顏真卿、楊凝式,晚年又學李北海,其后又多廣泛涉獵晉唐其他書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努力革新,繼而形成深厚樸茂的風格。其學生黃庭堅亦將蘇軾書法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蘇軾以禪的思辨,沖破了俗諦,追求“簡淡”“瀟灑”“清遠”,形成了“天真爛漫”的書風,創造了以平淡見斑斕的禪意之美。由此觀之,經過長期的領悟和視野的不斷開闊,此時的蘇軾已達到了頓悟的階段。
(3)書論思想。蘇軾書論中的禪意與禪風,是北宋書法理論與禪宗思想合流的明顯表現。禪宗重視“本心”與“自性”的作用,要求人們追求“梵我合一”的境界。它雖然是一種宗教學說,但在更深的層面上,有藝術創作有著想通之處。受禪宗思想的影響,蘇軾書論中十分重視“個性”與“本心”的表現。蘇軾在《評草書》中說:“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在《石蒼舒醉墨堂》詩中指出:“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受禪宗思想的影響,蘇軾書論中充滿了頓悟式的機鋒妙語,其中的禪風與禪味十分濃厚。蘇軾不僅在書論中寓禪于書,而且在創作中也真正做到了“寓禪于書”。
3 禪宗之悟與蘇軾的書法實踐
禪宗追求的是超越經驗的內心自悟,它反對格物,反對死于句下的分析、推理和判斷,認為只有心靈空靈澄澈時的全身心直覺體驗,才能對宇宙和人生作總結性根本把握,這種把握的途徑不是依靠“漸修”而得,而是依靠“頓悟”方式獲得。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境”就是這種頓悟的最好注腳。重視“頓悟”是禪宗思想與其他佛教宗派最大的區別之一,它也是禪宗思想核心要義所在。蘇軾在書法實踐上強調“通融無礙”的創作觀,我們在蘇東坡的名作《黃州寒食帖》中,看到的正是這種“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的禪意境界。在這件杰作中,字勢的欹側動蕩,行筆的爽健自然已經達到隨緣而適,隨機而化的神行境界。正所謂“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4 小結
不難發現,禪宗詩性哲學深深地影響著蘇軾的人生態度,也滲透于他的書法實踐和書法美學取向中,概而言之,是以“意”統攝下的以書入禪和以禪喻書,在“意造無法”“通其意”和“合于天造”的追求中闡釋禪的理趣與意蘊。因此,蘇軾書論中以禪喻書,寓禪于書,提供給后世的是一種比“尚法”更高妙的學書法則。這種對“通其意”的重視與肯定,既構成宋代尚意書風的主流形態,同時也為后世書風的深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蘇軾不僅是有宋書法史上的大家,更是中國佛學史上用藝術來抒發禪性的典型代表。
參考文獻:
[1]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Z].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2] 曾棗莊.蘇軾評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 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4] 曹慕樊,徐永年.東坡選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5] 沈子丞.歷代論畫名著匯編[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作者簡介:楊曉軍,男,甘肅蘭州人,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方向:美術學(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