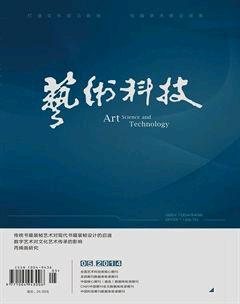戴少龍中國畫藝術探微
摘 要:結合當今實際,西方舶來的油畫沖擊著中國畫,使得中國畫面臨著挑戰,許多畫者作品中存在崇洋媚外,泛濫使用西方元素等問題,讓我們重新思考當今中國畫創作的方向問題,重建藝術家具有當代藝術的主體精神,又要使藝術家返回到母語的體系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創作,尋找到中國當代藝術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本文以戴少龍的寫意重彩畫為例,從造型、構圖、筆墨和色彩等方面對他的寫意重彩畫進行賞析。
關鍵詞:戴少龍;本土氣息;當代意識
戴少龍是湖北寫意重彩畫風的代表畫家之一,他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思路近年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要了解和感受他的作品,還需要一定的審美高度和筆墨形式方面的磨合。通過本文對戴少龍寫意重彩畫的藝術分析,希望讀者能找到與作品溝通的橋梁。
寫意重彩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繪畫體系,它吸收融合了水墨寫意的書寫性和工筆重彩的色彩表現,甚至還會借鑒西方藝術中的構成方式等,但同時又不斷地突破這些特性,它伴隨著現代以來中國畫的變革與創新。戴少龍的寫意重彩畫有著鮮明的個人特點:比例失調的人物及相似的人物特征,艷麗飽和的色彩,反復表現的題材和抽象的符號等等。正是因為這些明顯的個人特征,我們更能感受到戴少龍的執著和內心的真實。與其說戴少龍的作品是變形抽象的,我更愿意說他的作品是寫實的,不是對客觀事物的寫實,而是對內心情感的寫實。
戴少龍對造型的理解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創造出了具有個性的語言,他的寫意重彩畫有幾類比較典型的特征:一是扭曲的人體,一是稚拙的農民和村婦,再就是變形了的羊、狗、老虎等動物。辜鴻銘先生理解和概括中國人的特性說:“他們魯莽,而不至于卑賤下流;不好看,而不至于丑陋駭人;輕率猥瑣,而不至于猖獗傲慢;癡鈍,而不至于笨拙好笑”這正是戴少龍畫筆下的中國人的形象。戴少龍所畫的人體造型扭曲,甚至是概念地表現出來的。其實他正是想通過這種概念的、抽象的方式,來表示對當下社會的看法,表現當代人壓抑、憂慮和失落的感覺以及精神的缺失,這體現出他的寫意重彩畫具有“當代意識”。他有意識地扭曲人體來表達當代人的精神狀態,但又是以一種自然、無為的狀態來創作的。細心觀察人物的四肢和五官,或許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童年畫畫的影子,畫手指時,我們并不會考慮手的關節、體積,而是憑感覺概括成五個長條形。
戴少龍就是要追求童年時這種天真的、無為的造型方式。戴少龍覺得當代農民的身上有一些中國人的感覺,但是,他們來到了城市以后就讓金錢牽著鼻子走了,這樣的中國人的感覺就變了。于是,他筆下的“農民”形象均未沾染城市的喧囂,造型稚拙,眼神板滯。他的作品都是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是一種符號,我們欣賞他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們的眼睛和眉毛的造型相近,都顯現出一種脫俗的,具有中國氣質的造型,這充分顯示了戴少龍寫意重彩畫的“本土氣息”。再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戴少龍表現人物的眼睛時,并沒有像年畫那樣畫得很精細。他在刻畫人物的眼睛時,幾乎沒有描繪瞳孔的。說到不畫瞳孔,我不禁想起20世紀巴黎畫派畫家莫迪里阿尼。雖然戴少龍和莫迪里阿尼都不畫瞳孔,但是他們本質上想表達的內容是有區別的。莫迪里阿尼畫的是一種內向的自我凝望,尋求的是一種艱深的眼神。而戴少龍畫的是中國普通農民所共有的一種符號,追求的是一種質樸,單純的眼神。戴少龍或許有受到莫迪里阿尼的影響,但他并像某些畫者那樣完全照抄。他的寫意作品是構建在我國本土的文化的基礎之上再來創作的。
在戴少龍作品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夏加爾的崇尚,但是作品所呈現的感覺卻又是區別于夏加爾的,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看到畫面上出現了重疊、倒置的物體,這一點無疑是受到了立體主義和夏加爾的影響。夏加爾畫羊,戴少龍也畫羊,但是他們表現羊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夏加爾畫羊,表現的是一個農村生活的場面,表達了他對故鄉的思念,鄉愁幾乎是他一生中許多重要作品的靈感源泉。戴少龍畫的羊不一定是生活中真正的羊,他認為羊在中國文化里代表著陰性、弱勢、善良一類,而現代社會中需要這種“善”,他畫面中的羊只是一種代表“善良”的符號。
色彩是諸多藝術語言的組成要素,是中國畫藝術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畫的用色注重主觀的發揮與表達,強調寫意性和抒情性。這在戴少龍的寫意重彩畫里表現得尤為突出,他的畫面表現出大紅大綠,鮮艷而又穩重的色彩。他按照自我的主觀情感以及整個畫面構成形式的要求,自由地游走于色彩的對比統一錯綜復雜的關系當中,借色抒懷,以意賦色,使主觀的色彩感受在整個畫面中催化出韻律和美感。戴少龍畫面中的用色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傾訴,更多地代表著某種精神層面。他畫面中的顏色都是很陽性的,色彩都是充滿著光明的,它關注的是人性中一些美好的東西。
戴少龍對墨的掌控與運用,和他畫面中所運用的抒情性色彩相得益彰。他堅信,運用傳統的筆墨形式描繪當今時代生活會顯得蒼白無力.于是他在發揚“氣韻生動”精神的前提下,大膽舍棄傳統筆墨固有的某些東西, 不斷地探索尋求新的筆墨圖式和新的語言方式來豐富畫面,賦予所謂筆墨以新的內涵,創作出樣式獨特的戴少龍風格,從而創造出既具有“本土氣息”又不缺乏“當代意識”的作品。戴少龍的重彩畫是把顏色和水墨、宣紙及自己的繪畫造型方式,全部融合協調在一起。他對線描、工筆、水墨、油畫、壁畫,中國古代的文化包括西方現當代藝術創作都有涉及和研究,他吸收了工筆畫的技法和水墨畫的寫意性、隨機性等,另外借鑒了中國壁畫的色塊,包括一些重彩顏料的運用,加上他個人的心性和獨立的思考。
以戴少龍的寫意重彩畫為例,我們一起感受了他作品中那濃濃的中國泥土氣息以及畫家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即“當代意識”。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是優秀的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相比具有它獨特的一面。我們的文化藝術一定要在我們自己強大的傳統文化根基上去成長,在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與觀念基礎之上“容納”其他民族的藝術文化。中國畫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形式規范、理論原則和風格特點,它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不免要根據需要作相應的自我改造,但這不代表西方文化可以肆無忌憚地填充我們本國文化。在戴少龍的作品中在藝術創作方面,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我們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必須發自真實的內心,創作出具有“本土氣息”和“當代意識”的作品。
參考文獻:
[1] 周宏智.西方現代藝術史[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
[2] 戴少龍,周韶華.戴少龍寫意重彩畫[M].湖北美術出版社,2010.
[3] 戴少龍.我的生活與藝術——科教文匯(上半月) [J].2004(01).
[4] 美術研究.江南蛻變 19世紀初中國藝術史一撇[J].1998(04).
[5] 周宏智.西方現代藝術史[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7] 李世南.狂歌當哭[M].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
[9] 畢建勛.當代中國美術家檔案[M].華文出版社,2006.
[10] 姜壽田.現代畫家批評[M].河南美術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俞海超(1991—),男,河北石家人,江漢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系2010級本科生,美術教育專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