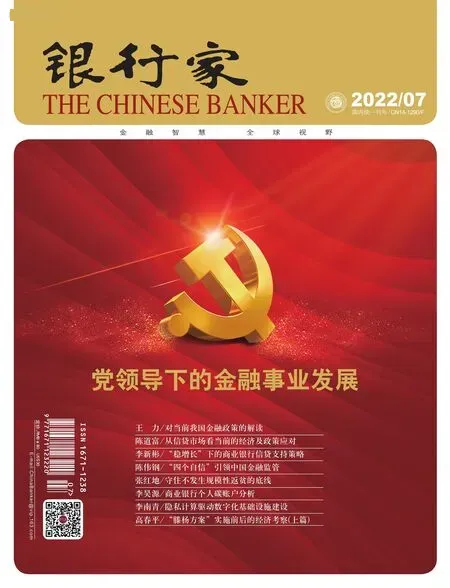中美銀行信貸資產出表之比較
李利++侯敬雯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非標資產快速發展和風險膨脹的現象受到了各方關注。其龐大的規模、復雜的交易鏈、對監管的規避以及不透明的內部運作,引發監管層關注并下發文件進行監管,但并沒有實質性改變。縱觀國外,美國銀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與我國類似的情況,但其憑借金融創新走出了困境,并領先全球金融業。因此,可以比較借鑒美國的先進經驗,為我國銀行業提供參考。
出表的動因比較
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規避監管、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及解決資產期限錯配是中美銀行信貸資產出表的三大動因。
規避監管要求。規避當局監管尤其是對貸款規模的監管是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重要動因。例如美國銀行業要突破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促進法》對資本比率的限制,我國銀行要突破貸款規模、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存貸款利率等監管指標限制。
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利率市場化給銀行帶來了嚴峻挑戰。從資產端來說,銀行同業間貸款業務進一步加劇,而非銀行金融業間通過債券市場也對銀行貸款業務產生了壓力;從負債端來說,日新月異的投資手段分流了銀行存款,提高了資金成本,銀行傳統的存貸利差盈利模式日益受迫。
解決資產期限錯配問題。“長貸短存”是中美銀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以代表性的美國儲貸協會為例,其負債端為中短期的居民儲蓄,資產端為長達30年的住房貸款。這種資產錯配不僅增加了風險,也使儲貸協會的利潤和資金流動性受到影響。為解決這一矛盾,儲貸協會將長期房貸打包證券化出售,保險公司、養老金等機構等根據自身需求來購買適當期限的品種,這樣在期限上使得雙方的資產負債表都得到了改善。我國銀行的期限錯配現象也十分嚴重,資金負債端主要來自中短期居民儲蓄,負債端主要是中長期貸款。亟需新的方式盤活中長期信貸資產。
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方式比較
美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以資產證券化方式進行。美國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的不動產主線,以證券化等標準化方式進行。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推出了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政策,鼓勵個人住房貸款。里根時代制定了“居者有其屋、實現美國夢”的中低收入住房改善政策,實行較寬松的信貸支持政策,鼓勵銀行向中低收入階層貸款,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嬰兒潮步入購房高峰,美國金融機構發放住房貸款所需的資金逐步緊張。金融機構僅依靠吸收存款、轉讓信貸等傳統融資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貸款需求。商業銀行放貸能力的受限使得其信貸資產出表需求強烈。為此,銀行采取了出售貸款、證券化等方式滿足需求,盤活了長期貸款資產,解決了貸款資金來源的困難。
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以“非標”方式和監管當局做著“貓鼠游戲”。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演繹著銀行與監管層博弈的“貓鼠游戲”。參與主體越來越多,含括信托公司、券商、保險公司、基金公司、財務公司、農村金融機構等;業務模式也由單一的銀信合作演變為繁多的同業業務、買入返售銀行承兌匯票、同業償付、票據雙買斷等多元模式;投資標的由信托計劃等演變為資產管理等眾多形式。
出表選擇的影響因素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走的是“正規軍”——資產證券化的道路;中國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正規軍”——“非標”的途徑。兩國出表方式的不同選擇,在于其監管政策、基礎資產、中介方以及標的等影響因素的不同。
監管政策比較
中美對于信貸資產出表的監管態度差別較大。美國注重法律和市場環境建設,并推動證券化發展為信貸資產出表創造條件。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是近幾年才蓬勃發展的新生事物,監管當局對此經驗不足,加之市場環境尚待培育,因此政策早期以“堵”為主,在多次貓鼠游戲之后,正逐步向“疏”轉變(如表2和表3所示)。
基礎資產比較
美國的信貸存量規模以消費信貸尤其是房貸為主,這種類型的貸款社會存量大,供給穩定,同質化、標準化程度高,易于打包證券化出售,方便以證券化方式出表。與美國不同,我國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在內的消費類信貸占比不高,銀行的主要信貸資產是工商業貸款,其標準化程度較之住房貸款低,證券化程度復雜。在市場發育未完全時,以非標方式出表更加簡單便利(如圖1和圖2所示)。
中介方比較
銀行信貸資產出表過程中,中介方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國的信貸資產出表,投行發揮了業務創新的重要作用。投行集發行、咨詢、承銷、做市、投資等多種角色于一身,持續創新和產品設計優化了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交易結構,使其在定價、風險等方面更能為投資者所接受,大大地增加了可證券化資產的廣度,滿足了不同投資者的配置需求(如表4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標”模式,中介方的業務創新主要集中在規避監管上(如表5所示)。利用多頭監管實現政策套利,引入過橋銀行間接設立定向資管計劃,過橋機構越多,操作越復雜,監管的難度就越大。券商成為銀行和信托公司間的通道,不承擔風險,賺取平臺管理費。
國內信貸資產出表的中介方雖然面臨著美國當時類似的尷尬境界:利潤下滑、市場被蝕、亟需創新,但卻沒有像美國一樣在產品創新上贏得先機。原因除了監管環境和政策不同外,市場的不發達和非均衡也有很大關系。從宏觀上說國內金融資源配置極不平衡,銀行的優勢地位使得中介方更多以滿足銀行需求為業務出發點,忽略了基于自身的業務創新。從微觀上說國內券商的業務品種創新仍處在模仿和追趕過程中,而實務中這種“舶來品”的盈利性較差,大大影響了券商創新的積極性。
標的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證券化市場標的多元化,有MBS(抵押貸款擔保證券)、ABS(資產支持證券)、CDO(債務抵押證券)等多種類型供選擇(如圖3所示)。
從規模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在2008年之前呈現較快增長態勢,但危機后迅速萎縮。從占比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以MBS為主,2013年占比超過50%(如圖4和圖5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目前主要有兩種標的:銀監會和央行主導的信貸資產證券化(ABS)和銀行間市場交易上協會主導的企業資產支持票據(ABN)。但嚴格來說,二者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實務中,券商承做的ABS審批行政成本較高,加之金融危機后被叫停三年,因此規模十分有限。由銀行承做的ABN是目前資產支持證券的主體,但與銀行債券發行規模及整體債券發行規模相比,仍然微乎其微(如圖6所示)。
結論及展望
從中美的各方情況比較來看,雖然我國信貸資產出表在諸多方面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有著類似情況,但二者由于環境不同,發展不盡相同。
美國由于政策支持、中介方創新能力強、基礎資產易于標準化、標的多樣等有利因素,走了一條資產證券化的道路,并引領了全球金融創新潮流。
相比之下,我國信貸資產出表采取證券化的方式條件仍不成熟。首先,在政策環境上,在監管分開進行、證券化額度受限,基礎資產要求較嚴,客戶資質要求較高的條件下,短期內無法培育出一個競爭充分的證券化市場。其次,中介方的創新能力與熱情不高、缺乏評級公正公開的機構等也影響了資產證券化的速度。
未來,預計我國信貸資產出表短期內最可行方式仍將以“非標”的方式存在。這是因為非標暫時有著其他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派生企業存款;形成中間業務;項目對接便利等。在127號文之后,銀行資產負債會作一定調整,買入返售項下非標轉移至應收款項類投資項下,可能出現中小銀行非標到期后由大行續作的情況。長期看,銀行非標業務模式會發生改變,其套利野蠻增長時代必將結束,未來可能走向資產證券化的道路。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非標資產快速發展和風險膨脹的現象受到了各方關注。其龐大的規模、復雜的交易鏈、對監管的規避以及不透明的內部運作,引發監管層關注并下發文件進行監管,但并沒有實質性改變。縱觀國外,美國銀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與我國類似的情況,但其憑借金融創新走出了困境,并領先全球金融業。因此,可以比較借鑒美國的先進經驗,為我國銀行業提供參考。
出表的動因比較
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規避監管、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及解決資產期限錯配是中美銀行信貸資產出表的三大動因。
規避監管要求。規避當局監管尤其是對貸款規模的監管是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重要動因。例如美國銀行業要突破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促進法》對資本比率的限制,我國銀行要突破貸款規模、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存貸款利率等監管指標限制。
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利率市場化給銀行帶來了嚴峻挑戰。從資產端來說,銀行同業間貸款業務進一步加劇,而非銀行金融業間通過債券市場也對銀行貸款業務產生了壓力;從負債端來說,日新月異的投資手段分流了銀行存款,提高了資金成本,銀行傳統的存貸利差盈利模式日益受迫。
解決資產期限錯配問題。“長貸短存”是中美銀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以代表性的美國儲貸協會為例,其負債端為中短期的居民儲蓄,資產端為長達30年的住房貸款。這種資產錯配不僅增加了風險,也使儲貸協會的利潤和資金流動性受到影響。為解決這一矛盾,儲貸協會將長期房貸打包證券化出售,保險公司、養老金等機構等根據自身需求來購買適當期限的品種,這樣在期限上使得雙方的資產負債表都得到了改善。我國銀行的期限錯配現象也十分嚴重,資金負債端主要來自中短期居民儲蓄,負債端主要是中長期貸款。亟需新的方式盤活中長期信貸資產。
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方式比較
美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以資產證券化方式進行。美國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的不動產主線,以證券化等標準化方式進行。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推出了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政策,鼓勵個人住房貸款。里根時代制定了“居者有其屋、實現美國夢”的中低收入住房改善政策,實行較寬松的信貸支持政策,鼓勵銀行向中低收入階層貸款,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嬰兒潮步入購房高峰,美國金融機構發放住房貸款所需的資金逐步緊張。金融機構僅依靠吸收存款、轉讓信貸等傳統融資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貸款需求。商業銀行放貸能力的受限使得其信貸資產出表需求強烈。為此,銀行采取了出售貸款、證券化等方式滿足需求,盤活了長期貸款資產,解決了貸款資金來源的困難。
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以“非標”方式和監管當局做著“貓鼠游戲”。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演繹著銀行與監管層博弈的“貓鼠游戲”。參與主體越來越多,含括信托公司、券商、保險公司、基金公司、財務公司、農村金融機構等;業務模式也由單一的銀信合作演變為繁多的同業業務、買入返售銀行承兌匯票、同業償付、票據雙買斷等多元模式;投資標的由信托計劃等演變為資產管理等眾多形式。
出表選擇的影響因素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走的是“正規軍”——資產證券化的道路;中國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正規軍”——“非標”的途徑。兩國出表方式的不同選擇,在于其監管政策、基礎資產、中介方以及標的等影響因素的不同。
監管政策比較
中美對于信貸資產出表的監管態度差別較大。美國注重法律和市場環境建設,并推動證券化發展為信貸資產出表創造條件。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是近幾年才蓬勃發展的新生事物,監管當局對此經驗不足,加之市場環境尚待培育,因此政策早期以“堵”為主,在多次貓鼠游戲之后,正逐步向“疏”轉變(如表2和表3所示)。
基礎資產比較
美國的信貸存量規模以消費信貸尤其是房貸為主,這種類型的貸款社會存量大,供給穩定,同質化、標準化程度高,易于打包證券化出售,方便以證券化方式出表。與美國不同,我國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在內的消費類信貸占比不高,銀行的主要信貸資產是工商業貸款,其標準化程度較之住房貸款低,證券化程度復雜。在市場發育未完全時,以非標方式出表更加簡單便利(如圖1和圖2所示)。
中介方比較
銀行信貸資產出表過程中,中介方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國的信貸資產出表,投行發揮了業務創新的重要作用。投行集發行、咨詢、承銷、做市、投資等多種角色于一身,持續創新和產品設計優化了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交易結構,使其在定價、風險等方面更能為投資者所接受,大大地增加了可證券化資產的廣度,滿足了不同投資者的配置需求(如表4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標”模式,中介方的業務創新主要集中在規避監管上(如表5所示)。利用多頭監管實現政策套利,引入過橋銀行間接設立定向資管計劃,過橋機構越多,操作越復雜,監管的難度就越大。券商成為銀行和信托公司間的通道,不承擔風險,賺取平臺管理費。
國內信貸資產出表的中介方雖然面臨著美國當時類似的尷尬境界:利潤下滑、市場被蝕、亟需創新,但卻沒有像美國一樣在產品創新上贏得先機。原因除了監管環境和政策不同外,市場的不發達和非均衡也有很大關系。從宏觀上說國內金融資源配置極不平衡,銀行的優勢地位使得中介方更多以滿足銀行需求為業務出發點,忽略了基于自身的業務創新。從微觀上說國內券商的業務品種創新仍處在模仿和追趕過程中,而實務中這種“舶來品”的盈利性較差,大大影響了券商創新的積極性。
標的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證券化市場標的多元化,有MBS(抵押貸款擔保證券)、ABS(資產支持證券)、CDO(債務抵押證券)等多種類型供選擇(如圖3所示)。
從規模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在2008年之前呈現較快增長態勢,但危機后迅速萎縮。從占比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以MBS為主,2013年占比超過50%(如圖4和圖5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目前主要有兩種標的:銀監會和央行主導的信貸資產證券化(ABS)和銀行間市場交易上協會主導的企業資產支持票據(ABN)。但嚴格來說,二者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實務中,券商承做的ABS審批行政成本較高,加之金融危機后被叫停三年,因此規模十分有限。由銀行承做的ABN是目前資產支持證券的主體,但與銀行債券發行規模及整體債券發行規模相比,仍然微乎其微(如圖6所示)。
結論及展望
從中美的各方情況比較來看,雖然我國信貸資產出表在諸多方面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有著類似情況,但二者由于環境不同,發展不盡相同。
美國由于政策支持、中介方創新能力強、基礎資產易于標準化、標的多樣等有利因素,走了一條資產證券化的道路,并引領了全球金融創新潮流。
相比之下,我國信貸資產出表采取證券化的方式條件仍不成熟。首先,在政策環境上,在監管分開進行、證券化額度受限,基礎資產要求較嚴,客戶資質要求較高的條件下,短期內無法培育出一個競爭充分的證券化市場。其次,中介方的創新能力與熱情不高、缺乏評級公正公開的機構等也影響了資產證券化的速度。
未來,預計我國信貸資產出表短期內最可行方式仍將以“非標”的方式存在。這是因為非標暫時有著其他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派生企業存款;形成中間業務;項目對接便利等。在127號文之后,銀行資產負債會作一定調整,買入返售項下非標轉移至應收款項類投資項下,可能出現中小銀行非標到期后由大行續作的情況。長期看,銀行非標業務模式會發生改變,其套利野蠻增長時代必將結束,未來可能走向資產證券化的道路。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非標資產快速發展和風險膨脹的現象受到了各方關注。其龐大的規模、復雜的交易鏈、對監管的規避以及不透明的內部運作,引發監管層關注并下發文件進行監管,但并沒有實質性改變。縱觀國外,美國銀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與我國類似的情況,但其憑借金融創新走出了困境,并領先全球金融業。因此,可以比較借鑒美國的先進經驗,為我國銀行業提供參考。
出表的動因比較
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規避監管、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及解決資產期限錯配是中美銀行信貸資產出表的三大動因。
規避監管要求。規避當局監管尤其是對貸款規模的監管是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重要動因。例如美國銀行業要突破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促進法》對資本比率的限制,我國銀行要突破貸款規模、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存貸款利率等監管指標限制。
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利率市場化給銀行帶來了嚴峻挑戰。從資產端來說,銀行同業間貸款業務進一步加劇,而非銀行金融業間通過債券市場也對銀行貸款業務產生了壓力;從負債端來說,日新月異的投資手段分流了銀行存款,提高了資金成本,銀行傳統的存貸利差盈利模式日益受迫。
解決資產期限錯配問題。“長貸短存”是中美銀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以代表性的美國儲貸協會為例,其負債端為中短期的居民儲蓄,資產端為長達30年的住房貸款。這種資產錯配不僅增加了風險,也使儲貸協會的利潤和資金流動性受到影響。為解決這一矛盾,儲貸協會將長期房貸打包證券化出售,保險公司、養老金等機構等根據自身需求來購買適當期限的品種,這樣在期限上使得雙方的資產負債表都得到了改善。我國銀行的期限錯配現象也十分嚴重,資金負債端主要來自中短期居民儲蓄,負債端主要是中長期貸款。亟需新的方式盤活中長期信貸資產。
中美信貸資產出表的方式比較
美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以資產證券化方式進行。美國信貸資產出表,沿著“美國夢”的不動產主線,以證券化等標準化方式進行。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推出了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政策,鼓勵個人住房貸款。里根時代制定了“居者有其屋、實現美國夢”的中低收入住房改善政策,實行較寬松的信貸支持政策,鼓勵銀行向中低收入階層貸款,美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嬰兒潮步入購房高峰,美國金融機構發放住房貸款所需的資金逐步緊張。金融機構僅依靠吸收存款、轉讓信貸等傳統融資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貸款需求。商業銀行放貸能力的受限使得其信貸資產出表需求強烈。為此,銀行采取了出售貸款、證券化等方式滿足需求,盤活了長期貸款資產,解決了貸款資金來源的困難。
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以“非標”方式和監管當局做著“貓鼠游戲”。中國式信貸資產出表,演繹著銀行與監管層博弈的“貓鼠游戲”。參與主體越來越多,含括信托公司、券商、保險公司、基金公司、財務公司、農村金融機構等;業務模式也由單一的銀信合作演變為繁多的同業業務、買入返售銀行承兌匯票、同業償付、票據雙買斷等多元模式;投資標的由信托計劃等演變為資產管理等眾多形式。
出表選擇的影響因素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走的是“正規軍”——資產證券化的道路;中國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正規軍”——“非標”的途徑。兩國出表方式的不同選擇,在于其監管政策、基礎資產、中介方以及標的等影響因素的不同。
監管政策比較
中美對于信貸資產出表的監管態度差別較大。美國注重法律和市場環境建設,并推動證券化發展為信貸資產出表創造條件。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是近幾年才蓬勃發展的新生事物,監管當局對此經驗不足,加之市場環境尚待培育,因此政策早期以“堵”為主,在多次貓鼠游戲之后,正逐步向“疏”轉變(如表2和表3所示)。
基礎資產比較
美國的信貸存量規模以消費信貸尤其是房貸為主,這種類型的貸款社會存量大,供給穩定,同質化、標準化程度高,易于打包證券化出售,方便以證券化方式出表。與美國不同,我國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在內的消費類信貸占比不高,銀行的主要信貸資產是工商業貸款,其標準化程度較之住房貸款低,證券化程度復雜。在市場發育未完全時,以非標方式出表更加簡單便利(如圖1和圖2所示)。
中介方比較
銀行信貸資產出表過程中,中介方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國的信貸資產出表,投行發揮了業務創新的重要作用。投行集發行、咨詢、承銷、做市、投資等多種角色于一身,持續創新和產品設計優化了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交易結構,使其在定價、風險等方面更能為投資者所接受,大大地增加了可證券化資產的廣度,滿足了不同投資者的配置需求(如表4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出表走的是“非標”模式,中介方的業務創新主要集中在規避監管上(如表5所示)。利用多頭監管實現政策套利,引入過橋銀行間接設立定向資管計劃,過橋機構越多,操作越復雜,監管的難度就越大。券商成為銀行和信托公司間的通道,不承擔風險,賺取平臺管理費。
國內信貸資產出表的中介方雖然面臨著美國當時類似的尷尬境界:利潤下滑、市場被蝕、亟需創新,但卻沒有像美國一樣在產品創新上贏得先機。原因除了監管環境和政策不同外,市場的不發達和非均衡也有很大關系。從宏觀上說國內金融資源配置極不平衡,銀行的優勢地位使得中介方更多以滿足銀行需求為業務出發點,忽略了基于自身的業務創新。從微觀上說國內券商的業務品種創新仍處在模仿和追趕過程中,而實務中這種“舶來品”的盈利性較差,大大影響了券商創新的積極性。
標的比較
美國資產出表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證券化市場標的多元化,有MBS(抵押貸款擔保證券)、ABS(資產支持證券)、CDO(債務抵押證券)等多種類型供選擇(如圖3所示)。
從規模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在2008年之前呈現較快增長態勢,但危機后迅速萎縮。從占比上來說,美國資產支持債券以MBS為主,2013年占比超過50%(如圖4和圖5所示)。
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目前主要有兩種標的:銀監會和央行主導的信貸資產證券化(ABS)和銀行間市場交易上協會主導的企業資產支持票據(ABN)。但嚴格來說,二者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實務中,券商承做的ABS審批行政成本較高,加之金融危機后被叫停三年,因此規模十分有限。由銀行承做的ABN是目前資產支持證券的主體,但與銀行債券發行規模及整體債券發行規模相比,仍然微乎其微(如圖6所示)。
結論及展望
從中美的各方情況比較來看,雖然我國信貸資產出表在諸多方面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有著類似情況,但二者由于環境不同,發展不盡相同。
美國由于政策支持、中介方創新能力強、基礎資產易于標準化、標的多樣等有利因素,走了一條資產證券化的道路,并引領了全球金融創新潮流。
相比之下,我國信貸資產出表采取證券化的方式條件仍不成熟。首先,在政策環境上,在監管分開進行、證券化額度受限,基礎資產要求較嚴,客戶資質要求較高的條件下,短期內無法培育出一個競爭充分的證券化市場。其次,中介方的創新能力與熱情不高、缺乏評級公正公開的機構等也影響了資產證券化的速度。
未來,預計我國信貸資產出表短期內最可行方式仍將以“非標”的方式存在。這是因為非標暫時有著其他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派生企業存款;形成中間業務;項目對接便利等。在127號文之后,銀行資產負債會作一定調整,買入返售項下非標轉移至應收款項類投資項下,可能出現中小銀行非標到期后由大行續作的情況。長期看,銀行非標業務模式會發生改變,其套利野蠻增長時代必將結束,未來可能走向資產證券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