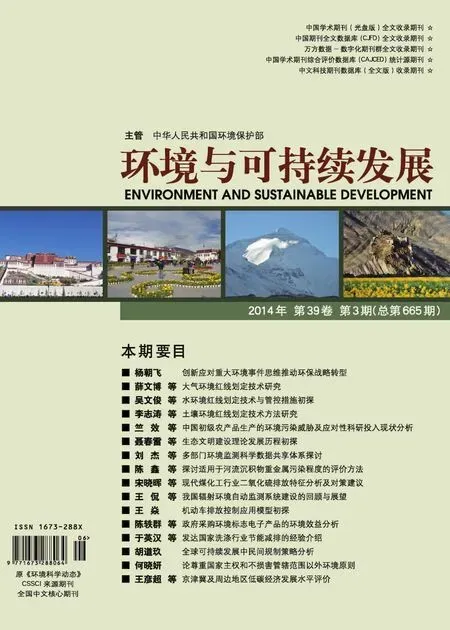探討適用于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的評價方法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北京 100012)
1 引 言
進入水體中的重金屬元素,絕大部分隨物理、化學、生物作用的進行能迅速由水相轉入固相(懸浮物和底泥),最終沉降至底泥中,使沉積物成為重金屬等化學物質的主要存儲庫。隨著河流水質理化條件的改變,底泥中的重金屬也可以重新釋放出來,導致水環境的惡化,甚至通過食物鏈對人類健康造成威脅。所以作為水環境監測的補充,沉積物的監測在水環境監測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目前,國內外對沉積物重金屬的監測技術比較成熟[1],國內外關于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的評價方法也很多[2],但是由于沉積物中重金屬的監測尚未納入例行環境監測,因此評價沉積物中的重金屬污染程度的方法尚未建立。
2 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文通過查閱文獻,篩選出了目前常用的兩種評價方法,并通過某一區域河流沉積物中重金屬含量的測定結果,比較了兩種方法的評價結果。為建立我國水環境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的判定評價方法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2.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同一區域的五條河流,采集了沉積物表層0~10cm的底泥樣品。監測項目為銅、鉛、鋅、鎘、鉻、汞和砷共7項指標。樣品的前處理方法和重金屬含量測定的具體操作參見《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第四版)》[3]。監測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沉積物中重金屬分析測試結果
3 結果與討論
3.1 沉積物評價方法與比較
對河流沉積物中重金屬污染的評價,目前我國尚沒有統一的評價規范與方法。國內外關于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的評價方法很多,常用且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地累積指數法(Geoaccumulation Index)、沉積物富集系數法(Sediment Enrichment Factor)、污染負荷指數法(The Pollution Load Index)、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回歸過量分析法(Excess after Regression Analysis)和臉譜法(Face-Graph)等。這些方法各具特色,適用范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根據文獻,目前我國在沉積物污染研究中用于評價的方法主要是地累積指數法和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4-9]。地累積指數法是德國學者Muller于1979年提出的[10],在歐洲被廣泛應用,主要用于研究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程度。近年來還有將其用于評估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和評價大氣降塵的報道[11-12]。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是1980年由瑞典學者Hankanson提出的[13],又名Hankanson指數法,多用于表征沉積污染物對生態環境的潛在危害。
3.1.1 地累積指數法
地累積指數法的優勢在于其與環境地球化學背景值相關聯。計算公式為:
Igeo=log2[Cn/(k×Bn)]
式中:Cn——元素n在沉積物中的濃度;
Bn——元素n的地球化學背景值;
k——考慮各地巖石差異可能會引起背景值的變動而取的系數(一般取值為1.5)。
Bn是計算地累積指數的重要參數,各家研究選取的標準并不一致,本文采用“七五”全國土壤背景調查成果《中國土壤背景值》[14]給出的當地土壤背景值(表2)。
地累積指數分為0~6級(共7級),表示污染程度由無至極強。最高一級(6級)的元素含量可能是背景值的幾百倍。Igeo值與重金屬污染程度分級關系見表3。
3.1.2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
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RI)多用于沉積物生態風險的評價。計算公式為:





RI——多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


表2 當地土壤環境背景值

表3 地累積指數與污染程度分級

表4 主要重金屬種類與毒性系數

表5 潛在生態風險指數和RI的分級標準
3.1.3兩種評價方法的比較
通過計算公式可以看出:潛在生態危害指數不僅隨重金屬含量的加大而增加,同時參與評價的重金屬種類越多的潛在生態危害越大。另外,由于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中賦予了不同重金屬的毒性系數,因此毒性大的重金屬在指數中占有更高的權重。地累積指數法的優勢在于其與環境背景值相關聯,主要用于表征沉積物中各種重金屬的污染程度。潛在生態危害指數可以評價出整體的風險程度,而地累積指數可以客觀反映某種重金屬的污染程度。
在進行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現狀評價時,如采用地累積指數法,有全國土壤背景值調查成果的支撐,技術條件完備;如采用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除需要采用全國土壤背景值調查成果外,不同重金屬的毒性系數也是重要的參數。由于我國尚無權威的資料參考,所以技術條件尚不成熟。
3.2 沉積物評價結果與討論
本文使用地累積指數法和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對上述五條河流的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測定結果進行了評價和比較。
3.2.1 地累積指數評價結果
根據地累積指數的計算公式,得到各斷面各個重金屬的地累積指數,對照表1進行分級,結果見表6。

表6 沉積物地累積指數與分級
根據7個測定的重金屬元素的地累積指數污染程度的分級:S1斷面沉積物中鉛的污染程度為5級,汞為1級,其余均為0級;S2斷面沉積物銅的污染程度為3級,鉛、鋅、鎘和砷為2級,鉻和汞為0級;S3斷面沉積物的污染程度較低,僅汞為1級,其余均為0級;S4斷面沉積物鉛的污染程度為4級,銅和汞為2級,鉻為1級,其余均為0級;S5斷面沉積物中鉛、鋅、鎘和砷為2級,銅為1級,鉻和汞為0級。
從表6可以看出,不同河流不同重金屬元素的污染程度不同,應該與污染源排放情況等人為影響因素有關。以最高污染等級評價,同一區域的五條河流的污染程度從1級到5級均存在。
3.2.2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結果
根據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計算公式計算得出沉積物中各個重金屬的 Eri指數與總體的RI指數,并參照表4進行分級與評價,結果見表7。

表7 沉積物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與風險評估
根據潛在生態危害指數的評價規則,同一區域的五條河流中,S1、S2和S5沉積物中重金屬對環境的潛在生態危害已經達到了高風險程度,因此,應該加強對該區域河流沉積物中重金屬含量的監視。
3.2.3兩種評價結果的比較
按照最大地累積指數污染程度評價,5條河流的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分成了1~5五級。按照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5條河流的沉積物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風險程度劃分成了高中低三級。
地累積指數評價污染程度為4級的S4,由于鉛的毒性系數較低,被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為中度風險。地累積指數評價污染程度為2級的S5,由于有多種重金屬的污染,被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為高度風險。
因此,不同的評價方法給出的評價結果有可能是是不同的。在實際應用時可以根據具體的評價目的選擇適當的評價方法。
4 結 語
(1)目前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評價和生態風險評估的方法不少,側重點不同,不同方法評價出來的結論也不盡相同。鑒于沉積物在水環境狀況評價以及水環境污染防治中的重要性,建議將河流沉積物重金屬的監測納入常規監測范疇,填補目前我國在常規監測中環境要素缺失的空白。
(2)地累積指數法與環境地球化學背景值相關聯,能夠客觀的反映河流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程度,而且目前我國環境監測部門的技術能力與技術水平已經完全具備了采用地累積指數評價河流沉積物污染程度的能力。建議采用地累積指數法作為環境質量監測中評價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的評價方法。
(3)對沉積物重金屬的監測可以分步實施,首先選擇重金屬礦產開采、冶煉等涉重地區,為掌握我國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與變化趨勢積累數據建立檔案。
(4)可以根據環境管理的需要,對沉積物的評價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將多種評價方法有機的結合起來,制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整體評述沉積物重金屬的污染狀況和風險程度的評價規范,為對水環境進行全面評價做技術儲備。
參考文獻:
[1]蘭靜,朱志勛,馮艷玲等.沉積物監測方法和質量基準研究現狀及進展[J].人民長江,2012,43(12):78-80.
[2]張鑫,周濤發,楊西飛等.河流沉積物重金屬污染評價方法比較研究[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28(11):1419-1423.
[3]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編委會,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第四版)[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
[4]尚英男,倪師軍,張成江等.應用地質累積指數評價成都市河流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J].廣東微量元素科學,2005,12(10):12-16.
[5]周秀艷,王恩德.遼東灣潮間帶底質重金屬污染地累積指數評價[J].安全與環境學報,2004,4(2):22-24.
[6] 康銀健.Hakanson指數法評價水體沉積物重金屬生態風險的應用進展[J].環境科學導刊,2008,27(3):66-68.
[7]安立會,鄭丙輝,張雷等.渤海灣河口沉積物重金屬污染及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中國環境科學,2010,30(5):666-670.
[8]Asma Binta Hasan,Sohail Kabir,A.H.M.Selim Reza,Mohammad Nazim Zaman,Aminul Ahsan,Mamunur Rashid.Enrichment factor and geo-accumulation index of trace metals in sediments of the ship breaking area of Sitakund Upazilla (Bhatiary-Kumira),Chittagong,Bangladesh[J].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2013 (125) :130-137.
[9]Azmat Zahra,Muhammad Zaffar Hashmi,Riffat NaseemMalik,Zulkifl Ahmed.Enrichment and geo-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sediments of the Kurang Nallah—Feeding tributary of the Rawal Lake Reservoir,Pakistan[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4 (470-471) :925-933.
[10]Forstner U,Ahlf W,Calmano W,et al.Sediment criteria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from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to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A],In:Heling D,Rothe P,Forstner U,et al.Sediment and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Selected Aspects Case Histories[M].Berlin Heidelberg:Spring Verlag,1990.311-338.
[11]WEI Zhiyuan,WANG Dengfeng,ZHOU Huiping,QI Zhiping.Assessment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Geoaccumulation Index[J].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1,(10 ):1946-1952
.[12]JI Yaqin,FENG Yinchang,WU Jianhui,ZHU Tan,BAI Zhipeng,DUAN Chiqing.Using geoaccumulation index to study source profiles of soil dust in Chin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8,(20):571-578.
[13]Hakanson L.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A sediment tological approach[J].Water Res.,1980,14:975-1001.
[14]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中國土壤背景值[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