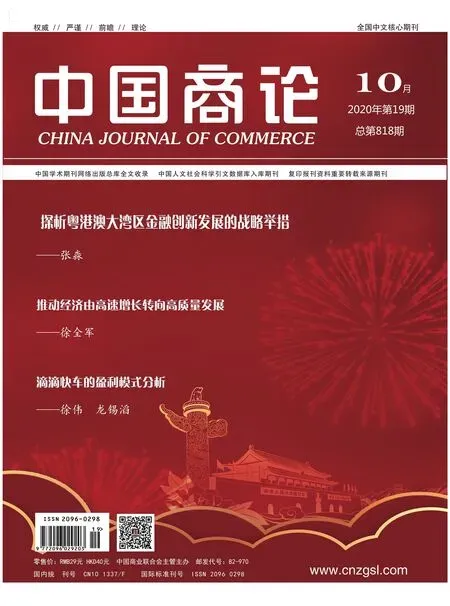校園文化消費(fèi)狀況的調(diào)查與探析①——以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手機(jī)消費(fèi)為例
新疆大學(xué)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宋嬌嬌 沈婷 毛小琴 李先游
在當(dāng)代消費(fèi)主義浪潮的席卷下,文化生產(chǎn)和文化消費(fèi)成為兩個相伴而生的問題。校園中大學(xué)生旺盛的精力、蓬勃的求知欲、對新生事物的敏感以及積極的好奇心,一方面構(gòu)建出特點(diǎn)鮮明的校園文化,另一方面也營造了內(nèi)容豐富頗具時代感的校園消費(fèi)市場。因而,本文從校園消費(fèi)文化的基本狀況出發(fā),解析消費(fèi)文化對當(dāng)代大學(xué)生的沖擊和影響,繼而對校園文化建設(shè)給予建議。在大學(xué)生的日常生活中,對手機(jī)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已經(jīng)不單單集中在使用價值維度上,手機(jī)和人的關(guān)系變得日益復(fù)雜。而圍繞著手機(jī)所形成的消費(fèi)系統(tǒng)已經(jīng)成為校園文化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通過近一年的調(diào)查分析,發(fā)現(xiàn)在新疆大學(xué)這個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文化場域,它所形成的手機(jī)消費(fèi)具有鮮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
1 消費(fèi)文化背景下的校園手機(jī)文化
當(dāng)代社會物質(zhì)豐富、媒體發(fā)達(dá),再加上廣告的高頻單向宣傳,消費(fèi)逐步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fā)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的文化狀況已經(jīng)逐漸由生產(chǎn)中心轉(zhuǎn)向消費(fèi)中心。“消費(fèi)作為社會主體的需求與可能滿足這種需求的物質(zhì)間的關(guān)系,就不應(yīng)當(dāng)簡單的看作主體占有、使用、消耗客體的過程,而應(yīng)看作社會主體的一種再生產(chǎn)形式。”[1]
(1)人們所消費(fèi)的產(chǎn)品是人化物,消費(fèi)者按照時尚化和被給予的消費(fèi)結(jié)構(gòu)來生產(chǎn)新的文化信息,因此形成了消費(fèi)文化。文化消費(fèi)是消費(fèi)者為了滿足自身的文化需求、精神享受而進(jìn)行的消費(fèi)。它不同于產(chǎn)品消費(fèi),在消費(fèi)社會中“文化消費(fèi)展現(xiàn)為消費(fèi)文化形體和社會景觀,當(dāng)代消費(fèi)文化形態(tài)又必須通過文化消費(fèi)呈現(xiàn)出來。”[2]
(2)手機(jī)文化建立在手機(jī)消費(fèi)的基礎(chǔ)上,一方面呈現(xiàn)在實(shí)用價值消費(fèi)上,即打電話,發(fā)短信的通信功能,以及智能手機(jī)和網(wǎng)絡(luò)的連接等。另一方面隨著手機(jī)生產(chǎn)的擴(kuò)大,大眾傳媒的發(fā)展,利用網(wǎng)絡(luò)的一體化,全方位多層次的強(qiáng)大力量使得手機(jī)具備了精神產(chǎn)品消費(fèi)的性能,“與巨大數(shù)量的手機(jī)使用者和頻繁被使用的手機(jī)各項(xiàng)功能密切相關(guān)的是一種新興的亞文化:手機(jī)文化。”[3]
(3)在校園里,手機(jī)文化的內(nèi)涵既包括大學(xué)生在通信、音樂、視頻、文學(xué)、游戲、交友等方面的應(yīng)用,而且更強(qiáng)調(diào)大學(xué)生社會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建立。由此可以看到,依靠當(dāng)今技術(shù)條件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與建設(shè),騰訊QQ、微信、微博等便捷手機(jī)操作軟件漸漸成為了人們的主要溝通方式,跨越了時空的障礙,身份地位的限制,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QQ閱讀、手機(jī)閱讀、百閱、掌閱iReader等軟件的應(yīng)用也大力推進(jìn)了學(xué)生手機(jī)文學(xué)閱讀的發(fā)展。
這樣,以手機(jī)為媒介的文化消費(fèi)就易于達(dá)到:既可以上網(wǎng)查找資料,也可以閱讀各種類型網(wǎng)絡(luò)小說使自己放松;既可以補(bǔ)充課題知識,但同樣也接受快餐文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通信軟件功能的增多,手機(jī)交友在近幾年流行起來。不同于傳統(tǒng)的QQ,如微信就具有搜索“附近的人”和“搖一搖”等功能,米聊、陌陌等同類聊天軟件也蓬勃發(fā)展。可以說,每個智能手機(jī)的使用者都能深切地體會到手機(jī)給生活帶來的變化。
而在大學(xué)校園這個特殊的環(huán)境中,大學(xué)生手中的智能手機(jī)蘊(yùn)含著更豐富的內(nèi)涵——不僅僅是物品的占有和使用,還是一種優(yōu)越感、幸福感的象征,一種追隨時尚的精神享受。在大學(xué)生的成長過程中,手機(jī)文化在學(xué)習(xí)手段上打破了學(xué)生對傳統(tǒng)印刷媒介的依賴,在思維模式上挑戰(zhàn)了主流聲音和價值觀的認(rèn)同,在個性塑造上更加突顯出創(chuàng)造性和創(chuàng)新意識。因而在高科技化、大眾化的文化氛圍中,大學(xué)校園的手機(jī)文化消費(fèi)是一個放大鏡,一副全息攝影圖,它能清晰而鮮明地將當(dāng)今的文化特點(diǎn)呈現(xiàn)出來。
2 新疆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文化現(xiàn)狀調(diào)查的對象、內(nèi)容和方法
2.1 調(diào)查對象
本次調(diào)查以新疆大學(xué)在校的漢族學(xué)生和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為主要調(diào)查對象,采用隨機(jī)抽樣和整群抽樣相結(jié)合的方法展開研究。首先,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則,確定漢族、維吾爾族、其它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問卷調(diào)查數(shù)量各占33.30%。其次,按照均衡性別比例的原則,做到男女生的調(diào)查人數(shù)各占50%。再者,在本科四個年級間的調(diào)查比例關(guān)系為:大一為13.30%、大二為20%、大三為33.30%、大四為33.30%。最后,將在校內(nèi)隨機(jī)抽取人員作為本次調(diào)查的調(diào)查對象發(fā)放問卷。本次調(diào)查共抽取了300人,其中發(fā)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300份,無效卷數(shù)為零(無效卷數(shù)主要是指被調(diào)查問卷填寫不完整,缺10項(xiàng)以上的),有效率達(dá)100%。
2.2 調(diào)查內(nèi)容
在參閱了大量文獻(xiàn)資料和研究報告的基礎(chǔ)上,編制了《新疆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文化調(diào)查問卷》。問卷包括新疆大學(xué)生手機(jī)使用現(xiàn)狀,學(xué)生手機(jī)消費(fèi)偏好特點(diǎn),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消費(fèi)群體特征三大內(nèi)容。問卷設(shè)置了20個問題,從手機(jī)的使用者的性別和族別來展開調(diào)查。具體內(nèi)容如下:
(1)大學(xué)生手機(jī)使用現(xiàn)狀:此次調(diào)查內(nèi)容為大學(xué)生手機(jī)使用現(xiàn)狀,目的是針對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的手機(jī)擁有狀況,與之相應(yīng)的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每月手機(jī)消費(fèi)狀況,以及手機(jī)使用時長。以此研究學(xué)生在新疆大學(xué)上學(xué)期間形成的手機(jī)使用特點(diǎn)。
(2)大學(xué)生手機(jī)消費(fèi)偏好特點(diǎn):調(diào)查內(nèi)容為大學(xué)生手機(jī)消費(fèi)偏好,目的是針對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關(guān)于購買的手機(jī)的價位、款式和品牌的選擇,以及大學(xué)生使用手機(jī)的不同的文化功能的偏好,研究大學(xué)生在日常學(xué)習(xí)生活中所形成的手機(jī)消特征。
(3)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消費(fèi)群體特征:調(diào)查內(nèi)容為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消費(fèi)群體特征,目的是針對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購買手機(jī)時對不同語言類型的系統(tǒng)和應(yīng)用軟件的選擇偏好,研究新疆大學(xué)這個多民族構(gòu)成的群體環(huán)境中在考慮到語言類和非語言類專業(yè)的因素下所形成的手機(jī)消費(fèi)群體特征。
2.3 調(diào)查方法
本次調(diào)查選擇在周末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主要在圖書館的自習(xí)廳進(jìn)行,在發(fā)放問卷調(diào)查前,說明問卷作答要求,被調(diào)查者當(dāng)場作答,完成問卷后,及時收回問卷,并及時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和分析。同時,為了增強(qiáng)調(diào)查結(jié)果的可靠性,項(xiàng)目組還增加了個案訪問(訪談)。即:由訪問者向被訪問者提出問題,通過被訪問者的口頭回答的形式來記錄收集信息。以此來突顯此次調(diào)查的完整性,通過這兩種研究方法達(dá)到問題的互補(bǔ)。一方面,通過問卷調(diào)查可以了解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手機(jī)消費(fèi)的狀況,得出一般結(jié)論;另一方面,通過個案訪談可以彌補(bǔ)問卷調(diào)查中未涉及的問題,進(jìn)行面對面的交流溝通,清楚真實(shí)地了解被調(diào)查者實(shí)際情況,從而使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完整與真實(shí)。
2.4 問卷的可信度分析
在《大學(xué)生校園手機(jī)文化調(diào)查問卷》的設(shè)計(jì)中,調(diào)查小組參考了大量的資料,例如《山西大學(xué)商務(wù)學(xué)院學(xué)生校園消費(fèi)水平調(diào)查問卷》、《2013大學(xué)校園4G手機(jī)消費(fèi)問卷調(diào)查活動》。本次調(diào)查主要采用“小樣本調(diào)查”,對問卷的實(shí)用性進(jìn)行考察,基于考察結(jié)果的合理性,項(xiàng)目小組對問卷調(diào)查的設(shè)計(jì)方案、呈現(xiàn)方式和填寫方式不斷改進(jìn)完善。為了彌補(bǔ)由于問卷設(shè)計(jì)者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所出現(xiàn)的部分題目不能窮盡所有可能性的問題,因此在有些題目上會增加筆者自己滿意的選項(xiàng)。問卷設(shè)計(jì)調(diào)查對象盡量做到問卷全面反映所要研究的內(nèi)容,做到題目表達(dá)言簡意賅,答案準(zhǔn)確單一,敏感問題委婉,立場問題鮮明。
3 新疆大學(xué)校園手機(jī)文化現(xiàn)狀調(diào)查的結(jié)果與分析
3.1 手機(jī)消費(fèi)狀況調(diào)查
在對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的手機(jī)消費(fèi)水平調(diào)查中,所涉及內(nèi)容有:每月手機(jī)消費(fèi)費(fèi)用、手機(jī)購買費(fèi)用、手機(jī)更新周期、手機(jī)選擇偏好。調(diào)查的結(jié)果顯示:63%的學(xué)生每月生活費(fèi)用處于500~1000元之間,而53.3%的學(xué)生每月手機(jī)費(fèi)用介于40~70元之間。由此可以看出,學(xué)生每月的手機(jī)費(fèi)用占生活費(fèi)的10%左右。并且,手機(jī)價格和自身生活費(fèi)之間存在一定的比例關(guān)系: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生活費(fèi)用大于等于1500元的人數(shù)占總?cè)藬?shù)的3.3%;購買手機(jī)價位在1500元以上的學(xué)生占總?cè)藬?shù)的20%;大學(xué)生每月生活費(fèi)用在1000~1500元之間的學(xué)生占總?cè)藬?shù)的23.3%;大學(xué)生購買手機(jī)費(fèi)用在1000~1500元之間學(xué)生占總?cè)藬?shù)的56.7%。
由此本文認(rèn)為,高價位手機(jī)是大學(xué)生普遍的選擇。這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類是生活費(fèi)用高,手機(jī)的消費(fèi)水平也高;另一類是生活費(fèi)用低的學(xué)生也選擇了高價位手機(jī)。相對而言,后者更引人關(guān)注。經(jīng)過個案訪問得知,他們選擇高價位的手機(jī)大都是因?yàn)槭艿綇V告宣傳以及周圍同學(xué)使用手機(jī)價位的影響。在他們看來,這事關(guān)個人的面子和品味,可以帶來心理上的滿足感以及使用時的愉悅感。也就是說高價位手機(jī)消費(fèi)的快感使得他們在精神上得到極大滿足。
基于此,本文認(rèn)為隨著手機(jī)的更新?lián)Q代,大學(xué)生的消費(fèi)觀也發(fā)生了變化,大學(xué)生不僅在意手機(jī)的使用價值,而且更注重品牌給自己帶來的精神愉悅的享受,手機(jī)作為一種標(biāo)識“幸福”的符號,讓每個大學(xué)生有機(jī)會平等地消費(fèi)。
而對于大學(xué)生手機(jī)更新周期這一問題,本文的調(diào)查問卷設(shè)定了三種情況:(1)從未換過;(2)一年以內(nèi);(3)一年以上。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其中3.3%的學(xué)生從未換過;30%的學(xué)生更換手機(jī)周期為一年以內(nèi);66.7%的學(xué)生更換手機(jī)的周期為一年以上。由此,結(jié)合上文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購買手機(jī)和每月手機(jī)的通訊消費(fèi)費(fèi)用并不占大學(xué)生的生活費(fèi)用的主要部分。而對于“手機(jī)偏好”這個問題,設(shè)置了三道選擇題,而這三道題的回答顯示:通常大學(xué)生更換手機(j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手機(jī)壞了”,其次是“看上了其他手機(jī)”,選擇“手機(jī)過時了”與“顯示身份”選項(xiàng)的人數(shù)占比例最小。對于手機(jī)款式的選擇,“觸屏”手機(jī)成為首要選擇。在手機(jī)的“品牌、價位、功能、外觀、評價”的排序中,最注重的是手機(jī)的品牌,功能、價位緊隨其后。
由此說明,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對于手機(jī)選擇是出于手機(jī)實(shí)用價值的考慮,一般接受性價比高的手機(jī),手機(jī)消費(fèi)觀理性而不盲目。但結(jié)合訪談的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對手機(jī)更換原因和使用問題的關(guān)切上,智能手機(jī)的品牌問題凸顯出來了:大學(xué)生普遍認(rèn)為品牌手機(jī)的后臺技術(shù)支持使得操作更方便,而技術(shù)落后則是“手機(jī)壞了”的真正內(nèi)涵。可見,在當(dāng)代大學(xué)生的消費(fèi)心理中,已經(jīng)潛在地關(guān)切到了在商品的消費(fèi)背后延伸出的符號意義和文化內(nèi)涵。而手機(jī)文化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蘊(yùn)含著由需要所承載的實(shí)用性,同時它也包含著對廣大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意識灌輸和培養(yǎng),即追求高品質(zhì)的物質(zhì)享受,以此來表達(dá)自身的特殊性。
3.2 手機(jī)使用狀況研究
本文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手機(jī)是每個學(xué)生的必備品,在校大學(xué)生基本上都選擇手機(jī)作為主要的通訊工具。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學(xué)生每人一部手機(jī),其次是擁有電腦的學(xué)生占總?cè)藬?shù)的75%,而電子詞典占和MP3/4/5的學(xué)生占總?cè)藬?shù)49%。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同時擁有電腦和手機(jī)的人數(shù)占70%,只有手機(jī)的人數(shù)占20%,而漢族學(xué)生擁有三件以上電子產(chǎn)品的人數(shù)占60%。
本文又調(diào)查了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使用手機(jī)時長問題。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使用手機(jī)時長在兩個小時以上的人數(shù)為236人,約占總?cè)藬?shù)的79%。兩小時以下的人數(shù)只有64人約占總?cè)藬?shù)的21%。這說明大學(xué)生對手機(jī)的依賴程度很高。其所使用的手機(jī)功能首先包括通信、瀏覽網(wǎng)頁、手機(jī)游戲、學(xué)習(xí),其次是手機(jī)下載、手機(jī)購物、閱讀電子書、看視頻。在調(diào)查問卷設(shè)計(jì)的“選擇手機(jī)媒體的原因”這一問題中,大多數(shù)被調(diào)查者選擇:方便聯(lián)系、獲取資訊和學(xué)習(xí)、生活娛樂。少數(shù)選擇緩解壓力、消磨時間。由此可見,手機(jī)已經(jīng)成為大學(xué)生校園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電子詞典等電子設(shè)備已經(jīng)漸漸地淡出了學(xué)生的生活,功能多樣的手機(jī)漸漸取代其他電子產(chǎn)品和紙質(zhì)材料的地位。
在本次調(diào)查的第19題和20題中,提出了“是否含有或使用非漢語的軟件通信和瀏覽網(wǎng)頁”的問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選擇使用非漢語軟件的原因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33.3%的學(xué)生是因?yàn)椤吧贁?shù)民族不能順暢地使用漢語軟件”;26.7%是因?yàn)椤白詫W(xué)其他語種的需要”;40%的學(xué)生是由于“專業(yè)的需要”。而在使用非漢語軟件的學(xué)生中90人是少數(shù)民族,而其中50個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是因?yàn)椴荒茼槙车厥褂脻h語交流而選擇民族語輸入軟件。除此之外,手機(jī)使用非漢語軟件的學(xué)生中有40個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和60個漢族學(xué)生,他們主要是為了加強(qiáng)專業(yè)素養(yǎng)以及自學(xué)其他語種的需要來使用非漢語軟件通信和瀏覽網(wǎng)頁。
可見,目前開發(fā)的非漢語軟件是有一定的市場,而一定程度上手機(jī)軟件的使用成為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的一部分,學(xué)生能夠主動使用非漢語軟件進(jìn)行自學(xué)和專業(yè)學(xué)習(xí)。從少數(shù)民族使用的軟件語言來看,新疆大學(xué)學(xué)生雖然要求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進(jìn)行HSK的普通話等級考試,但還是有很多人依然不能順暢地使用漢語,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仍然存在,少數(shù)民族在使用自己母語時還有必要繼續(xù)提升漢語水平,也有一些學(xué)習(xí)外語的少數(shù)民族同學(xué),他們也選擇了非漢語軟件。此外,有些漢族學(xué)生使用非漢語軟件則是因?yàn)閷I(yè)的需要,下載了相應(yīng)的語言和使用相應(yīng)語言的軟件。還有一些學(xué)生對自己要求較高,自學(xué)其他語種提升自身語言水平。在大學(xué)校園里,尤其是新疆大學(xué)處于民族和文化交融的環(huán)境中,學(xué)生所使用的手機(jī)也反映出不同的選擇偏好,這些都來源于學(xué)生的民族特性,專業(yè)區(qū)別以及個人愛好。整體來看,手機(jī)已然成為現(xiàn)代學(xué)生學(xué)習(xí)交流、溝通娛樂的實(shí)用性極強(qiáng)的設(shè)備。
綜上所述,新疆大學(xué)的學(xué)生手機(jī)占有率達(dá)到了100%,從手機(jī)的使用時長來看,他們對于手機(jī)依賴程度比較高;一般使用手機(jī)獲取信息和學(xué)習(xí),其次是娛樂,手機(jī)已經(jīng)成為大學(xué)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對于手機(jī)的消費(fèi)更加看重其使用價值,是一種求實(shí)消費(fèi)觀念。相比之下漢族學(xué)生較多的受到了社會時尚潮流的影響更注重手機(jī)消費(fèi)帶給自己的精神享受。此外,基于新疆大學(xué)獨(dú)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傾向于使用民語軟件,這一方面源于大部分的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不能順暢地使用漢語,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他們更注重傳承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心態(tài)。此外,還有少部分漢族學(xué)生也在使用外語軟件幫助自己深化專業(yè)學(xué)習(xí),如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等語言專業(yè)都是國家重點(diǎn)支持的專業(yè),它的招生對象是面對漢族學(xué)生的,因而對于漢族學(xué)生來說,使用民語軟件是提高自己少數(shù)民族語言水平的很好選擇。學(xué)習(xí)其他語言的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亦可通過非漢語軟件提升自己的學(xué)習(xí)效率。可見手機(jī)對于大學(xué)生的專業(yè)學(xué)習(xí)也具有實(shí)際意義的幫助。通過訪問得知,周圍多數(shù)大學(xué)生手中的手機(jī)已經(jīng)不是第一部,換了又換的手機(jī)現(xiàn)象,顯現(xiàn)出了大學(xué)生對社會化身份的渴求和一定程度的心理貧困,而這種情緒源于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要求,以及突出個性化特征的迫切愿望。
總之,在當(dāng)今的文化氛圍下,智能手機(jī)在校園廣泛使用首先豐富了大學(xué)生的校園生活,便于大學(xué)生及時溝通、下載、游戲、學(xué)習(xí),而伴隨著手機(jī)應(yīng)用技術(shù)的推陳出新,手機(jī)的實(shí)際價值又大大超出了實(shí)用范疇,而成為滿足使用者社會化精神需求的文化要件。一言以蔽之,當(dāng)代大學(xué)生借力手機(jī),通過這種物化了的人際溝通形式走向社會認(rèn)同、形成自我人格,在符號化的交際時代探索、嘗試、開拓、成長。
[1] 羅鋼,王中忱.消費(fèi)文化讀本[M].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3.
[2] (英)邁克·費(fèi)瑟斯通.消費(fèi)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M].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
[3] 巨斯巍.淺談手機(jī)文化的定義及特點(diǎn)[J].知識經(jīng)濟(jì),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