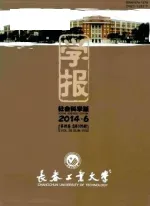新世紀文學的命名、鬼畫符及其他
陳紅旗
(嘉應學院 文學院,廣東 梅州514015)
新世紀文學的提名由來久矣,早在1993年就有學者著文《呼之欲出的新世紀文學》[1]為新世紀文學的即將面世助勢張目,更有著名作家荒煤力主“新世紀的文學要真正站起來”:“在21世紀,中國人民不僅要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巨人屹立于東方,中國人民還必將把這個社會主義新的經濟巨人的光輝形象,通過文藝創作,震撼人心地傳遍世界!”[2]接著,有學者指認“知識分子”是新世紀文學的“新主角”。[3]及至2005年《文藝爭鳴》推出“關于新世紀文學”專欄、2010年《南方文壇》開展“網絡文學”討論和“新時期與新世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海南召開以來,“新世紀文學”的先鋒性、包容性、多元性、斷裂性和存在意義被不斷挖掘出來。在諸多精英作家的心目中,新世紀文學是一個精英文學的新紀元或“創世紀”的精英文學的新開端。然而,不管學術界關于“新世紀文學”的討論如何熱烈,不管新世紀文學的發難者、倡導者如何呼喚“創新”、精英和經典的出現,十多年來的精英文學并未出現多少值得學界公認的經典作品,也未表現出與20世紀文學界的深刻和21世紀新媒體的新銳相襯的思想水平與勃勃生機,即使莫言獲得諾獎也不意味著問題的消失,倒是原來被大家無視乃至蔑視的網絡文學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大有取代純文學和市場化文學而成為文學主流的趨勢。這是新世紀文學發展十年之后,主流文壇頗為困惑的所在,也是學術界應該去直面的重大問題。
一、“新”飾語加新命名,一個世紀的文學的新開端?
新世紀以來,文藝界出現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精英文學作品,似乎非常生動地驗證了作家劉玉堂在世紀初對新世紀文學的想象圖景:“想象中的新世紀的文學,文學含量將會更高,生活信息將會更加豐富,表現形式上則會有快餐,更有經典;有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人性、愛情、戰爭、自然等依然會是文學的主題。”[4]問題在于,主題的豐富不代表經典的生成,而閱讀上述作品后,我們甚至會有些驚詫:這些作品確實很優秀,但它們真的值得我們學界的一流批評家為之設定“富有經典性”的評語嗎?莫言獲得諾獎能夠平息那些對新世紀文學的質疑嗎?那些曾經引領過時代風潮的先鋒作家的沖勁哪里去了?假如新世紀以來的精英文學只靠莫言等少數作家撐著,而大多數嚴肅文學作家難以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創作水準的話,那么我們還有必要為“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敘事文學的輝煌時代就要終結了”[5]而感到傷悲嗎?
丁帆曾直言不諱地強調學界應該針對新世紀十年來的文學病癥進行會診,以便為今后文學的發展及早糾偏。同時,他對新世紀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存在的“二十二條”問題進行了極為尖銳、深刻和全面的剖析:“(一)有些主流作家對事件和事物的判斷力下降,這不僅是思想能力的退化,同時也是審美能力衰退。……(一)第一種批評家:圍繞各種‘工程’與‘獎項’為體制與市場需求做吹鼓手和抬轎者,其最終目的就是使自身成為世紀初文學大餐中的既得利益者。……”[6]由此看來,面對《萌芽》、《十月》、《天涯》、《北京文學》等純文學刊物銷量的持續萎靡和創作界拜金主義思想橫行等亂象叢生的現實,我們確實還無法為新世紀以來的精英文學設定更高的藝術水準、精神品格和經典視域。
毋庸置疑,新世紀以來的一大批精英文學實踐者和倡行者是非常關心民族國家命運或底層民眾生存境遇的,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也一直在嘔心瀝血地寫作,所以陳忠實在《白鹿原》登上話劇舞臺后心血耗盡,不由自主地發出“我寫不了長篇了”[7]的慨嘆。然而,陳忠實“十年磨一劍”的做法并未被諸多新世紀文學創作者所認可,甚至一些精英作家也開始主動“媚俗”,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搶占市場份額,追求創作的利益最大化。結果,21世紀的精英文藝界存在著大量立寫立變現的功利行為和輕易將情感庸俗化或再現為形象的亂象,不再年輕的寫手們不斷重寫著他們過去的臆想和想象,并糅之以自身并不真切的摯情。問題還在于,他們太相信自己的感覺和體驗了,他們以最快的速度生產著各類作品,而在他們快速寫作的背后,文學創作的神圣感日漸消解,甚至充溢著對文體乃至文學的輕僈。結果,當后輩的文學愛好者想向這些精英作家學習寫作經驗時,他們從這些前輩的諸多創作體會里所得到的,既不是經典寫作的精髓,也不是市場化寫作的謀略,而是某些冠冕堂皇的理論、說辭和借助市場炒作獲取利益的小智謀。這顯然與新世紀文學發難者的期望值相去甚遠,也背離了新世紀文學起初被寄寓的世紀性、全球性、人類性等終極理想訴求,形成了奇特的意圖謬誤現象,進而引來了關于這一概念名實不對應、“大而無當”[8]等令人難以辯駁的多重質疑。
二、網絡文學的壯大讓主流文壇的說教淪為“鬼畫符”
從“媒介革命”的角度來看,21世紀以來站在“新”或“全球化視域”一面的精英作家仍然“重視”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內容的成分,但變革文學形式的沖動明顯在減弱,其標志就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日趨平靜、曲高和寡或曰“回歸自身”。與精英文學的日漸“萎靡消沉”相比,“新媒體文學”(主要是網絡文學)的興起速度之快、銷售量之巨和受眾面之廣都令人驚嘆。在某種意義上,網絡文學成了新世紀文學的希望所在。
從文學生產的角度來看,新世紀已成為最重視媒介元素的時代。毫不夸張地說,以往需依托于報紙、雜志和副刊才能成名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相反,一條微博可能帶來的幾百萬次的點擊量和極高的跟帖率以及難以估量的轟動效應完全顛覆和消解了紙質傳媒的神話。由于新媒體和文學生產的結合還是一個“新生”事物,所以熱衷于在新媒體上發表作品的作者們還沒有20世紀精英作家們那種形式的覺悟,他們更在乎的是情感的傾訴、剎那的感悟、即興的言說和受眾的反應,真正注重文學結構和詩學建構的沒幾個。就算是有一些作品有嚴肅的思想主題和明晰的“詩化”傾向,也往往被輕易淹沒在作家身份日益淡化、非專業化和文學出版“大躍進”的數字化浪潮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就是這些駁雜的網絡文學作品彰顯了民間寫作的力量和活力,它們沖破了20世紀思想文藝界的藩籬,為文壇帶來了巨大沖擊、新鮮氣息和海量文本。
新世紀文學須完成“文學走向新世紀”的“絕對命令”。對于正統文藝界來說,剛剛過去十年就談文學新世紀未免太過倉促和盲目了。但實際上,“文學新世紀”已經走完了其開端或曰發難階段,而這一任務就是由網絡及其所刊載的網絡文學所實現的。網絡既不同于古代口耳相傳的“說書”式傳播手段,也不同于報紙雜志副刊這類現代文學生產媒介,它正在悄悄地消解乃至取代書刊的重要地位,這并非聳人聽聞。要知道,對于廣大網民來說,與其花費幾十塊錢去買一本“蝸居時代”無處存放的紙質書刊,何如到百度文庫里下載來得輕松寫意和經濟實用。還值得深思的是,如果21世紀的作者們正在從事用網絡文學來超越或替代書刊這一文化工程的話,他們無須憑借任何本來就沒有的前人經驗,他們只要能夠輕松進入這個新生代的網絡世界就可以完成這場“文學傳播革命”,其難度似乎僅僅大于讀完初中甚至小學語文課程。更具諷喻意味的是,這本來是極其令人震撼的一個社會工程,可真正令人震驚的是網絡文學推手們開展這項工作的輕松隨意性以及文學的概念、邊界、主體、讀者、功能、體驗、空間和內涵的急劇擴大。事實上,“文學的生產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文學的本質”,[9](P18)一旦網絡被高水平的文學作者和讀者們普遍接受之后,網絡將決定未來文學的生產方式,那么它勢必將在未來文學生產的調度中處于樞紐地位。而“手機文學”、“網絡文學”等名詞不僅說明了文學活動與新媒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也意味著網絡打破了地域、時空和傳統媒介的隔絕形成了新的社會有機體。可以說,當下諸多的文學活動就是在這種網絡空間中開展的,而新的文學流派和主體力量也勢必會在這種網絡空間中成長起來,并以其“絕對”的自由特性成為一股“難以控制”的新生力量。
網絡文學在中國的興起是與中國現代化工程的快速發展緊密相關的。網絡文學的誕生是為了適應中國廣大網民積極參與文學書寫的精神訴求的結果。從90年代中國開始普及互聯網到當下網民的幾何級增長,網絡文學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文空間和非同人性質的文學社群。據推算,2011年底中國網民總數將超過5億,互聯網普及率將升至36.2%。網絡將無數愛好文學的個體組成了一個以網民為身份認同前提的共同體——一種松散的虛擬而又實存的新的社會結構組織。同時,網絡推動社會思想文化向“新世紀”的價值認同演進,往往一個網絡事件就代表或揭示了一種新的社會心理、思維邏輯乃至意識形態的生成。網絡改變了人們的身份,改變了“創作”的神秘性,改變了人們的審美心理圖式和閱讀習慣以及接受之維。就此而言,網絡文學的涉及面可謂廣之又廣。是故,錢建軍在上世紀末著文強調說:“網絡文學給人們帶來的沖擊,不僅僅是寫作方法的問題,而是牽連著諸如法律、責任以及觀念等許許多多的問題。嚴格地說,它是涉及了本世紀末一個最大的社會問題。正是因為網絡文學所具有的重大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使其在不遠的將來,將超越書本和報紙雜志的閱讀和普及,它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將顯示出日益深刻的革命性的影響。”[10]顯然,錢建軍發現了網絡在21世紀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社會意義,并將它放在文化革命的層面上來加以認同,這并非偶然,而后來的事實也驗證了他的這一價值判斷。在當下,網絡越來越直接地導引著國民的價值取向,網絡文學則越來越直接地影響著新世紀文學的發展走勢。
隨著網絡的普及和網絡文學受眾面的駁雜化,文學寫作越來越被非專業化。網絡推動和加快了文學內容、形式、流派和現象的演變。網絡一方面加強了網民對類型文學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又導致文學論爭的不斷上演和文學大事件的迅速發生。而網絡文學徹底改變了現代文學在啟蒙、救亡、改造國民性、民族化、現代化主題背后的嚴肅格調和憂世情懷。通過網站無形的運作和推動,使得“灌水”、“造勢”、“圍觀”、“神馬”、“浮云”等術語和網絡文學一起流行起來,并開始深刻影響人們的認知邏輯和審美觀。在“二余之爭”、“直諫陜軍”、“直諫池莉”、“文學存在理由”討論、“新世紀文學五年與文學新世紀”研討會、“網絡文學”的“再發展”與“中國作協”的“被關注”[11]等文壇事件和文學論戰中,網絡扮演了直接的推手角色。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網絡這種新媒體的參與、炒作,這樣一些本來并不見得有多么重要的事件和論戰居然會成就一場場的文學狂歡。其實,這些事件和論爭的背后就是“網絡之戰”。在這些“網絡之戰”中,網絡的消解力量之大令人咋舌。比如,在“中國作協”的“被關注”事件中,網民中的“憤青”似乎一夜之間就將中國作協由“權威機構”和“合法的作家聯合體”變成了一個“中國足協”式的“病入膏肓”的“腐敗組織”。在當代中國,網絡將文學論爭如海嘯一般推出,將數以百萬計的網民卷入了諸多沒有實質意義的口水戰、情緒戰和“語言游戲”之中。
21世紀以來,文學論爭中巨量的非理性的“拍磚”和酷評令傳統意義上的主流文壇尷尬不已。本來,由作協、文聯和報紙雜志書刊構成的主流文壇一直在代表文藝界發出權威聲音,它們既是文學作者們學習寫作和發表作品的重要陣地,也是文學讀者閱讀作品和了解文學發展動態的直接窗口。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一直強調文學研究要回到文學本身,要從文學本體的角度來構建完整的有內在發展邏輯的文學史。在這一過程中,文學媒介的效用往往被忽略了。可如今我們已經無法忽視作者與新媒體之間的關系,因為對于那些網絡寫手來說,網絡就是他們的文壇、生存空間和實現志業的平臺。網絡最大的特點是自由、平等、快捷、方便、同步無延時,它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兼收并蓄的話語空間。網絡世界不僅比主流文壇有趣得多,而且形式和內容也豐富得多。網絡以最通俗化的姿態和形態擁抱大眾,真正實現了“大眾化”。在當下,正是網絡把最廣博的知識和消息以立體化的方式傳播開去。網絡為大眾提供了全方位接觸文學和文化的機會與可能性,而且網絡是最接近和代表人民立場的公共空間,是最能體現人民性和延展人民話語權的世界共同體。
在生存壓力巨大的中國,盡管經濟學家和政客們想盡辦法讓國民去消費,但限于高房價、低社保、殘醫保和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率,傳統意義上的個體購書等文學消費率低得可憐。相對昂貴的書價將讀者拒之門外,于是廉價或免費的文學網站格外受到讀者的青睞。當然,文學網站也傾向于市場化和商業性。文學網站的運作同樣具有明顯的商業運作的特點和軌跡,為了吸引人們的眼球,從名流到草根都有可能成為這個“新生世界”的商業籌碼。文學網站可謂包羅萬象,它們快捷而敏銳地把各種類型的作家、作品搜集在一起,輔之以“聲色犬馬”的圖片、音頻、視頻,然后分門別類地把各色內容的文本鋪展開來,并且以比現實世界更井然有序的商品陳列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讀者可以依據自己的愛好隨意挑選各風格、流派、題材、體裁、類型、品牌的作家和作品。同時,文學網站的更新效率極高,它們以最快的速度把各類文學作品、文學寫手、文壇消息和文藝動態大力推出。以長篇小說為例:“自2004年網絡文學收費閱讀模式產生以來,長篇小說逐漸作為網絡文學的主導文體。網絡長篇小說創作內容、形式多種多樣,學界統稱為類型文學,大致可分為:架空穿越類(現代人通過時光交錯進入特定的歷史時期,運用自身經驗改變歷史進程)、玄幻科幻類(區別于西方魔幻小說的東方本土幻想小說)、都市青春類(反映現代都市生活、表現現代情緒的小說)、官場職場類(以官場博弈和職場奮斗為題材的小說)、游戲競技類(根據網絡游戲改編或具有網游特征的小說,一般采用晉級形式)、靈異驚悚類(以鬼怪或探險為題材的小說)、新軍事類和新武俠類(區別于傳統軍事和武俠的小說,添加幻想成分)等。”[12]以是觀之,正是那些不斷滾動發展的網站推動或制造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話題、文學論爭乃至文學思潮。
如今,文學網站的市場化、商業性和全球化謀略正在起到逐漸弱化乃至替代主流文壇的效用,甚至可以說,文學網站的收購和壯大構成了新的文壇。文學網站的商業性質決定了它們必然以讀者為中心,它們非常自覺地強化著自己作為服務者的姿態,讀者被真正當做“上帝”來對待,它們把“迎合讀者的心理和趣味”作為網站運營的終極法則。就這樣,文學網站最大程度地滿足了讀者消遣和娛樂的精神訴求。當然,每一個網站都有它的辦站原則和價值取向,即使是號稱“以讀者為本”的網站也在吊起、調劑乃至制造著讀者的胃口。2010年,盛大文學公司相繼收購了“小說閱讀網”、“瀟湘書院”、“悅讀網”等三家文學網站,使得旗下的文學網站多達九家,圖書策劃出版公司達到三家,從而確立了自己“網絡文學寡頭”的地位。2010年12月的數據顯示:盛大文學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民營出版公司。按照該公司的說法:“盛大文學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中國網絡文學,已經與世界性寫作同步,正在構建一個恢宏的想象力世界。盛大文學將以這些豐富的內容為核心,打造中國最大的全版權運營基地。”[13]更令人震驚的是,盛大文學提出了“打造全球華語小說夢工廠”的口號,并力圖引領和制造小說領域的時尚和潮流。盛大文學等公司的成功運作,不僅意味著網站為讀者和作者的交流互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還意味著它們為文學寫手們提供了天馬行空的自由創作空間,更意味著商業資本依托文學網站構建了富有后現代氣息的人文空間并打破了以往報紙雜志副刊構建起來的“文人圈子”,進而使得以往的文學概念界定已經涵蓋不了今天的文學現象,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界在面臨今天的網絡文學或語言時難免會尷尬乃至失語。
如果說,20世紀中國文學是在紙質傳媒和書房這類私密空間里和讀者大眾直接發生關系的話,那么新世紀文學多是在新媒體和網絡這種公共空間里與讀者發生親密關系的。每個網民都可以成為某一文學網站的寫手,只要他有書寫的欲望、發表的想法和相應的寫作能力。如此看來,網絡寫作已經成為被商業資本控制或組織起來的精神生產和娛樂方式之一,它將不可避免地指向虛擬世界和世俗人生,而非精英文學所指向的詩意棲居之地。與此同時,新世紀的文學作者們再也無法離開網絡、手機等新媒體,他們不用再孤獨地躲在象牙塔里為現實中可能需要直面的讀者來寫作了,他們可以群體合作或曰以某一類文學風格為模板進行“類型文學寫作”。他們的產品需要被填充在網站的某一框架之下,并被預告將納入某類人群的消費意志之下,而不是要去建構純文學性或者生發某種新的藝術體驗。當然,如果有利于提高消費額度,后者也是可以的。至此,“文學的流行”被不停地制造著,網絡運作成為一種制約文學發展或曰使文學發展充滿變數的無形力量,而傳統意義上的主流文壇很難輕易獲得網民的無條件認同或皈依了,他們在西方文論光鮮外表包裹下的主義、思想、名詞、流派和說教通通成了“網絡憤青”眼中的“鬼畫符”,他們需要重新確立自我認同、網絡身份、社會角色和文學觀念。
三、新世紀文學的發展,“強勁”還是“乏力”?
新世紀文學不僅僅是指網絡文學,它還包括一切以“新世紀”為價值旨歸的其他文學形態、內容、形式、慣例和審美主體。不過,網絡文學確實是新世紀文學中最有代表性和發展前途的一種文學形態。而今,每一個作者都深知網絡的催化劑效用。新世紀以來,陸續有大牌作家、專業作家在網站上進行博客寫作,比如虹影、柯云路、劉醒龍、余華等,這就是非常有力的例證。盡管如此,對網絡文學不屑者仍然大有人在,有人認為網絡文學中90%以上的作品都是垃圾。也有學者從學理的角度表達了對網絡文學的不認可:“我對網絡文學這種命名方式持質疑態度。如果說有網絡文學的話,也只能說是文學的傳播媒介發生了變化,寫作方式與原有的傳統方式不太一樣,但文學觀念并沒有根本的改變。”[14]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也非常有代表性,不過是有問題的。毫無疑問,網絡文學魚龍混雜、精品稀少,所以難免會令人對其產生不屑感,但不認可其強勁發展勢頭背后文壇格局的改變是不應該的。筆者認為:網絡文學的發展已經改變了以往學界認定的文學認知體系,并帶來了文學觀念的深刻變化,簡而言之就是:沒有人是作家,也沒有人不是作家。
我們知道,20世紀的作者多是專職作家,可如今民間寫手在數量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所謂的專職作家。據統計,目前我國的網絡經常寫手達170萬人之多。就長篇小說創作的總體情況而言:“從事網絡長篇小說創作的作者幾乎沒有傳統作家,75%為40歲以下的青年,他們散布全國各地,有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邊遠地區,這為豐富全民文化生態發揮了積極作用。從數量上看,網絡長篇小說的產量大大超過傳統寫作,每年達3000部以上,在每年落地出版的兩三千部長篇小說中,大約有一半來自網絡。網絡小說在版權輸出中也占有相當份額。在商業收費模式的推動下,依靠網絡寫作生存的網絡職業寫作者隊伍已經超過了各地作協的專業作家隊伍。”[12]更不可思議的是,網絡文學的銷售量和影響力實在太驚人了,比如,僅龍人的玄幻武俠小說發行量就達3000萬冊,網絡上的點擊率達十億人次。再如,被譽為“最激勵人心的職場生存小說”——《浮沉》在2007年9月底出現在新浪原創和天涯社區之后,點擊率很快突破百萬,回帖超過數千,其他數百個網站紛紛轉載,數十家出版機構致電詢問小說的版權歸屬。數以萬計的《浮沉》粉絲以各種形式結成聯盟,討論該書以及神秘作者京城洛神。如今《浮沉》熱仍在繼續。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對于這樣的情況,我們用一個俗套的網絡流行語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太“給力”了。網絡文學以其強悍的發展情態、令人炫目的發展前景和雄厚的創作實力直接撐起了新世紀文學的天空。更值得深思的是,網絡文學所帶來的已不是基于期望值高低而形成的價值判斷是否存在偏頗性的問題,而是它作為一種在新的傳播媒介和生產方式下產生的文學形態已經深深地改變了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性質和文學批評的范疇。
至此,我們認定:在關于網絡文學的研究或批評聲浪里,不管學人如何抨擊這種文學形態的粗鄙性、通俗性、商業性、民間性、駁雜性等問題,都不得不承認文學網站正在把網絡文學不斷做大,從而形成了不可忽視的“文學潮流”和“時代精神”。在當下,很少有純文學刊物僅僅依托于傳統的發行——運輸——銷售——被閱讀的方式來生存了,它們都要建立網站來宣傳自己,這表明純文藝界正在努力“轉向”以順應網絡時代的流行浪潮,也意味著新世紀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在文學生產方式和文化建設取向等方面有了根本性區別,因為它正在或曰已經建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創世紀”。
[1]吳野.呼之欲出的新世紀文學[J].當代文壇,1993,(1).
[2]荒煤.新世紀的文學要真正站起來[J].文藝爭鳴,1993,(1).
[3]學正.新世紀文學的新主角[J].文學自由談,1995,(2).
[4]劉玉堂.新世紀的文學什么樣?[J].走向世界,2000,(Z1).
[5]孟繁華.新世紀:文學經典的終結[J].文藝爭鳴,2005,(5).
[6]丁帆.新世紀文學中價值立場的退卻與亂象的形成[J].當代作家評論,2010,(5).
[7]陳忠實.《白鹿原》今晚走上話劇舞臺 陳忠實:“我寫不了長篇了”[EB/OL].http://news.sina.com.cn/o/2006-05-31/09419077297s.shtml.
[8]吳思敬.“新世紀文學”,還是“世紀初文學”?——關于當下文學命名的思考[J].文藝爭鳴,2007,(2).
[9]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10]錢建軍.第 X次浪潮——華文網絡文學[J].華僑大學學報,1999,(4).
[11]白燁.新變、新局與新質——為新世紀文學把脈[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1).
[12]馬季.網絡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第二次起航[EB/OL].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4422559.html,2011-4-19.
[13]盛大文學[EB/OL].http://www.sd-wx.com.cn/introduce.html.
[14]楊揚,等.影響新世紀文學的幾個因素[J].文藝爭鳴,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