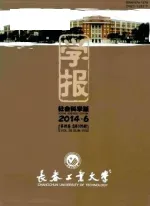論波德萊爾“應和”思想與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內在一致性
王小溪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波德萊爾的十四行詩《應和》(又譯作《感應》)是體現其“應和”思想的經典之作,被譽為“象征派的憲章”。[1](P4)詩人借助意象的交錯呼應,展現出一個充滿神性的廣袤世界。在詩歌描繪的心物交融的世界中,意義在互通共感中自然呈現。“這首十四行詩在表達一種美學見解的同時,其本身也是對這種美學見解的具體演示。”[2]然而,僅將“應和”當作象征主義文學的創作手法或窺視波德萊爾美學思想的途徑,顯然忽略了其中的哲學意蘊。筆者認為,波德萊爾的“應和”思想與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具內在一致性,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將“應和”思想視為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初級形態。
一、“應和”思想中“世界”的哲學意蘊
波德萊爾的“應和”世界,是萬物相互聯系的整體,萬物互為象征,向彼此昭顯意義,“如同悠長的回聲遙遙地匯合/在一個混沌深邃的統一體中/廣大浩漫好像黑夜連著光明——芳香、顏色和聲音在相互應和”。[3](P17)在這個世界中,“色彩說話,就像深沉而顫動的聲音;建筑物站立起來,直刺深邃的天空;動物和植物,這些丑和惡的代表,做出一個個毫不含糊的鬼臉;香味激發出彼此應和的思想和回憶;激情低聲說出或厲聲喊出它的永遠相像的話語”。[1](P73)可見,應和的世界區別于現實的世界。在應和的世界中,物我、感官的界限都被打破,意義自然流動和呈現。
波德萊爾應和的世界與海德格爾對于“世界”的觀點具有相似性。海德格爾認為“此在”的基本結構是“在世界之中存在”,[4](P61)這里的“世界”是此在“在世”意義上的世界,區別于客觀世界。“在‘在世’這個名稱中的‘世’卻絕不意味著塵世的存在者以別于天國的存在者,也不意味著‘世俗的東西’以別于‘教會的東西’。‘世’在‘在世’這個規定中的意思根本不是一個存在者,也不是一個存在者的范圍,而是存在的敞開狀態。”[5](P392)在這樣的“世界”中,人“被拋而處‘在’存在的敞開中”。[5](P392)既然世界是“存在的敞開”,而人是這世界中特殊的存在,那么,世界也是人這種特殊存在的“敞開狀態”,即世界與人之間具有了共通性。這樣的“世界”中,“‘世’就是存在的澄明”,[5](P392)即人可以從“世界”中直接體悟存在之真。正如在應和世界中,人自動接收“自然”中的“話音”,從而達到對“自然”的體悟。只有在這樣的世界中,才能透過存在者體悟到存在并追問存在者怎樣存在以及存在者存在的意義。波德萊爾應和的世界是萬物交融、意義自然呈現的世界;海德格爾的“世界”是與此在渾然一體、本真存在的世界。從這一角度講,兩者的“世界”是共通的。而且,波德萊爾希望借助“應和”揭示世界意義的想法與海德格爾透過“存在者”揭示“存在”的想法也是相似的,都是對傳統主客二分觀念的反對。
波德萊爾在《評L.德·塞納維爾的〈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中指出了詩與哲理的關系:“詩在本質上是哲理,但是由于詩首先是宿命的,所以它之為哲理并非有意為之。”[1](P8)筆者認為這句話有三層含義:首先,詩的本質是哲理,哲理以詩的形式外化展現;其次,詩先于哲理,是詩人通過“創造性直覺”[6]對具有統一性的世界的把握,旨在揭示存在之真;最后,既然詩先于哲理,那么詩絕不是對某一哲學觀點的迎合。波德萊爾的這一論述不僅使“應和”思想中的哲學意味體現得更加明顯,而且表達出了他對“詩”的獨特看法,這與海德格爾的“詩思觀”也具有一致性。
二、“應和”思想中的語言神性色彩
“自然是座廟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時說出了模模糊糊的話音;人從那里過,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識的目光將他注視。”[3](P17)“自然”中意義的呈現需要一定的方式——“話音”。這種“話音”是對應和世界中萬物本真存在狀態的直接呈現。人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在自然中時刻接受著這種“話音”傳達的意義。但由于人們習慣用傳統的主客二分觀念認識世界,未領會萬物應和之道,所以不能領悟“話音”傳達的意義。于是,揭示萬物“應和”意義的重任落到了詩人肩上。波德萊爾在《維克多·雨果》中指出:“詩人(我說的是最廣泛的意義上的詩人)如果不是一個翻譯者、辨認者,又是什么呢?”[1](P89)詩人“翻譯”、“辨認”的正是應和世界中的意義,即本真意義,而承載意義的載體就是詩的語言。海德格爾在《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中將詩人稱為語言之家的“看家人”,他說:“只要這些看家人通過他們的說使存在之可發乎外的情況形諸語言并保持在語言中,他們看家的本事就是完成存在之可發乎外的情況。”[5](P358-359)可見,海德格爾認為,詩人的任務是揭示存在之真,并將其保存在語言中。這與波德萊爾將詩人比作“翻譯者、辨認者”具有一致性。
在波德萊爾看來,詩的語言不僅要表達情感、思想,還要揭示“混沌深邃的統一體”。詩的語言作為應和“自然”中的一部分,與萬物交織且意義共通。這是其能夠揭示“自然”的前提。詩的語言揭示的對象是應和的“自然”,揭示的方式是象征。所以,在波德萊爾的“應和”思想中,意義能在“自然—應和—話音—詩的語言”四方中流轉,根源于四方間的互通性。“自然”作為本真的存在,具有“神性”意蘊,“自然”中的萬物以“應和”的方式彼此聯系,用“話音”傳遞信息。作為“自然”中特殊存在的人,體悟著“自然”的“話音”,又以“詩性的語言”揭示“自然”。
波德萊爾在《應和》中稱自然傳來的“話音”是“模模糊糊”的,可見,他對“自然”呈現的意義的理解是模糊的。在《論泰奧菲爾·戈蒂耶》中,波德萊爾指出:“在詞中,在言語中,有某種神圣的東西,我們不能視之為偶然的結果。巧妙地運用一種語言,這是施行某種富有啟發性的巫術。”[1](P73)波德萊爾敏銳地察覺到語言具有豐富的蘊藉,他將這種蘊藉視為“神圣的東西”和“巫術”。由于他并未指出萬物內部的“應和”通過詩的語言外化進而呈現意義,所以“應和”這一具有哲學意味的思想始終充滿文學氣息。
海德格爾晚期對語言、詩與思問題格外關注,他指出:“語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思的人們與創作的人們是這個家的看家人。”[5](P358)海德格爾提出的“語言—詩—思”問題與波德萊爾《應和》中“自然—話音—應和”問題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首先,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根本意義上的詩”,[7](P295)即語言是詩,所以具有詩性,這對應的正是波德萊爾語言觀中的“神圣的東西”。“海德格爾認為詩與思分別具有去蔽(Aletheia)和聚集(Logos)之特性,詩與思是近鄰,因為二者都是存在的道說,必相鄰近。從某種角度上說,詩就是思,思就是詩。”[8](P417)這里有必要對“思”進行解釋。“思”區別于日常生活中邏輯性的思考,“思是存在的,因為思由存在發生,是屬于存在的。思同時是存在的思,因為思屬于存在,是聽從存在的”。[5](P361)既然詩既思,思又是存在對世界的把握,那么,人就可以接收并理解“自然”的“話音”,并通過詩性語言表達對“自然”的體悟,而這“自然”正是應和的世界。
通過海德格爾的詩思觀,我們理解了波德萊爾“應和”思想中語言的神圣性,這種神圣性源于語言與思維的一體兩面關系。正因如此,詩的語言才能延伸到“話音”內部,將存在之真揭示出來。
三、“應和”思想中“世界”與“大地”的聯系
波德萊爾將自然喻為具有神性特征的“廟宇”。在這“廟宇”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柱子”說出了“話音”,“森林用熟識的目光將他注視”,以往作為主體的人在“廟宇”里成了傾聽者和被審視者。波德萊爾只是用朦朧的詩句來傳達自己的體驗——“如同悠長的回聲遙遙地匯合/在一個混沌深邃的統一體中”,[3](P17)并沒有揭示出“自然”具有神圣性的原因。
海德格爾這樣論述神廟:“神廟作品闃然無聲地開啟著世界。同時把這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這般,大地本身才作為家園般的基地而露面。”[7](P263)筆者認為,這段文字可以作為波德萊爾筆下自然“廟宇”的注解。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有兩大特征,即世界的建立和大地的顯現。神殿屹立于大地之上,建立了一個意義的世界,這個世界處于敞開狀態,區別于遮蔽著的大地。此在在敞開的世界中,在“神殿”光環的感召下,探尋著本真的存在。然而,神殿創造的世界是不能脫離大地的,大地是存在者存在的家園。雖然大地的本質是自我封閉的,但是這種封閉是對存在與存在者的保護,大地同時也是此在超越的根基。藝術正是世界的敞開與大地的封閉的斗爭中的承擔者,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7](P256)所以,海德格爾認為神殿作品肩負起了連接大地與世界和顯現真理的重任。在波德萊爾的“廟宇”中,同樣發生著大地與世界的爭斗。
波德萊爾以詩人的敏感感受著“自然”的蘊藉,但并未作出海德格爾般理性的論述,沒有提出邏輯嚴明的概念。在他眼中萬物都是藝術的存在,“自然”也“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大自然’,不是浪漫主義意義上那種可以讓人逃避城市生活而縱情山水的自然,而是指一種已經擬人化或人格化了的自然,具有很強的隱喻性,表示某種與人或人的心靈狀態具有緊密關聯的外部世界”,[6](P10)是我們理解的詩性的自然。波德萊爾的“自然”通過“話音”向外傳達真理和意義,其“自然”觀可以用海德格爾的理論來解釋,即這種詩性的自然是大地和世界斗爭、真理自行置入的結果。在詩性的自然中,萬物也都具有詩性,都蘊含著大地與世界抗爭過程中顯現出來的“自然”的真理和意義。所以,波德萊爾詩性的自然中,意義無處不在且具有共通性。人,尤其是詩人,作為詩性世界中的一部分,與萬物具有意義上的共通性。
波德萊爾認為:“一首美妙的詩使人熱淚盈眶,這眼淚并非極度快樂的證據,而是表明了一種發怒的憂郁,一種精神的請求,一種在不完美之中流徙的天性,它想立即在地上獲得被揭示出來的天堂。”[1](P187)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的“大地世界”說的初級形態。詩,或者說藝術,就是這樣一種依托大地構建意義世界(天堂)的東西。詩的創作源自一種對不完美進行超越的沖動,而超越不能脫離大地。正是在超越的過程中,詩中蘊含了真理。海德格爾認為這種真理需要經過遮蔽與澄明的斗爭才能得來。而波德萊爾認為“自然”本身就是一首直接呈現真理的詩。可見,兩人思想雖然具有一致性,卻也有差別。
通過對海德格爾大地和世界關系的思考,我們明晰了波德萊爾“混沌深邃的統一體”中真理和意義的發生過程,深化了對“應和”思想的理解。在波德萊爾的“應和”思想中,我們看到了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初級形態。
[1]〔法〕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C].郭宏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2]劉波.波德萊爾“應和”思想的來源[J].四川外語學院院報,2004,(4).
[3]〔法〕波德萊爾.惡之花[M].郭宏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
[5]〔德〕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A].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上)[C].上海:三聯書店,1996.
[6]劉波.《應和》與“應和論”——論波德萊爾美學思想的基礎[J].外國文學評論,2004,(3).
[7]〔德〕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A].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上)[C].上海:三聯書店,1996.
[8]張賢根.海德格爾美學思想論綱[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