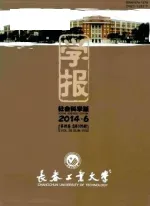民國時期輿論界對農地制度的思考及其啟示——以《東方雜志》為例
蔡 勝
(安徽醫科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合肥230032)
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指出了農地問題的重要性:“有關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法律和慣例,在經濟上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在農業是主要活動形式的比較貧窮的地區里,尤其這樣。”[1](P143)中國自秦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就遭到廣泛抨擊。到了民國時期,輿論界更是對此掀起討論高潮。農地問題也是學界的關注熱點,但現有成果集中于國共兩黨的土地思想及其實踐活動,關于輿論界的思考卻鮮有敘及。鑒于此,本文以《東方雜志》為切入點,來透視民國時期輿論界對農地制度變遷的關注和思考,以期對現實有所裨益。
一、《東方雜志》對農地制度的深切關注
《東方雜志》是中國近代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雜志,它以高度的嚴肅性、學術性和豐富的內容,受到社會的推重,被稱為“雜志界的重鎮”和“雜志的雜志”。[2](P7)作為公共領域的輿論空間,《東方雜志》密切關注農地制度問題。
民國成立前后,由于社會動蕩不安,《東方雜志》側重于報道各地的民變,農地問題尚未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農地改革在歐洲各國興起,此種思潮傳入中國,《東方雜志》對此進行關注。《東方雜志》編輯高君實論述了俄國的土地改革;《新覺路》雜志主編鄧初民提倡蘇俄的土地國有制度;時為《時事新報》和《晨報》駐德記者的俞頌華對東南歐諸國的改革進行了闡述。此時期各論者還僅僅停留在介紹歐洲各國土地改革的層面。
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社會各界寄希望于政府的土地改革,紛紛撰文進行熱烈討論。北京大學的高一涵教授論述了愛爾蘭、英國和丹麥的土地改革,總結出各種值得注意的問題;暨南大學的雷賓南教授和巴黎大學的彭師勤研究員分析了歐洲各國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諸青來發表了《土地分配問題》一文;蕭錚對國民政府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進行了分析評論。此時《東方雜志》各論者試圖通過總結歐洲各國土地立法的經驗教訓,修訂完善指導農地制度變遷的《土地法》。
1930年《土地法》頒布后,并沒有得到實施。1933年福建出現了“計口授田”土地制度,1935年山西出現了“土地村有”制度,《東方雜志》再次掀起關注農地制度變遷的熱潮。分析閩西土地政策的有《東方雜志》編輯“有心”的評論文章和福建省民政廳鄔丹云的介紹文章;對于“土地村有”制度的評析,有《東方雜志》編輯史國綱的論述和刊登于《東方雜志》32卷21號的一組文章,各論者通過對土地村有的評論,闡述了各自的主張。此后,李景漢和王相秦等人對此亦撰文探討。此時各論者的討論開始積極回應農地制度變遷的實踐活動,著眼于制度的實施層面。
從《東方雜志》關注農地制度的過程來看,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關注點集中在三個階段,各階段關注重點又有所不同,探討重心從介紹歐洲各國土地改革轉變到探討中國農地制度變遷,內容具有逐步深入的趨向。其次,作者來源廣泛,既有報社編輯和駐外記者,又有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等,說明社會各界對農地制度的關注熱情都非常高。再者,鮮明的國際視野。一戰以前,《東方雜志》尚未刊載有關農地制度方面的文章。一戰以后,《東方雜志》通過報道歐洲農地改革,逐漸意識到中國農地改革的必要性。俞頌華就明確指出寫作目的在于“間接提起國人對于本國地制改良的注意。”[3](P73)此外,編者和投稿者發表了大量歐洲農地改革的文章,更加具有借鑒意義上的自覺性。彭師勤認為,在中國,“要革命成功,不能不靠農人加入,不能不把農地問題予以解決。”[4](P30)故寫作《歐洲農地改革的昨日和今日》一文,得以借鑒。蕭錚甚至發表了譚麥熙克對中國《土地法》的意見。
農地問題的重要性和農地改革的必要性得到《東方雜志》各論者較廣泛的認可。正如時人所說,“吾國目下土地問題之日趨嚴重,已盡人皆知。”[5](P123)李景漢指出,“土地為農業的基礎,為生產的根本工具。農民不得使用土地,或使用而不得其道,則農產必致衰微,農村亦隨之凋敝。土地不得適當之解決,則農村一切問題無從說起,在中國尤為嚴重而急切,因為中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若土地問題不得解決,農業經濟即發生危機,整個社會經濟亦將陷于崩潰。”[6](P145)
二、《東方雜志》關于農地制度變遷的不同路徑方案
《東方雜志》各論者在農地制度變遷的思考中,從土地所有權、如何征收土地和農地經營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路徑改革方案。
(一)土地所有權歸屬問題
主要有公有(或國有)和農有兩種觀點。鄧初民、蕭錚和閻錫山等人堅持土地公有(或國有),鄧初民認為一切土地為公產,應該廢除土地私有制,進行土地公平分配,農民有使用權。閻錫山認為,土地應該收歸村公有。[7](P17)蕭錚則認可國民政府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原則,認為其實質是土地國有,“土地所有權之形態,為最科學最合理之所有權兩級制。國家有支配管理之權,而個人有使用、收益之權。”[8](P13)新橋、唐啟宇和諸青來等人則倡導土地農有,他們對土地農有必要性的論證主要依托于對土地公有的批駁。新橋認為,土地公有不利于農業生產,他指出,“土地公有將塞農人勤勉節儉之心,影響生產,而使農人及全社會均蒙其不利。”[9](P29)唐啟宇認為土地公有不僅在理論上不公平,而且在實踐上也會導致社會無以進步和國家處于危險境地。在理論上,從地主有田,佃農卻無田的原因來說,“地主所以有田得之于遺傳,得之于贈與,得之于勤儉,得之于儲蓄。耕農所以無地,經濟之困難也,習慣之束縛也,思多種也,己田之太遠也,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也。”[10](P7)土地一旦實行公有,“至少有一部分勤儉儲蓄所致之田產,收為公有,而分與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之夫,毋乃勵游惰而懲勤勞,豈世之所謂均平。”[10](P7)在實踐上,唐啟宇認為“耕地公有,勞己而利人,授田期屆,剩余之利益,自身且不能享,遑恤其后,雖地上有價物可給予補償金,然物質之報酬幾何?人懷茍安之念,無復遠大之思,社會前程,無復進步之可言矣。”“耕者不能自有其田,人與地之關系,日趨薄弱,孰為保守鄉里?孰為捍御外侮?遇有危難,去之若浼,是真國家民族前途之極大危機也。”[10](P7)
(二)如何征收土地問題
土地能否成功征收是農地制度改革的前提,其難度也最大,這成為當時重點考慮的問題。輿論的視點集中于征收問題,形成三種觀點:
第一,“踢去”地主,即無償沒收地主土地。鄧初民堅持此項原則,認為應該仿照蘇俄的方法,“一切土地,宣告為公產……至對于原地主,不予以賠償。”[11](P16)
第二,“買去”地主,即有償收買地主土地。其中關鍵在于購買資金的來源問題,高一涵指出了購買土地的資金困境問題,他指出,政府財政紊亂,無力購買土地,“就是只收買一部分土地,財政上已經毫無把握,何況收買全國的土地呢?”[12](P42)如果由農民來擔負購買土地的資金,農民“必定感覺擔負上的痛苦,結果與佃農仍是一樣。”[12](P42)
各論者紛紛提出策略來規避收買土地的資金困境。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發行公債來收買土地,各論者具體辦法卻有所不同。閻錫山提倡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并且以產業保護稅、不勞動稅、利息所得稅等作為分年還本之擔保。[7](P18)吳景超認為,“購買土地之款,應由政府全部借給農民。至于此種款項之來源,或由政府舉債,或撥給地主以土地債券均可。政府借給佃戶購地之款,利息應低,可由佃戶將本息于若干年內攤還,其數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戶負擔為原則。”[6](P157)丁文江則認識到佃戶還款時間太長,可以利用清理田賦所得的款項作為購地之用,他指出,“中國田地不但稅則輕重不均,而且漏稅的極多。如果全國實行土地測量,把無糧的田地變為有糧,田賦收入一定可以增加四分之一以上,大約是有把握的。”[6](P158)具體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通過發行公債來收買土地,將土地分給佃農,但公債的利息仍由佃農擔任。然后政府利用清理田賦所得收入,將其全部用于公債還本。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早定佃農的土地權,佃農的負擔也可以在短期內減輕。二是通過征稅來積累資金。高一涵認為在政府公債信用不高的背景下發行公債會導致失敗,最緊迫的方法是對佃農減租和對大地主征收累進稅,[12](P42)諸青來也指出,“不耕業主之增稅、契稅、繼承稅,每年悉數撥出,另作專款存儲,備充自耕者購田基金,諒無缺乏之虞矣。”[13](P17)
第三,“稅去”地主。各論者具體方法也有所不同。蕭錚倡導采用累進稅制,他認為,“采累進稅制則有其利而無其弊。大地主之土地加多,其納稅愈重,勢不能不讓賣其一部。土地集中于少數人之手之事實,決能因此免除。”[8](P14)唐啟宇提倡采用累進稅和遺產稅。[10](P10)李景漢則認可孫中山的“照價抽稅,照價收買”,“限制占田”和“移民墾殖”準則,其核心是“照價抽稅”,強調土地增值效益歸國家所有,“以土地價格為標準而征收。地主之原有部分仍歸地主,而社會增價值部分歸于國家。”[6](P161)他認為這就是以“平均地權”作為手段,先從土地農有來進行過渡,最后達到土地國有的辦法。
(三)農地經營方式問題
中國古代流行的租佃制度受到時人廣泛詬病,民國時期輿論界對租佃制度進行強烈抨擊,認為其阻礙了社會公平和生產發展。
閻錫山指出了租佃制度導致社會更加不平等,“無田之耕農歉歲所分之糧少,不足以供食用,豐年所分之糧賤,不足以易所需,而藉租息生活者不勞而獲,翻(反)比一般貧農無論豐年歉歲生活為優。”[10](P7)李景漢則指出租佃制度不利于生產的發展,“租佃制度本身的不合經濟原則是人所公認。產權不確定,佃戶不肯合理的利用地力或作比較有永久性的設備。因之阻礙農業技術之改進,使生產低落。地主與生產工作完全分離,而坐享不勞而獲之地租,此地租即為土地生產之利潤,亦為生產之必需的流動資本。”[6](P150)
各論者在農地經營方式上出現的分歧主要表現在避免小農經營弊端的策略上。時人普遍認同于“耕者有其田”的原則,①其中,論者對“耕者有其田”中的“有”指所有權還是使用權,觀點并不一致。但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必然導致小農經營,而小農經營存在不利于機械生產等各種缺陷,不利于經濟發展。如何能夠避免小農經營的弊端,使分散的經營轉為規模經營,這成為時人思考的難題。
時人主要從合作和國有荒地進行大農經營等方面提出對策。耕地合作方面,俞頌華認為應該獎勵農地的集約耕作方式,從而發揮小農生產大量吸收人口的優勢,另一方面也應培養農民的合作精神,“獎勵農業上各方面的合作,培養農民間共同生產消費的良好習慣,并于農產物的販賣上,資本通融上,增進他們互助精神。”[3](P72)這樣可以避免小農生產的劣勢。蕭錚認為大經營的模范作用可以帶動小農的合作,“在每縣成立一個國有的大農場。在這農場上做各種農事試驗,例如以新的機器,新的種子及新的肥料等等。凡這些事情,小經營是極難做的。這種作模范的大經營能鼓勵小土地所有主組織合作,這便可兼有小土地所有與大規模經營的優點了。”[8](P18)諸青來、李景漢和應德田等人則主張在地廣人稀的省份或國有荒地可以采用大農經營,以利于機械生產。
三、《東方雜志》對農地制度變遷思考的啟示
20世紀上半葉,國民黨在各種矛盾中一直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共產黨在不斷糾錯過程中,暫時解決了農地制度供給問題。在“三農”問題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瓶頸的今天,農地制度建設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農地制度變遷的路徑也是眾說紛紜,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路徑:土地國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重構土地集體產權。通過分析民國時期《東方雜志》的思考,我們有三點啟示:
(一)農地產權明晰化
時人爭論目標雖然指向國有(公有)或私有,但并沒有認識到產權明晰問題。從產權理論角度分析,無論是私有土地,還是公有土地,其產權皆是一組權力或權力束。[14](P96)
私有土地并不是單一產權,也面臨著政府干預等產權分割現象。王家范即指出,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產權“究其實質都擺脫不了‘國家主權是最高產權’的陰影。”[15](P2)
國(公)有土地同樣也面臨著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等各種權力分離現象。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環境中,產權更是進一步細化分解,農地產權的明晰日益重要。其中,明確國家、個人及集體多重產權主體的權限是關鍵問題,從而可以優化各產權主體的行為。
首要舉措應為制定相關的法律,來明確各項農地產權。而時人對1930年《土地法》進行了不同的解讀,王相秦認為,《土地法》“僅為實現平均地權第一個階段之主張”,[5](P120)即“限制土地私有”階段,是實行土地農有的準備階段,[5](P115)強調的是私有。蕭錚則認為,此《土地法》規定“國家有支配管理之權,而個人有使用,收益之權”,[8](P13)強調的是國有。對法律條文的不同理解說明了《土地法》規定的產權并不清晰,因此《土地法》推行甚為困難,這也是南京國民政府農地制度變遷失敗的原因之一。
(二)農地集體產權完善化
民國時期,輿論界重點討論如何征收土地問題,實質就是探討農地制度變遷成本問題,成本該由誰負擔?公平性如何?是否具有可行性?
當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地主已不復存在,當代學者提出各種農地國有、農地私有等制度變遷路徑,意圖用消滅集體產權的方法來消除集體土地產權的主體不夠明晰問題。
農地國有化有兩條途徑:國家購買集體土地或國家無償沒收集體土地,前者要求國家承擔制度變遷成本,但國家無力負擔;后者要求農民承擔制度變遷成本,剝奪了農民的權益。農地私有化會造成國家和個人的交易成本增大,還會造成各種不確定的影響。農地國有化和私有化都不能達到“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14](P274)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分析,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和制度設計成本,在變遷過程中還存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16](P150)沿著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的方便一些。[17](P58)堅持和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能夠降低制度變遷成本,其中,明晰農地集體產權是著力點。
(三)農業人口非農化
在現實國情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農地具有農民生活保障的政治功能和農業生產的經濟功能。《東方雜志》也主要圍繞這兩大功能進行論述,但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導致時人在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的抉擇中進退失據。平均分配土地的結果只能是零細小塊土地,時人對此采取的對策是耕地合作、國有荒地大規模經營,甚至是土地社有,但過多的人口在過少的土地上耕作的現狀仍不能改變。在土地不能繼續增多的情況下,除了限制人口外,只能是將農業人口轉移到非農業領域,消減土地承載的人口壓力。此外,在農業人口非農化的過程中,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削減農地的政治功能顯得額外重要。
[1]〔英〕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M].周師銘,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方漢奇.《東方雜志》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J].東方,2000,(11).
[3]俞頌華.戰后捷羅巨三國地制改良[J].東方雜志,1924,(14).
[4]師勤.歐洲農地改革的昨日和今日[J].東方雜志,1930,(17).
[5]王相秦.平均地權之理論與實施[J].東方雜志,1937,(13).
[6]李景漢.中國農村土地與農業經營問題[J].東方雜志,1936,(1).
[7]朱偰.土地村公有乎實行增值稅乎[J].東方雜志,1935,(21).
[8]蕭錚.譚麥熙克對吾國土地法之批評與管見[J].東方雜志,1931,(10).
[9]新橋.土地村有不可能[J].東方雜志,1935,(21).
[10]唐啟宇.評閻錫山氏之土地村有[J].東方雜志,1935,(21).
[11]鄧初民.土地國有問題[J].東方雜志,1923,(19).
[12]高一涵.平均地權的土地法[J].東方雜志,1928,(1).
[13]諸青來.土地分配問題[J].東方雜志,1931,(3).
[14]〔美〕H·登姆塞茨.關于產權的理論[A].〔美〕R·科斯,〔美〕D·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C].劉守英,等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15]王家范.中國傳統社會農業產權辨析[J].史林,1999,(4).
[16]〔美〕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17]吳敬璉.路徑依賴與中國改革——對諾斯教授演講的評論[J].改革,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