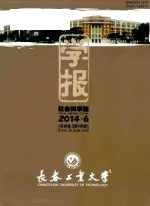從“粉絲”到“屌絲”——論“-絲”的語法化
那 劍
(西南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綿陽621010)
2012年《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收錄了流行詞“粉絲”,用以指稱“迷戀、崇拜某個名人的人”,“粉絲”正式進入標準漢語。隨著“粉絲”一詞的日益普及與合法化,有關“x絲”的詞語不斷涌現,如“鐵絲”(鐵桿粉絲)、“鋼絲”(相聲演員郭德綱的粉絲)、蕾絲(演員徐靜蕾的粉絲)等。如今“屌絲”一詞的盛行使得“x絲”詞語模不斷擴充,這不僅豐富了當今漢語的詞匯,也給漢語詞匯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類推的可能。從“粉絲”到“屌絲”,“-絲”從無到有,它如何產生,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本文認為“-絲”從“粉絲”到“屌絲”的進化是一種語法化過程。以下將詳細考察“-絲”作為語法成分的產生過程及產生原因。
一、語法化與“-絲”
語法化,最早由法國語言學家梅耶于1912年在其《語法形式的演化》一書中提出,用來描寫一個詞匯形式如何演化成一個語法標記。[1]后來被美國功能主義認知語言學派進一步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理論。沈家煊的《“語法化”研究縱觀》將語法化理論引入中國。隨后,劉堅、文旭等相繼發表文章介紹國外語法化理論的相關成果,語法化研究在中國得以發展。多年來,中外學者對“語法化”進行了多種定義,目前普遍認為Jerzy Kuryloweicz在《語法范疇的演化》一文中給出的定義最經典:“語法化是指語法范疇和語法成分產生的過程或現象,典型的語法化現象是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項或結構式變成無實在意義、僅表語法功能的語法成分,或者一個不太虛的語法成分變成更虛的語法成分。”[2]王鳳敏在總結了幾個有代表性的“語法化”定義后認為,語法化應該指語言發展過程中語法單位和語用法的從實到虛的穩固和逐漸演變過程。“-絲”作為語法成分經歷了特殊的產生過程,其意義從實到虛逐漸演變,符合語法化的規律。
二、“-絲”的語法化路徑
(一)“粉絲”之“-絲”
“粉絲”一詞是英語單詞“fans”的音譯,意為“熱心的追隨者、狂熱者、愛好者”。與“fans”諧音的詞有很多,如香港曾將其譯為“番士”,為什么最終“粉絲”成為了通用譯法呢?這是因為“fans”在被處理成漢語時,既要適應漢語的語音系統,又要盡量適應漢語的詞匯系統。好的翻譯還要盡力使詞語的能指與所指緊密聯系,引發人的相關聯想。我們可以從“粉絲”的詞義分析來尋找“fans”與“粉絲”聯系的理據。《新現代漢語詞典》將“粉絲”釋義為:用豆類制成的一種絲狀食品。“絲”是“粉絲”一詞的重要語義特征。《說文解字》:“絲:蠶所吐也。從二糸”。百度詞典對“絲”釋義中的一項為:糾纏在一起的東西。“絲”千頭萬緒,糾纏不清,被用來隱喻表示人們內心復雜的情緒。情緒越復雜,牽動的感情越多,越難以割舍。所以,用“粉絲”一詞作為“fans”在漢語中的對應形式,不僅語音和諧,在意義上也很好地體現了“鐘愛”、“迷戀”之意。可以說“粉絲”是隱喻式音譯。
與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等音譯詞不同的是,“粉絲”是對英語復數形式的翻譯,“-絲”對應音節-s。漢語不以形態為主要語法手段,“粉絲”因此揚棄了英語的數范疇,既可指集體,也能指個體。英語里,fan是詞根,-s為詞尾的形態標記,在表義上fan顯然比-s重要。“粉絲”原本只是兩個音節連綴的單純詞,內部并無語法、語義關系,但隨著“鋼絲”、“鐵絲”、“蕾絲”等“x絲”結構的出現,“粉絲”有向偏正式合成詞轉化的傾向。“受一個漢字一個語素模式的影響,漢民族集體心理中深藏著將無意義音節語素化的情結。”[3]漢語中的外來名詞普遍存在音譯成分語素化現象,即取外來詞中一個音節代替該詞作為語素來構造新詞,如:迪(disco迪斯科)有“蹦迪”、“迪廳”,麥(microphone麥克風)有“耳麥”、“麥霸”,巴(bus巴士)有“大巴”、“中巴”等。這些共時層面的縮略語素大多是粘著的,不能自由使用,尚未取得詞的資格,但這些無意義音節卻起著負載整個詞義的作用。這是外來詞在目的語中發展、演變與馴化的一種方式。“x絲”的類化作用——保留正的語素(絲)、替換偏的語素(x)構造新詞——促使人們偏離焦點提取的原則,根據位置關系選擇附加手段的“絲”而舍棄音義主體的“粉”來肩負整個“粉絲”意義,催生了一個單音節外來語索“絲”,相當于“狂熱的愛好者”,這顯然不同于漢語的原有語素“絲”。
觀察“x絲”類詞語。這些詞語的構造可以用一個模型來說明,即“名字中的某個字或其諧音字+絲”,如郭德剛的粉絲“鋼(剛)+絲”,徐靜蕾的粉絲“蕾+絲”。絲類詞語中的“絲”詞素已經逐漸虛化,慢慢蛻去它的本義,意思向fan的本義過度。這種現象其實可以看作是漢語實詞虛化的表現。按照葛本儀[4](P134)先生的觀點,“漢語中的實詞和附加詞素都有所發展。它們發展的途徑,一是創制新的成分。一是實詞的虛化。”后者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由實詞類變為虛詞類,一是由可充當詞根詞素的實詞虛化成了附加詞素。“絲”本來是個實意名詞,從“粉絲”、“鋼絲”、“鐵絲”諸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詞語中的“絲”逐漸脫離了其本義,而走向了虛化的道路,變成了一個標志粉絲義項的類詞綴。
(二)“屌絲”之“-絲”
2013年4月,紅遍中國,卻也備受爭議的流行語“屌絲”走出中國,以醒目的“屌絲Diaosi--Made In China”出現在紐約時報廣場的電視看板。盡管后來該廣告很快被禁播,但由此可見“屌絲”一詞的“活力”。與通過“fans”音譯而成的“粉絲”不同,“屌絲”是李毅吧的粉絲根據“毅絲”一詞仿制出來的。前國腳李毅稱自己的護球像法國球星亨利大帝而被網友稱為“李毅大帝”,“李毅吧”隨即被簡稱為“帝吧”或“D8”。他的粉絲遂自稱為“毅絲”或“D絲”。當“李毅吧”與另一貼吧—“wow吧”交惡后,后者便取“D”的諧音為“屌”,諷刺、羞辱“毅絲”為“屌絲”。[5]面對嘲諷,李毅吧吧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并開始以“屌絲”自稱。
隨著網絡的推波助瀾,“屌絲”的意義不斷發展,陣營也愈來愈大,成為網絡流行語。剛躥紅時,“屌絲”多指那些身份卑徽、生活平庸、前途渺茫、感情空虛、不被社會認同的“苦逼男青年”。相比“高富帥”,他們只有“矮窮挫”;他們沒錢沒背景沒未來;他們愛幻想,卻缺乏行動力,想做而不敢做。與之相對的女青年,不甘心話語權被男性剝奪,也以“屌絲”自稱。后來,這個詞又發展出“惡搞、搞笑、扭捏”等新義,所指稱對象也開始泛化,普通網友、IT精英、白領,甚至文化名流也戲稱自己是“屌絲”。作家兼賽車手韓寒稱自己是純正的上海郊區農村“屌絲”;人氣樂團“五月天”說,走下舞臺我們就是“屌絲”。如今,“屌絲”指自我嘲諷,但不自暴自棄的人。更多的反應人們對自己生活現狀、境況的不滿和無奈。
從“屌絲”一詞的產生來看,“-絲”最初本指“粉絲”,指“狂熱的愛好者”。隨著語義的發展,“-絲”脫離了“粉絲”的“鐘愛”、“迷戀”之意,而指特定的一類或一群人,類似于漢語的“者”。如此看來,“屌絲”更像是一個由詞根加詞綴構成的合成詞,其主要語義由詞根語素“屌”來承擔。
三、“-絲”的語法化動因
“語言意義和形式的演變是有理可據的,即有各種動因。這種變化有的源于語言之間的接觸,有的來自交際中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的互動,有的形成于創新用法,也有的產生于對語言的誤解和誤用。然而不管是哪種原因,語法化的發生必須是高頻率重復和慣常化的結果。”王寅[6]、Bybee也強調了語法化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重復,促使一個詞語語法化進程的必要條件就是它具有足夠高的使用頻率。我們認為促成“-絲”語法化的動因主要有語言接觸、創新用法及高頻率重復。我們認為促成“-絲”語法化的動因主要有語言接觸、創新用法及高頻率重復。
(一)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是“-絲”語法化的動因之一。從fans的引進使用到“粉絲”的火爆升空,到“x絲”類詞語的大行其道,再到“屌絲”的大紅大紫,其演變的背后是中西語言文化的一種交流與嬗變。當然這一過程是循序漸進的。本世紀初,fans登錄東南沿海城市,原滋原味,以其本來面目進入漢語。但漢語系統怎會容下一個奇裝異服的外族人。很快,強大的漢語就找到了在音義上都能完美匹配它的本族人“粉絲”。這個極為世俗化、平民化的譯詞,吻合了后解構時代摒棄經典、隨意而作的思潮,隨著2005年湖南衛視選秀節目“超級女聲”而風行大江南北。后因語用的需要,仿擬出一系列“x絲”類詞語,“-絲”語義逐漸被虛化。隨后“屌絲”在音、義上仿擬“粉絲”并大肆流行,“-絲”語義進一步被虛化。
(二)創新用法
為了豐富語言的表達手段,人們會創造性地使用語言,從而催生語言的語法化。[6]用“粉絲”一詞作為fans在漢語中的對等詞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使用。“x絲”類詞語通過結構和意義的仿擬,形成一種獨特而有趣的語言現象,緊跟時代步伐,符合當下人的審美品位,得以迅速走紅。人們傾向復制模仿那些最具時尚感的語言信息。被模仿的語言信息越時髦、越新潮,越有新意,人們就越愿意模仿它。[7]“屌絲”就是李毅吧的粉絲根據“毅絲”一詞仿制出來的。這個詞語,大膽創新,讓人感到新奇、爽口、刺激,讓追求標新立異的年輕人耳目一新、高度興奮,因此被他們當作時髦的東西,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證明自己沒有“out”,“屌絲”一詞也因此而紅遍網絡。“粉絲”、“屌絲”這類詞的創造和流行為“-絲”語素的出現和進化提供了可能和土壤。
(三)高頻率重復
湖南衛視“超級女聲”節目出現后,“粉絲”一詞如爆竹升空般火速流行,被網絡、報刊、廣播、電視、電影等媒體高密度報道使用,有力地推動了它的傳播,擴大了公眾影響度,為隨后“x絲”類詞語的出現奠定了廣泛基礎。“屌絲”自出現以來,苦逼男青年是它,頹廢女青年是它;民工是它,白領是它;“矮窮挫”是它,“高富帥”是它;有洋屌絲,有老屌絲。“屌絲”不分年齡、種族、性別。各種媒體報道、文化名人討論、學者教授解析,高密度全方位的關注使“屌絲”不斷深入人心,使“-絲”語素得以發展,從而擁有了如今的語言身份。
[1]石毓智.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動補結構的產生及其影響[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3.
[2]王鳳敏.關于語法化及語法化五個方面的評述[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9).
[3]周日安.“可伶可俐”現象解讀——兼談元意義音節語素化[J].中國語研究,2004,(46).
[4]葛本儀.漢語詞匯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5]應琛.“屌絲”的狂歡[J].新民周刊,2012,(16).
[6]王寅.語法化的特征、動因和機制——認知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法化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7).
[7]陳林霞,何自然.語言模因現象探析[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