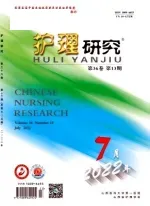乳腺癌病人全人照護模式的發(fā)展與思考1)
裴 艷,吳蓓雯,袁長蓉,方 瓊
乳腺癌作為威脅全世界女性生命健康的最常見惡性腫瘤之一,近年來日益得到關(guān)注。無論是全球每年十月的“粉紅絲帶乳腺癌防治月”,還是好萊塢女星安吉麗娜·朱莉掀起的基因檢測熱潮,均引起了媒體及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也引發(fā)了專業(yè)醫(yī)護人員的深入思考。統(tǒng)計顯示,2008年全世界女性乳腺癌新發(fā)病例約138萬例,近46萬例女性死于乳腺癌[1]。與北美、北歐和西歐等乳腺癌高發(fā)病率國家相比,我國雖乳腺癌發(fā)病率較低,但近年來由于我國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老齡化等,乳腺癌的發(fā)病率每年以1%~3%的速度遞增,2005年我國乳腺癌發(fā)病人數(shù)較2000年增長了38.5%,已成為近年來新增發(fā)病人數(shù)幅度最快的惡性腫瘤之一[2],尤其在京、津、滬等大城市。2007年乳腺癌已成為上海地區(qū)女性發(fā)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其發(fā)病率約為73/10萬[3]。盡管乳腺癌發(fā)病率呈逐年遞增趨勢,但由于早期診斷和治療方式的改進和創(chuàng)新,乳腺癌死亡率已逐漸下降[4],Ⅰ期、Ⅱ期乳腺癌病人5年生存率可分別達到95%和85%以上。這就意味著,乳腺癌的早期發(fā)現(xiàn)與治療、康復期病人的身心問題、復發(fā)轉(zhuǎn)移病人的照護等問題,均需要專業(yè)人員給予全面和持續(xù)的關(guān)注。
1 乳腺癌照護模式的發(fā)展
1.1 自然哲學醫(yī)學模式下的生活護理 原始的醫(yī)學是混雜著迷信與巫術(shù)的經(jīng)驗醫(yī)學,這一歷史時期,其研究和應用都十分落后。乳腺癌的治療亦從“沒有治療”到食療、通便、放血和水皰療法等保守治療[5],因此護理工作也僅局限于簡單的生活護理。
1.2 生物醫(yī)學模式下的功能制護理 隨著歐洲文藝復興和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人類對自身構(gòu)造和疾病的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飛速發(fā)展的科學技術(shù)給人類研究和治療疾病提供了有效手段。然而由于受唯心的二元論哲學思想和機械唯物觀的影響,將人類醫(yī)學研究陷入了形而上學的境地,將人視為機器。乳腺癌手術(shù)治療從 “根治術(shù)”到“擴大根治術(shù)”,雖然完全切除了腫塊,但也帶來了淋巴結(jié)水腫、胸壁畸形等嚴重并發(fā)癥,并直接影響了病人的免疫功能。這一階段的護理工作也只是將人看作一個生命體,開展以疾病為中心的護理,將工作重點放在執(zhí)行醫(yī)囑及圍術(shù)期常規(guī)護理等內(nèi)容上。
1.3 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下的整體護理 辨證唯物主義指導下的醫(yī)學模式告訴我們,人的生命活動不是一種簡單的生物現(xiàn)象,而是更為高級的、復雜的生物、心理、社會的復合體。在診療活動中,不僅要考慮疾病的治愈,還應兼顧病人的形象、心理康復等多重因素。因此,從改良根治術(shù)到保乳術(shù)再到乳房重建術(shù),從腋窩淋巴結(jié)清掃到前哨淋巴結(jié)活檢,從切除活檢到空心針穿刺活檢及細針抽吸活檢等,乳腺癌的診斷、治療方式也發(fā)生了革命性的發(fā)展。與其相適應的護理工作,除關(guān)注手術(shù)及并發(fā)癥護理,需要更多地關(guān)注到病人的文化程度、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心理狀況等,為病人提供身、心、社、靈的全人照護。
2 乳腺癌病人全人照護模式的內(nèi)涵
2.1 全人照護的概念 全人照護正是在現(xiàn)代醫(yī)學模式背景下產(chǎn)生的新型照護理念,其不僅強調(diào)生病前要提供正確有效的預防方法、生病時要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yī)療照護,同時也強調(diào)生病后要有正確、有尊嚴的康復與支持。具體而言,全人照護是指以人為中心,提供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合一的照顧,該理念不僅強調(diào)以個人為中心,同時也強調(diào)以家庭為單位、社區(qū)為范疇的整合性、協(xié)調(diào)性和持續(xù)性。
2.2 全人理念在乳腺癌病人照護中的意義 乳腺作為女性重要的第二性征器官,不僅具有哺乳的基本功能,還是重要的性器官、保持身體形象的重要身體部分。因此乳腺癌、乳腺切除術(shù)等,對于女性病人以及其家庭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從確診階段的恐懼、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問題;到伴隨各個治療階段的副反應,如疼痛、功能障礙、脫發(fā)、胃腸道反應等;以及康復階段對腫瘤復發(fā)的擔憂、所面臨的婚姻生活問題、生育問題、社交障礙等心理、社會適應問題。這些問題從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病人的治療選擇、治療依從性及治療康復階段的生活質(zhì)量。如何幫助病人及時發(fā)現(xiàn)和治療疾病、正確面對疾病、積極促進其身心康復等問題擺在醫(yī)護人員面前,需要護理人員提供無縫隙的、全程的、個體化的、專業(yè)的照護服務。
2.3 乳腺癌病人全人照護的內(nèi)涵
2.3.1 身體照護 隨著醫(yī)療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全人關(guān)懷理念的深入,乳腺癌的治療方案也已從昔日的單一手術(shù)治療,發(fā)展到目前以手術(shù)治療為主,集放療、化療、內(nèi)分泌以及靶向治療為一體的綜合治療模式。隨著治療的開展,疾病的確診,乳房的缺失,術(shù)后的疼痛,脫發(fā)、嘔吐等化療反應的出現(xiàn),放療期間皮膚的變化等,都會接連考驗著病人的身心。相關(guān)研究表明,乳腺癌術(shù)后慢性疼痛的發(fā)生率已超過50%[6],乳腺癌病人術(shù)后淋巴水腫的發(fā)生率接近50%[7]。這就需要護理人員結(jié)合病人所處的不同疾病及治療階段、不同的手術(shù)方式和治療方法等,運用專業(yè)護理知識和技術(shù),給予病人針對性護理,以減少術(shù)后并發(fā)癥、降低和緩解治療不良反應、促進傷口愈合及患肢功能恢復等。
2.3.2 心理、社會照護 心理情緒的變化是伴隨著疾病診療及康復過程的,每個診療階段,病人都將面臨治療的選擇、當下的無助、對未來的擔憂等。不同性別、年齡、生理階段、社會角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腫瘤類型、疾病期別、應對方式等均與其照護需求和身心康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8-10],這也使得其對于治療的選擇、信息的獲取、心理支持等多方面的需求也呈現(xiàn)出一定的差異性[11]。如年輕乳腺癌病人可能面臨著治療與結(jié)婚生育等問題的矛盾,中年病人則容易因無法照顧家庭而產(chǎn)生自責;有的家庭會因治療面對嚴峻的經(jīng)濟壓力,有的病人因為缺乏社會支持而得不到很好的照顧等。有研究報道,乳腺癌病人焦慮、抑郁的發(fā)生率為13%~54%[12-14]。然而,負性情緒不僅影響乳腺癌病人的機體康復,也會影響病人的化療、放療等治療行為及治療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而影響到病人的生活質(zhì)量甚至生存率[15]。
此外,疾病的影響并不局限于病人本人,亦會影響到其家庭、照顧者等。研究顯示,配偶照顧者經(jīng)歷的家庭調(diào)整和個人調(diào)整是非配偶照顧者的兩倍[16]。他們不僅要照顧病人、向病人提供情感支持并“過濾”掉負面信息來保護病人,還要應對家庭的調(diào)整,因此往往比病人更容易產(chǎn)生應對壓力[17]。當持續(xù)照顧時間超過12個月后,照顧者出現(xiàn)的心理反應多數(shù)跟照顧工作無關(guān),而是跟癌癥的診斷和預后以及經(jīng)濟負擔重有關(guān),他們陪同病人反復住院接受各種治療,病人的病情變化,以及同病房病友復發(fā)、轉(zhuǎn)移和死亡無形中也給他們帶來了不確定感。
因此,只有及時了解病人及其家屬的心理狀態(tài)及社會需求、排解其心理顧慮、切實解決其生活困難,才能更好地幫助病人面對并戰(zhàn)勝疾病。
2.3.3 靈性關(guān)懷 靈性的需求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每一個人,無論有無宗教信仰,都會有心靈需要,都會追求心靈的平靜安寧。特別對于晚期乳腺癌病人,其靈性需要主要包括減輕心靈痛苦(如面對死亡的恐懼)、復和關(guān)系、維持希望與尊嚴、尋找愛、生命意義、人生目標以及追求內(nèi)心平靜安寧[18]。這就需要我們在靈性照顧中幫助病人:①完成“整合生命”,即回顧、檢視人生經(jīng)驗的意義及價值,整合生命中的正面經(jīng)歷、傷痛以及遺憾;②“復和關(guān)系”,主要是分享、傳承、復和,包括與重要他人之間愛的表達、情感交流、人生經(jīng)驗與智慧的傳承,以及創(chuàng)造冰釋前嫌的機會;③“活在當下”,主要是活得精彩,好好享受每一天,以及學會珍惜、欣賞和感恩。
3 乳腺癌病人全人照護模式的特點
3.1 全程管理 罹患腫瘤往往會使病人對于自己身體的關(guān)注較健康人更加頻繁與敏感。且這種關(guān)注與需求呈現(xiàn)出階段性、持續(xù)性、全程性、專業(yè)性等特點。研究顯示,對于乳腺癌術(shù)后階段,病人最關(guān)心的問題可能是疾病治愈的可能性、疾病的播散程度和治療方案的選擇等[19],而在化療階段,關(guān)注重點則還包括抗腫瘤藥物副反應的管理[20]、營養(yǎng)及康復鍛煉等需求。因此,在腫瘤治療這個動態(tài)的連續(xù)過程,需要關(guān)注從病人確診到入院手術(shù),至后期治療、康復、隨訪的整個過程:不僅關(guān)注病人的疾病治療,還要關(guān)注其整體身心健康;不僅關(guān)注住院期間的治療,還關(guān)注出院后的全程康復和社會回歸;不僅關(guān)注病人自身,還要關(guān)注病人家屬。這也要求照護模式應該滲入整個診療康復階段,動態(tài)了解病人的疾病治療階段、心理情緒變化、社會靈性需求等全方面信息,才能更好地為病人提供無縫隙、個體化的全程專業(yè)照護。
3.2 全隊參與 隨著乳腺癌診療模式的綜合化,已逐漸告別了由單一專業(yè)成員作決定的診療策略,而逐漸轉(zhuǎn)向多學科聯(lián)合診治。從疾病的診斷、治療到疑難病例的討論,乳腺外科、腫瘤內(nèi)科、放療科、放射診斷科、病理科等多學科共同參與的診療模式已逐漸被接受和推廣。綜合團隊的參與,有效促進了疾病的早期發(fā)現(xiàn)與診斷,規(guī)范了治療,提高了病人的遵醫(yī)行為和生活質(zhì)量。從治病救人到醫(yī)療慈善,從院內(nèi)服務到出院后的病友活動,通過連接和調(diào)動可得的醫(yī)療及社會資源,將照護服務的內(nèi)涵拓展到滿足病人的經(jīng)濟需求、社會心理需求,全方位提升了病人的生活質(zhì)量。
3.3 全家照護 作為一個社會的人,病人的診療康復狀況與其家庭密不可分。如何與家屬及孩子討論病情、如何重新定位家庭及職業(yè)角色、如何調(diào)動更多的社會支持、如何增進親密伴侶關(guān)系……病人有很多超出疾病的需求需要護理人員去關(guān)注和解決。這也就使護理人員的服務范圍從院內(nèi)延伸到院外、從病人擴展到其家屬、從身體康復關(guān)注到身心康復。
4 推進乳腺癌病人全人照護的有益嘗試與思考
圍繞乳腺癌病人診療階段的需求,針對全人照護的內(nèi)涵與特點,我中心做了一些積極的嘗試與探索。
4.1 全程信息支持 通過多種形式,為病人提供貫穿住院與出院階段、治療與康復階段的全方位、立體化的信息支持網(wǎng)絡。①設計制作多種形式的宣教資料:針對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治療階段病人的需求,印制健康宣教單、宣教手冊20余種等,拍攝宣教錄像5部,構(gòu)建中心網(wǎng)站2個。②開設病人資源中心[21]:整合疾病相關(guān)的書籍借閱、免費上網(wǎng)、視頻播放,假發(fā)、義乳等康復品陳列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為病人提供形象、直觀的健康宣教。③定期組織宣教、義診:結(jié)合中心目前住院周轉(zhuǎn)情況,圍繞乳腺疾病的診治及護理,每兩周開展1次病區(qū)病人講座,每季度組織1次出院病人講座活動;此外,與上海市總工會、癌癥康復組織等聯(lián)合,定期深入社區(qū)、企業(yè)開展科普宣教。
4.2 全隊專業(yè)指導 為進一步規(guī)范乳腺癌的診療,中心先后開設了疑難病例討論聯(lián)合門診、術(shù)前診斷聯(lián)合門診、術(shù)后輔助治療聯(lián)合門診等,通過多學科會診的形式,綜合乳腺外科、腫瘤內(nèi)科、放療科、放射科、病理科等醫(yī)生的意見,縮短了明確診斷時間,標準化了治療方案的制定。作為多學科診療團隊的一分子,專科護士也參與到病例討論、聯(lián)合會診、傷口換藥等多個環(huán)節(jié),負責會診病人的信息錄入、方案解釋等工作,并為病人提供出院后24h的電話咨詢服務,有效應對了病人出院后的各種身心問題。
4.3 全人身心照護 針對病人疾病各階段的心理社會問題,中心與社會團體聯(lián)動,定期組織病友活動,邀請營養(yǎng)師、化妝師、心理咨詢師、行為治療師等專業(yè)人士,通過專題講座、現(xiàn)場參與、聯(lián)合互動等多種形式,為病人搭建溝通交流的平臺,促進其心理康復與回歸社會。同時,針對一些經(jīng)濟困難的乳腺癌病人,中心聯(lián)合社會及企業(yè)力量,成立“瑞金-哈根達斯乳腺癌救助基金”,開展慈善救助,切實幫助病人盡早接受治療。
綜上所述,乳腺癌病人的診療照護是一個需要多學科參與的、全程的、專業(yè)的過程,但鑒于以上經(jīng)驗僅限于我中心的具體做法,欲構(gòu)建和推廣適用范圍更廣的乳腺癌全人整體照護模式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探索。
[1] Jemal A,Bray F,Center MM,et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J].CA Cancer J Clin,2011,61(2):69-90.
[2] 楊玲,李連弟,陳育德,等.中國乳腺癌發(fā)病死亡趨勢的估計與預測[J].中華腫瘤雜志,2006,28(6):438-440.
[3] 2009年上海市惡性腫瘤報告[R].上海: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57.
[4] Jemal A,Siegel R,Ward E,etal.Cancer statistics,2008[J].CA Cancer J Clin,2008,58(2):71-96.
[5] 曹旭晨,乳腺外科手術(shù)圖譜[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8:7.
[6] 周凱娜,李小妹.乳腺癌根治術(shù)患者疼痛、焦慮及抑郁現(xiàn)況研究[J].中國護理管理,2011,11(4):70-73.
[7] 代莉莉,段艷芹.乳腺癌術(shù)后上肢淋巴水腫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和上肢活動度調(diào)查[J].護理學報,2012,19(7A):20-22.
[8] Mills ME,Sullivan K.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giving for patients’newly diagnosed with cancer: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J Clin Nurs,1999,8:631-642.
[9] Miller SM.Monitoring versus blunting styles of coping with cancer infiuence the information patients want and need about their disease.Implications for cancer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J].Cancer,1995,76:167-177.
[10] Wallberg B,Michelson H,Nystedt M,etal.Information needs and preferences for participation in treatment decisions among Swedish breast cancer patients[J].Acta Oncologica,2000,39(4):467-476.
[11] Lee JA,Lee SH,Park JH,etal.Analysis of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patients with cancer[J].J Prev Med Public Health,2010,43(3):222-234.
[12] Burgess C,Comelius V,Love S,etal.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Five year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J].BMJ,2005,330(7493):702.
[13] Hopwood P,Haviland J,Mills J,etal.The impact of age and clinical factors on quality of life in early breast cancer:An analysis of 2 208women recruited to the UK START trial(Standardisation of Breast Radiotherapy Tria1)[J].The Breast,2007,16(3):241-251.
[14] So WK,Marsh G,Ling WM,etal.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during adjuvant therapy[J].Eur J O Nurs,2010,14(1):17-22.
[15] Hopwood P,Sumo G,Mills J,etal.The cours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ver 5years of follow-up and risk factors in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Results from the UK.Standardisation of Radiotherapy Trials(START)[J].The Breast,2010,19(2):84-91.
[16] Hwang SS,Chang VT,Alejandro Y,etal.Caregiver unmet needs,burden,and satisfaction in symptomatic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at a Veterans Affairs(VA)medical centre[J].Palliat Support Care,2003,1(4):319-329.
[17] Molassiotis A,Wilson B,Blair S,etal.Living with multiple myeloma:Experiences of patients and their informal caregivers[J].Suppont Care Cancer,2011,19(1):101-111.
[18] 劉曉芳,讓晚期癌癥患者享有全人關(guān)懷:姑息醫(yī)學社會工作服務經(jīng)驗 分 享 [EB/OL].[2012-10-31].http://www.elseviermed.cn/news/detail/Let_the_advanced_cancer_patients_enjoy_holistic_care.
[19] Luker KA,Beaver K,Leinster SJ,etal.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women newly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J].J Adv Nurs,1995,22(1):134-141.
[20] Lee YM,F(xiàn)rancis K,Walker J.What are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J].Eur J Oncol Nurs,2004,8(3):224-233.
[21] 裴艷,董曉晶,張男,等.乳腺癌資源中心的構(gòu)建及作用[J].中華護理雜志,2011,46(8):83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