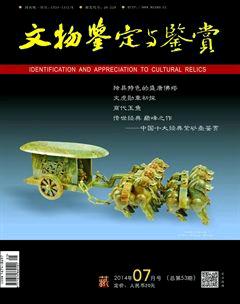重返單純 心念收藏
李暉軍
本刊記者:很多人出身于世家,從小耳濡目染,流淌在血脈里的世代相傳的因子不斷激活,除了傳承家族的使命以外,也是對家族夢想的堅守。這是中國家族獨有的秘密,使命與夢想,無不用心創(chuàng)造,代代傳承。您出身于收藏世家,這種使命與夢想的堅守在您身上尤為顯現(xiàn),在市場化的今天,更多人選擇了收與放,忽略了藏,而您恰恰相反,您在堅守什么?
龍國祥:家族對我的影響至深,不僅僅在收藏上。我的祖籍在江西撫州,祖輩是工商業(yè)的富商,資助過學校、開過食品廠,在當地享有盛譽。我爺爺很喜歡收藏,父親更是熱愛收藏,精于品鑒,受家庭影響,從小便接觸古董、字畫、瓷器等藝術。我十幾歲時,是從收藏郵票開始的,旋至書畫,及長,興趣愈廣,至今,收藏史已近30年,收有藏品千件,其中有張大千的《寫意青綠谷口山水圖》、李可染的《峽江輕舟圖》、乾隆官窯蓮子缸、唐三彩馬等,經多名國內知名專家鑒定,俱為真品。
你這個問題其實也問出了當下家族文化延伸轉折的方向。在傳統(tǒng)社會以其忠孝的文化觀念,注重家族命運,傳承至今日,家族文化的傳承也適應時代的要求,強調人生的社會貢獻和價值,忠誠于民族國家。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群體力量和文化探索因素促使著我們對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的守望。我從小就受父輩文化熏陶,他常以家中的藏品為例為我講解其中的文化淵源。當時不理解為什么家中那么多的藏品,不論朝代,不論是瓷器,還是書畫,父親都能以文化根源解釋這一切。太神奇了!這幾十年來對文化的研究也慢慢地理解了當年父親所說的文化根源問題。中國文化注重歷史性和親屬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家族的世代相傳、香火不斷的獨特人生觀一直延續(xù)至今。幾千年來隨著生活生產的進步,加速了思想的轉變,也促使了文化的流動和擴大,但如何傳承這種變化和創(chuàng)新,物體的承載也就應運而生。而在民族、區(qū)域、語言的差異下,物體承載記錄的文明打破了交際障礙,加速了精神和物質產品的流通,將種種差異納入到一個共同的物體中,使其具體化。
我之所以在這里大談文化,也是家族對我的影響,就像我在前面說到的,家族的影響不僅僅是收藏。雖說這幾年收藏市場火爆,拍賣一場接著一場,也著實讓一批收藏人士富裕起來,但我更愿意花時間研究藏品本身所承載的文化。守望文化比把玩更有意義。
本刊記者:祖?zhèn)鞯那」俑G蓮子缸,見證了您在收藏界近30年的成長,在收與藏的雜糅中,30年太久,卻又恰恰是在最平凡的生活里。30年的平凡堅守,包容了收藏的苦與痛。我與您認識的這幾年里,您從來沒有和我抱怨因收藏的苦痛給您帶來悲觀消極,反倒越來越樂觀豁達,這是怎樣的一種心境?
龍國祥:堅守,對文化的堅守。如果把我這30年的收藏經歷放在歷史的時間表中,一粒塵埃都算不上。和歷史上真正的收藏大家相比,我連塵埃都算不上,我哪有資格去苦悶。歷史上有很多大藏家,定是把畢生的精力投入到或鑒賞、或收藏、或傳承文物上。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很敬佩王世襄,是因為王世襄對中國古玩收藏界的貢獻,不僅僅是身體力行地收藏到一批堪稱經典的博物館專題展覽級別的精品,還著書立說,全面反映明清時期家具全貌和發(fā)展進程,并把明清家具的收藏研究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學術文化層面,為中國的明清家具收藏文化研究留下不朽的一頁。王世襄的收藏閱歷、收藏學養(yǎng)、收藏經驗、收藏文化影響力是當代任何一名收藏家都難以與之匹敵的。這又是怎樣一種心境呢?不言而喻。
收藏在于研究,我正是把王世襄的這種精神樹為榜樣,把收藏提升到研究的層面,雖然辛苦,但有意義。
本刊記者:名利是很多人畢生的追求,收藏界也不例外,為此有的藏家不惜重金收藏,以求名揚。似乎您不太關注這些。您更多關注的是什么?
龍國祥:我喜歡收藏,但從不沉迷其中,不因收藏而玩物喪志,量力而行,不太注重名利場上的事。對于我而言,關注點是在學術研究上。慚愧的是,至今也沒有研究出什么來。收藏這口井實在是太深了,看著井口小,一眼就能看到水,但真正當你去取水時,似乎怎么也夠不著水。有的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點滴之水;有的人則是滿載而歸;有的人就沒有那么幸運,花了大把的時間和金錢,最后桶還是在半空中,拉上來不忍心,繼續(xù)取水,精力也殆盡。尋找如何取到水的秘笈也就運用而生了。還真被能人異士找到了,想取水的人也就蜂擁而至,結果是,能人異士成了大師,想取水的人也都分了一杯羹。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我想市場的答案可能更權威。至于別人如何取到水,那都在為收藏而努力,只是途徑和方法不同罷了。我的方向是研究藏品本身的文化及其根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到成都旅游,順道去拜訪了四川大學陳教授,兩人一起逛了杜甫草堂文物市場,無意中陳教授發(fā)現(xiàn)了張大千的《寫意青綠谷口山水圖》長卷,當時便和教授探討張大千的繪畫藝術等問題,后經多次研究和比對后,我決定收藏這幅長卷。后來事實證明,當初的決定是對的。張大千這幅《寫意青綠谷口山水圖》長卷,長659厘米,高26.5厘米,前有溥心畬的題跋,后有劉海粟的長跋。也正是這次收藏讓我意識到僅僅對張大千的畫風進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每個時期會有相對應的作品,以作品為基點深入研究局部風格,從點到面的匯總,形成一個整體,可能更有益于我去收藏張大千的作品。這里我就不班門弄斧了,借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書畫鑒定專家呂長生教授鑒定此卷時的一段話:“張大千是國畫大師,書法造詣也十分了得。詩書畫與齊百石、溥心畬齊名,故有美稱為‘南張北齊和‘南張北溥。谷口山水圖‘筆力雄健在畫中充分顯現(xiàn),筆力直追古人。筆墨者,傳統(tǒng)中國畫之精魂。大畫家黃賓虹有云:‘筆是骨,墨是肉,缺了這兩者國畫就難以立起來。沒有筆力做底,國畫就沒有神韻。韻律在畫中流徜全在于筆墨(彩)。造型線條的清晰靈動如何,全靠書法的功底。筆到什么程度,畫作的線條、骨力就到什么程度。書法的功底讓畫的線條優(yōu)美、景物傳神,讓畫作逸氣橫流,氣象萬千。‘大象無形筆落硯,神飛翰逸畫生輝。張大千谷口山水圖線描筆力表現(xiàn)出來的爐火純青,正是如此。圖卷物情美、物態(tài)美、彩色美、構圖美,教人回首,仔細研讀,用心體味,受益匪淺,樂趣無窮。”
本刊記者:“收藏不應沉迷其中,接下來專心公益。”從何時起您有這種想法,或者是一直就有這樣的想法,是從什么時間來踐行這種“責任”?
龍國祥:讓我最有幸福感的不是收藏,而是做公益慈善事業(yè)。我一直堅信一個收藏家擁有的不只是藏品數量上的多與少,還有胸懷和氣魄的大與小。
做公益事業(yè)的想法也是受我爺爺的影響。他老人家早些年就投入到公益事業(yè)中,資助過學校。在家庭的影響下,收藏的藏品不會永遠屬于一個人,最終還是要回歸社會、服務于社會的這種理念隨著年齡的增長日益加深。這些年來也陸陸續(xù)續(xù)地做了一些慈善活動,為部隊雙擁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也捐助了一些資金給貧困的孩子們,但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籌辦一所公益學校。
教育能改變人的一生,貧困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思想。辦一所公益學校是解決那些因貧困等種種原因不能上學的孩子們能有一個場所安心地學習。只有通過學習,人們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
辦學校的夢想從小就有了。有夢想并不一定就有未來,這中間是一個漫長的努力過程。現(xiàn)在計劃出讓一些藏品,籌集辦校資金。可喜的事,目前學校已經完成辦學手續(xù)。
我希望我的藏品變現(xiàn)后,能支撐我正在籌辦的公益學校,雖說出讓多年的藏品,多有不舍,但作為一個藏家,始終是要回歸社會的——公益事業(yè)事關自己的“人格”,是自己曾經承諾過的東西,一定要辦。■
收藏家簡介:
龍國祥,廣仁齋堂主人,廣東古董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出身于收藏世家,祖父龍信榮熱愛收藏,精于品鑒,受父輩的影響,從小就開始接觸古董、字畫、瓷器等藝術,年十幾歲,自始收藏郵票,旋至書畫,及長,興趣愈廣,至今,收藏史已近30年,收有藏品千件,其中有張大千的《寫意青綠谷口山水圖》、李可染的《峽江輕舟圖》、乾隆官窯蓮子缸、唐三彩馬等,精品良多(且經多名國內知名專家鑒定,俱為真品。)。秉承“文物,乃文化傳承之器物”的共識,積極舉辦個人書畫古董收藏品博覽會及古董展覽,讓更多的人見識和了解文物,弘揚中國收藏文化,在業(yè)內聲名鵲起,現(xiàn)專事藝術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