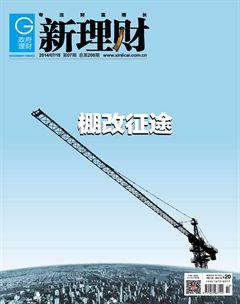土地財政大考
史可
土地財政—一個輿論窮追不舍,地方政府諱莫如深的詞匯。從古至今,土地財政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著,但都沒有像今時今日這樣處境尷尬。如今,且看它十年繁華落盡曲將散,或許是該冷靜下來思考其“原罪”與“救贖”的時候了。
《新理財》5月刊曾經關注過各地政府對于低迷樓市的“救市”措施。目前來看,地方政府對于房地產市場進行軟著陸調整的力度正繼續擴大。據不完全統計,出臺放開限購等調控政策的城市已經擴大到寧波、無錫、杭州蕭山、天津濱海、銅陵、鄭州、揚州、南寧等多個城市。除卻這些公開救市的城市之外,廣州南沙、佛山高明、常州和福建等有救市傳聞的城市也已經超過10個。
有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二季度越來越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量價齊跌的態勢,但糟糕的情況并不會就此停歇,預計深度的價格調整將會在三、四季度顯現出來,并且會牽連房地產業上下游的行業。
低迷的樓市無疑會波及地方財政收入,而通過刺激樓市來緩解地方財政壓力似乎是最有效快捷的方法。但是從目前來看,救市并未收到意向的效果,樓市量價齊跌的壓力仍未改善,并且正在傳導到各地的土地拍賣市場。
地方財政考驗
自4月下旬以來,土地市場迅速冷卻,多個二三線城市的大量地塊以底價成交,廣州、濟南、蘇州、杭州、南京、武漢、天津等城市流拍地塊顯著增加,底價成交在多地土地市場唱主流,溢價率、樓板價較高地塊似乎已絕跡。
進入5月份后,土地市場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呈現出斷崖式下墜。據中國指數研究院報告顯示,5月全國300個城市共成交土地1767宗,環比減少19%,同比減少45%;土地出讓金總額1375億元,環比下降30%,同比下降38%。另外,土地成交量和出讓金均不同程度銳減。
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認為,當前,土地市場進入低迷期,這將直接影響到地方的償債水平,甚至可能引發階段性土地財政危機,進而進一步影響到地方政府公共設施的建設與償債能力。
從近期中國經濟研究院發布的我國23省份“土地財政依賴度排名”(土地償債在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中占比)的結果來看,對于土地財政依賴度最小的城市也有1/5的債務需要依靠賣地償還,而土地財政依賴度排名前兩位的浙江省和天津市兩地政府債務有2/3的份額要靠賣地來償還。按照中國經濟研究院的統計,浙江省和天津市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分別是66.27%和64.56%。
另外,今年年初浙江省審計廳公布的審計公告中也曾明確指出,地方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
不過,中國經濟研究院統計數據受到了一些財政人士的質疑。東南某省財政廳的相關人士就對記者表示,雖然報告的數據來源于相關省份的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但是研究機構對于土地財政的概念理解和評價方法并不完善,結果值得商榷。同時該人士也表示受經濟下行和房地產行業調整的影響,今年地方的財政收入確實有所減少。
一位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面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大幅減少,為了穩增長大局,今年財政支出有所增加,支出力度加大、支出進度有所加快。目前來看,自5月底財政部發布通知加快預算執行進度后,山東、江蘇、廣西、內蒙古、河北等省區都已經開始重點部署,提速農田水利、生態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等資金的支付力度。同時,記者了解到財政支出進度的加快在銀行也有所反映,進入6月份以來財政存款增幅較為明顯。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當前地方政府面對土地財政受到影響的局面,一方面在不斷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另一方面通過地方債“自發自還”試點的推進促使地方融資平臺更加回歸其融資的本質。強化地方政府投資計劃及其資本預算約束機制,并逐步建立一個有利于強化地方債務約束和透明化的城市政府城鎮化融資體制。
十年黃金路
土地財政一詞并非中國獨創,但是在中國似乎起到了最“名符其實”的作用。回顧土地財政自誕生之后的十年來的發展歷程,先拋開中口徑和大口徑的土地財政收入不談,即不算因地權交易引起的相關稅收收入和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益的杠桿化所生成的“土地金融”收入,僅從小口徑的土地財政收入即土地出讓金來看,十年來和高企的房價交織在一起的土地財政可謂是走過了一段節節攀高的歷史。
在20世紀80年代末之后,土地市場在全國主要城市逐步建立。從1992年開始到2003年,我國的土地財政進入萌芽期,這一時期全國累計收到1萬多億元人民幣的土地出讓金。
在2004年到2006年的發展期,全國累計出讓土地面積達57.44萬公頃,獲得了1.9萬億元的土地出讓收入。
2007年開始,土地財政迎來了繁榮期,土地出讓金大幅攀升,僅2007年一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就達到了22.65萬公頃,收入1.19萬億元。
接下來的六年里,土地出讓面積和價款都呈現出快速上漲之勢。一直到2013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達到最高峰,全年土地出讓面積36.70萬公頃,出讓合同價款42000億元,折合地價1144億元/萬公頃。而這一數字是十年前的三倍多。
2014年一季度土地出讓收入達到1.08萬億元,同期地方公共財政收入1.95萬億元。土地出讓收入與地方公共財政收入比達1:1.8。這意味著,即便是在房地產市場不太好的時候,土地收入占地方總財力仍超過1/3。
但大凡事物的發展在歷經繁華之后逐漸走向衰落都是一種必然,從近幾年的數據上來看,土地財政也符合這一規律。近幾年,土地的拿地成本越來越高,支出的成本大量增加,若將土地出讓金扣除用于征地拆遷、補助被征地農民、支付破產或改制企業職工安置費等成本補償性支出,那么土地的凈收益將大幅縮小。
根據海通證券的測算,2010年全國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入占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地方本級收入+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比重達到了40%的最高點,從2011年開始這一比重開始有所回落,到了2012年降到了27.13%。
同時,隨著拆遷成本的不斷提高,到2012年雖然土地出讓金收入2.89萬億,但是相關補償費用卻達到2.26萬億,導致土地出讓凈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至5.88%。海通證券認為,這一趨勢還將延續,靠賣地支持地方財政的道路已難持續,即將走到盡頭。
功過之爭
土地財政由于被房價、腐敗、泡沫等問題所綁架,摒棄土地財政在學術界和輿論界呈愈演愈烈之勢。有學者就表示,本是地方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外收入,但是卻在地方政府的財政中占有很大份額。地方政府不僅預收了未來50?70年的土地收益,同時也在預支未來的土地收益,其風險不容小覷。
近幾年,因為輿論的影響,看起來似乎抨擊土地財政者呈一邊倒之勢。但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對記者表示,根據他的了解,學術界、官員里不乏對于土地財政的強烈肯定者。他認為,任何一個制度的安排一定是利弊互見的,土地財政有利的一面是為工業化、地方建設提供比較大的財源,支撐了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展。
盧鋒表示,近幾年土地財政的利弊天平開始有所傾斜,弊端大于利端,制度缺陷性愈發凸顯。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土地的基本制度處于一個不可持續的狀態中,例如,一部分農地不可能轉換為建設用地,但是現實生活中,很多農地都繞過了監管,這些問題大范圍的發生說明制度是有缺陷的。
土地財政最大的“力挺”派或許會是地方政府,對于很多地方政府來說,來自土地的收入無疑是地方財政收入的大功臣。這些收入支撐著地方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社會保障的資金需求。據了解,平均60%以上的地方公用事業建設支出需要依靠土地財政,一些省份甚至能高達70%?80%。一旦土地出讓金出現下滑,勢必造成地方調節經濟的空間受到限制。
僅以2012年的數據來看,我們大致可以如此量化土地帶給地方財政的“好處”。從大口徑的土地財政的概念來看,2012年地方政府獲得了2.89萬億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相當于地方財政的47%;當年的稅收收入中,與房地產有關的11個稅種,即土地、房地產開發和交易相關稅收,貢獻了地方財政收入的31%,合計1.9萬億;另外,截至2012年,地方融資平臺直接通過土地抵押獲取至少2.9萬億的融資。如此說來,2012 年,地方財政從土地上獲取的收入至少有4.8萬億元,如果不包括中央稅收返還,土地財政占地方收入高達52%。
同時,學術界也不乏為土地財政“喊冤”者,廈門市規劃局局長趙燕菁曾撰文指出,中國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制度—“土地財政”。沒有這一偉大的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話。
趙燕菁認為,中國能走土地財政這條路是因為計劃經濟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國有化和農村土地集體化,為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創造了條件。“土地財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場機制,將這筆隱匿的財富轉化成為啟動中國城市化的巨大資本。
格局調整
關于土地財政的是非功過雖然未能蓋棺定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土地財政已難持續已經是社會各界的共識。僅從土地市場來看,地價不可能一直無限制上漲,最重要的是土地一級市場是有限的。盧鋒稱,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貢獻度呈現出下降趨勢,因此當前財稅改革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于地方財政進行補充。
專家指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戒除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由原來的投資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我國的財稅改革進程。一直以來我國在財稅方面責權不匹配現象嚴重,中央政府應該適當將一部分財權讓渡給地方政府。另外,開征房產稅、營改增都將使地方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
伴隨著財稅改革的推進,地方財政格局在轉型的同時,相應地中央財政、企業的利益格局勢必也會做出調整。記者根據行業分析師的報告,以營改增、房產稅、分稅制改革為主線,整理出如下的調整脈絡。
第一,中央財政將分擔營改增的結構性減稅部分。而在分稅制改革方面,中央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的支出減少。
第二,地方財政最終受益于房產稅,房產稅可以彌補土地出讓收入減少的缺口,但最終結果取決于房產稅征收方案和執行情況。分稅制改革方面,地方財政的支出減少,來自轉移支付的收入減少。另外,原歸屬地方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繼續由地方征收。
第三,對于企業來說,房地產企業因市場調整其高利潤受擠壓,投資減速。同時,一些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將從營改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