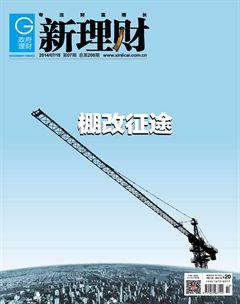回歸“第一財政”
余遠山
土地財政,一個地方財政人不愿提起,媒體窮追不舍,政府諱莫如深的詞匯。
這個詞其實沒那么深奧:土地財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屬于公共財政預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財政。
但有意思的是,并沒有“第一財政”這個定義。所謂“第一財政”,我們根據第二財政給它的延伸定義,也就是“正常的、健康發展的地方財政”。
那么,如何回歸?筆者認為,土地財政雖然還遠遠談不上“末路”一說,但最終它會以不同的路徑、不同的方式回歸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基于此,至少有三種土地財政的“解法”:政策回歸,被動回歸和主動回歸。
第一種解法:政策回歸
所謂政策回歸,即地方政府主官的政績與GDP尤其是財政收入完全脫鉤。
這是一個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極難的工作。我們往前看十年,2003年媒體即報道,綠色GDP體系正在國家統計局與環保總局的聯合攻關之中,出臺后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將與現行的干部考核體系掛鉤。綠色GDP核算制度在國內已討論很久,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已在包括北京在內的10個省市推行“綠色GDP”核算試點。所謂“綠色GDP”,通常是指在國民經濟核算過程中,把土地、礦產、水資源、森林資源、環境污染的損失等都考慮在內的一種核算辦法。
不過之后幾年的情況卻讓人大跌眼鏡。2007年,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消息,綠色GDP核算在中國還難以推開。國家統計局表示,“國際上沒有綠色GDP標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采取這樣的核算方式,所以中國還不能夠公布綠色GDP數據或者真正進行價值量的核算。”專家指出,將本著嚴謹、科學、慎重的態度,繼續開展研究和探索可行的核算辦法,把這項工作往前推進。
再之后幾年的發展更加讓人無語。2011年,某官方媒體稱,“唯GDP論”的發展思路已難以為繼。從上到下,以民眾福祉為旨歸,扭曲的政績觀正在逐漸轉向,新的發展考核指標體系也在醞釀生成中。
歸根結底,還是在原地打轉。在每年高增長的GDP推動之下,地方財政收入也不得不被一起推著水漲船高。土地出讓金的高收入,顯然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財政被逼著解決“面子問題”的一大良方。因此,要想讓土地財政真正成為歷史,首要的一點,就是要讓GDP和財政收入解綁,財政收入與地方主官政績解綁。否則即使我們有一天賣完了所有的增量土地使用權,而對于存量土地的各項稅費“依然在探討當中”的時候,代替土地財政的另一種可能更加扭曲的財政收入方式,依然盤旋于各級財政人頭頂。
第二種解法:被動回歸
如前文所言,即使我們的GDP和財政收入長久依然沒有解綁,財政收入每年強行要求增長的份額依然高企不下,增量土地畢竟是有限的。那么如果真的有一天,增量土地都賣完了,怎么辦?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種可能回歸的情況:被動回歸。所謂被動回歸,即在土地出讓金無法支撐依然居高不下的硬性財政收入增長之時,地方財政和地方政府的對策。
雖然早在幾年前就有人說“土地財政五年之內必將末路”,但眼看著五年已經過了一大半,土地出讓金收益依然是各地財政不可或缺的財政收入來源。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每一屆政府都知道地區GDP和財政收入有客觀的泡沫存在,但每個人都心存僥幸,想著它不會在自己的手里破裂。
但好在解決之道已經近在眼前。日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接受新華社訪談時表示,完善稅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改革重點鎖定六大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其中房產稅方面,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由人大常委會牽頭,加強調研,立法先行,扎實推進。
這對于地方財政來說確實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房地產稅一旦對存量房產開征,將有效的抑制以增量賣地為財政收入的地方財政的壓力。但兩個問題也隨之而來:第一,是征收增量房產稅還是存量房產稅,現在并無定論。如果只征收增量房產,或者“暫時試點”,對于地方財政來說都是一輛等不起的車。第二,何時正式開征。雖然現在已經有了幾個試點城市,但這些試點城市每一個細微動作都會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照此看來,房產稅的正式開征,顯然還需要一段相當可觀的時間。
也正因此,如果地方財政消極等待土地財政進入“第二階段”,顯然要背負相當大的風險。一些有條件的地方財政也正在思考著,通過一些技術手段,讓現在依然如火如荼的“第二財政”主動回歸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
第三種解法:主動回歸
從客觀角度來說,主動回歸,才是解決土地財政的根本之道。其實現在擁有“不靠土地出讓收入活著”觀念的地區甚眾,而甚少地區擁有解決方案。在此筆者列出幾種解決方案,或許沒有太大的可復制性,但可以引以為鑒。
第一,以企業稅收回歸。這種模式基本出自東部沿海等發達地區。由于這些地區的企業稅收本身就占到地方財政稅收的絕大部分,土地財政減少其實對他們影響并不大,只是作為企業年景不好的時候對于財政收入的一種補償措施而已。相對于這些本就擁有成熟的產業鏈的城市,一些其他城市也在以政策優惠等方式搶占企業資源。但從筆者調查結果來看,這種政府對企業的“惡性吸引”甚至造成了一些企業“吃完就走”的情況。近年來一些地區產業政策的收緊讓這種情況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并非每個地區都能以企業來作為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
第二,以主動降速回歸。這是一個無論是讓地方政府還是地方財政都很尷尬,但是卻正確的選擇。在GDP長期注水的現在,財政收入也不得不在這種大環境下變得“亞健康”。在這種情況下,擠出財政收入中的水分,率先放棄財政收入和GDP之間的“潛規則比例”關系,確實需要壯士斷腕一般的勇氣和魄力。2014年過了一半,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地方政府宣稱,今年不再以財政收入論英雄,也不再以GDP作為衡量地方官員政績的唯一標準。但這些是豪情萬丈的宣言,還是真的下定決心要首先讓財政收入的“衛星”回歸現實,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