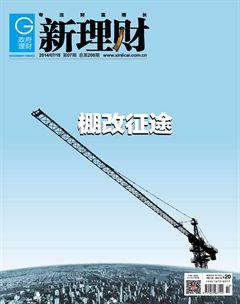碳交易多維化
喬欣
記者第一次參加“地壇論壇”是在兩年前,當時對其知之甚少,后來了解到,論壇的主題是探索中國低碳發展與碳市場建設,名字也是取了“低碳”諧音。日前,當記者再次回到這一年一度的論壇時,有些意外的發現,這個論壇已經從過去的摸索如何在中國建立碳市場交易發展出了包括碳披露與碳信息管理、林業碳匯以及節能融資模式創新等在內的更多維度的探討。
試點下一步
業內習慣于將2013年稱為中國碳交易試點的啟動元年,因為自這年6月開始,包括北京、天津、廣東等在內的七省市碳交易試點相繼啟動。
針對已經試點地區的情況,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副司長孫翠華說:“試點工作共同的特點是都明確了交易范圍,設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標,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體系,同時也建立了注冊登記系統和交易平臺,并開展了相關的能力建設。通過幾個交易試點,下一步是直接進入部署開展全國碳交易市場建設工作。包括確定碳排放交易的邊界和范圍,制定出相關的管理細則,研究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和市場調節機制,完善國家的碳交易注冊登記系統。同時開展碳期貨交易,現在開展交易的試點地區是現貨交易,不包括期貨交易,我們和證監會正在研究在國內實施期貨交易的可行性,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過首先要加強的是統計工作,也要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重點企業碳排放制度,這是碳交易市場的基礎。通過市場機制推動企業低碳發展是一個目的,同時企業也可靈活減少碳排放成本。國家層面上計劃到2020年將達到碳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
孫翠華特別強調,國家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經啟動,計劃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辦法法律地位的問題。“因為建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是個強制的市場,一定要有強有力的法律性文件才能實施,不然工作就很難推動。所以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制定全國碳市場的管理辦法、交易的管理辦法,同時開始研究各省市碳排放權分配的方法,如何分配、分配多少,是總量控制下的,還是先設一個排放權等問題都在研究。”她說。
林業碳匯新探索
隨著碳市場交易的試點,與之相關的更多探索也相應展開,林業碳匯就是其中一環。不過,什么是林業碳匯?“這是一個目前還沒有為大家所熟知,但是在行業里已經說爛了,在業外要說清楚又很費勁的一個詞匯。而實際上北京林業碳匯交易也尚處于探索階段。”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碳匯辦主任周彩賢坦言。
林業碳匯資源原本僅是一種稀缺的、具有公共屬性的環境物品,在CDM下或者是志愿市場交易的需求下,進入京都市場或志愿市場,而轉化為一種需要具備明確產權主體的財產。
北京市在2012年3月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方案,當時林業碳匯項目被納入到自愿減排交易中,鼓勵企業和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植樹造林。周彩賢介紹,在過去兩年中為了探索林業碳匯交易,他們開展了林業碳匯項目綜合管理平臺,從碳匯的登記、注冊、審定,以及項目的公示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在林業碳匯交易嘗試的過程中,我們把碳匯交易的項目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目前碳排放交易體系當中的模式,就是參與CCER或者是BCER模式。第二是自愿市場,目前主要是北京碳匯基金和義務指數購匯履責,在碳匯基金下開展了很多綜合類的項目。第三是基于碳權的配額交易模式,我們跟有關部門合作,嘗試是否能讓北京市林業碳匯的交易跳出CCER,做出碳權配額交易形式,目前正在研究進展當中。”
結合北京林業碳匯的試點情況,周彩賢表示,要把握這樣的原則:政府指導、行業自主。“碳匯的操作性和政策性比較強,這些環節上需要政府把關和指導。另外是簡化程序、降低成本。林業碳匯在交易的過程中一直受CDM項目的影響,程序非常復雜,條件非常苛刻,在交易當中尤其是從碳匯生產到計量的過程導致很多人被嚇住,本來林業就沒有多少錢,后面開發成本又這么高,最后能不能賣出去都是問題,所以程序上需要簡化。還有成本一定要降下來,在打開市場之前這是很重要的環節。”
當被問題現在林業碳匯交易的挑戰在哪里時,周彩賢直言:“首先是碳匯交易的管理細則還需要完善,碳排放交易管理辦法下規定了林業碳匯作為補充機制可以抵消,具體怎么來抵消,我們如何在各個環節,比如園林綠化局和北京市發改委在管理過程中界限和時間等等細節還沒有完善。第二,碳匯宣傳還需要加強。之前我們跑了很多區縣,發現到一些問題,一是造林地不知道歸誰,碳匯賣了錢歸誰。二是企業先讓我們投錢開發,如果交易不了,最后這個錢投入的損失誰來算,所以很多都是觀望的態度。第三,方法學和技術標準體系還需要加強。今年年初我們在做一個項目過程中發現很多方法學和國家有沖突,如何在國家的指導下統一化還是一個挑戰。第四,是計量監測與審核認定機構資質管理問題。計量監測到底如何來做,也是需要我們下一步要考慮的問題。最后,是園林綠化碳匯家底需要摸清。”
京津冀的低碳機遇
今年論壇的主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下的低碳新機遇”,不難看出,這個主題也是在努力貼合時下大熱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個國家戰略,并且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正如環保部規劃財務司司長趙華林所言,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因此必須把轉變發展方式作為統籌解決環境資源制約和霧霾等突出環境問題的根本措施。也就是說我們的結構不變,發展方式不變,我們的環境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統觀世界各地的發展經驗,凡是高碳發展的地區環境污染都是非常嚴重的,高碳意味著污染,所以我們必須要轉變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建立有利于向低碳發展轉變的體制機制,低碳發展與環境保護具有協同相應,是加大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應有之意,改善京津冀地區的環境質量,統籌低碳發展環境保護是必由之路。
而這條路究竟該怎么走?在趙華林看來,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加強頂層設計、解決環境問題是突破口。要深入研究生態環境傳遞的規律,以此引導約束城市的功能定位,規劃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
協同發展產業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來推進產業的轉移,避免發達地區把高污染高耗能的項目轉移到欠發達地區;也不能“搶桃子”,有比較好的項目都去搶。需要有一個一體化的規劃建立產業體系,統一環境的準入,合理的分工。
另外,要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加強天然氣在城市供熱、分布式能源、高效發電、電網調風等領域的應用。因地制宜發展非化石能源在風電、太陽能、垃圾發電、生物質能源方面取得突破,加大外送電比例,尤其是京津冀要吸收一些外送電。
就京津冀而言,城鎮化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建立城鎮化體系應該符合生態格局,要與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我們最近在研究城鎮化不能是‘攤大餅式的發展,一定要有生態的安全距離,也就是說城里環境質量的保證必須城外有生態的功能來確保。華盛頓周圍都是一大片禁止開發的區域,所以保證了華盛頓的空氣質量。我們不能無限制的全部開發,在城里做文章是永遠做不完的,所以最近在研究城鎮之間最小生態安全距離,一定要有距離,不能把京津冀變成打工地連在一起,這就不是京津冀一體化。”趙華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