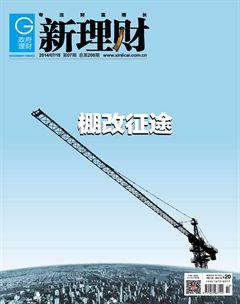農民自主城鎮化之惑
陳琴
今年年初北京鄭各莊價值9000多萬元的36棟別墅被拆,引起經濟學家、財經媒體等的廣泛關注,并圍繞“農民能否在自己土地上自主城鎮化”這個話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事實上,這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從東南沿海先富鄉村城鎮化到鄭各莊的發展,其實都是在農村集體土地上的城鎮化嘗試。它所反映的,依然是中國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城鎮化困局。
從城鎮化典型到違法用地典范
在媒體報道中,鄭各莊最廣為人知的事有兩件:一是鄭各莊被哈佛大學列入城鎮化轉型的課堂案例;二是用直升機給在高爾夫球場的村黨總支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宏福集團董事長黃福水送餛飩。
而在一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眼中,鄭各莊代表的是中國城鎮化的另一條道路。傳統的城鎮化模式,即政府主導的征地造城運動,已經越來越難以持續。200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曾專門到鄭各莊調研,從而提出了“農民自主的城市化”這一概念。
鄭各莊采用“村企合一”的發展模式,全村土地統一流轉給從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宏福集團經營,集團外只租不賣。與此同時,鄭各莊先后在1984年、1996年制定發展規劃,最終規劃于2005年獲得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正式批復。在這份規劃中,全村4331.3畝土地,除保留73.5畝農業用地外,其余全部為集體建設用地,用于建設住宅,工業、教育科研,商業文化娛樂、公共設施等。
通過30年的發展,原本為貧困鄉村的鄭各莊,2012年已經興辦了96家企業,創產值95億元。千余名村民人均純收入近6萬元,主要來自集體資產分紅收益和土地、房屋租金收益。與此同時,還吸引了3萬多外地人到這里居住和工作。
鄭各莊與其他城市周邊鄉村農民自發造城運動的不同之處,在劉守英看來,是“農民集體一方面通過宅基地的商品化和資本化,發展房地產,將土地級差收益留在村莊,用于企業發展、村莊改造;另一方面通過土地的非農化發展第二三產業,推進農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胡必亮也認為,鄭各莊“成功首先體現在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福利改善,民主化程度提高。其次,鄭各莊通過產業轉型,完成了工業化,進而改變人口聚居方式,代表了城鎮化發展的方向。”
同時,天則經濟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等機構的一些研究者也紛紛表示,鄭各莊突破了現有的一些法律規定,比如突破行政主導的規劃、集體建設用地統一規劃使用、村企合一等,是極有意義的改革探索。
而在著名經濟學家華生看來,鄭各莊只是利用了其位于北京郊區的有利位置,通過在集體土地上發展房地產富裕起來的農村,本質上是“抓住市場需求的逐利行為”。
“沒有這些大市政和交通的投入,村莊本身的自主城鎮化也是搞不起來的。換句話說,一個村莊的自主城鎮化并沒有覆蓋城鎮化的真實成本。這樣不該得的收益全自己得了,該負擔的支出又沒有負擔,這種富裕當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還會成為擴大財產和收入差距的不公平因素。”華生在其與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篇辯論中如此寫道。
一直在現行法律、法規、制度下冒險的的鄭各莊,位置越來越尷尬。隨著國土部和住建部加緊遏制在建在售小產權房,今年鄭各莊不得不拆除了其建在北京市城市規劃為綠隔區的“天價小產權房”。而鄭各莊也由城鎮化典型,變成北京市規委眼里的“違法用地無法處理典范”。
集體土地入市之困
鄭各莊不是孤例。“根據我們的調研看,在江浙、廣東、福建一帶,縣以下的地方,城鎮化幾乎都是在農村集體土地上自發進行的。上世紀80、90年代,這些地方在通過改革開放發展外貿,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產業,同時也形成了小城鎮,比如浙江諸暨店口鎮,東莞下屬的虎門鎮、長安鎮等。”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政策研究處博士魏劭琨說道,這有點類似于西歐最早的城市化過程,都是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據魏劭琨介紹,這些地方在集體土地上建廠,與使用者簽署租賃協議,實質上相當于集體土地已經流轉了。現在隨著城市規模擴大,也依然按照原有模式在集體土地上建工業園區等。區別只是當時農地、宅基地和經營性用地的管理還不嚴格,而現在這些建有廠房的集體土地無法上市,無法流轉,不能抵押融資。“現有的法律制度下,在農村集體土地上進行的城鎮化,必然要面對土地轉性的問題。”
那么,隨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轉性亦即轉為國有土地是否可以避免?
對于集體土地入市,主流觀點趨于一致,都認為是將來改革的方向。分歧在于,哪些集體土地可以入市,以什么方式入市,入市之后的各方權益尤其是農民權益如何保障等方面。這牽涉到的不只是農民自主城鎮化中集體土地使用的合法性,還包括小產權房、城中村土地使用的合法性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代表了一類人的觀點,即農地農房應該與國有土地一樣入市。據他撰文介紹,198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到1998年《土地管理法》再度修訂時,規定變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從此,城市的國有土地可以合法轉讓,農村集體土地沒有了相同待遇。周其仁堅持,既然城市房地入市沒有引起天下大亂,反而積累了經驗,農村集體土地也完全有理由急起直追,爭取同地同權。
華生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舉出的一個例子是城市工業用地與房地產用地尚不能同權,農村集體土地有農地、宅基地、經營性建設用地、公益用地之分,如何能夠“一刀切”地同權?又與哪種土地同權?土地必須在符合現代用途與規劃管治的前提下,才能談同權同價。
自主城鎮化還要面對另一個重要問題:土地的開發建筑權是公權利還是私權利。當前土地制度、規劃管理制度確實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如村莊、農民在城鎮發展規劃制定過程中缺乏話語權和知情權,也無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但若任由農村集體自行規劃發展,恐怕也難以改變集體建設用地混亂、整體水平低下的現實。
先土地還是先人
對于集體土地上市,一些地方政府也做了嘗試。在確權基礎上,北京市政府主導、海淀區東升鎮集體所有土地上建成的東升科技園以11棟農村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樓房和其他房產作抵押,獲得民生銀行5億元貸款授信。據媒體報道,國土局、海淀房管局等部門,對集體建設用地房屋所有權證抵押流轉可操作性做出確認,并出臺了抵押登記的操作流程。
但從實際情況看,這種為了引入外部資金、又囿于集體土地不能交易的法律限制,所提出的“房、地”分離抵押貸款模式,因產權和風險問題,還未得到金融機構的廣泛認可。
去年年底,深圳原農村建設用地公開掛牌入市,被稱為土地制度改革破冰之舉。但事實上,深圳轄區的土地早在2005年就統一轉為國有,此次掛牌,不過是為了解決其歷史遺留問題,與現行法律并無相悖。
而對于以鄭各莊為代表的發展模式,包括華生在內的一些專家認為,它與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要求相差甚遠。在新型城鎮化“人、地、財”三大因素中,“人”也就是農民如何進城是核心。城鎮化要讓農民不僅在城市工作居住,還應該享受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
非本村居民很難享有鄭各莊的公共福利。華生通過在廣東和江浙的調研發現,不論是小城鎮還是富裕村莊,都不對外地人開放,不允許外地人占用本地資源。同時他也指出,將外來人口進城的全部壓力放在本地不現實,在國家和聯合國的農民工融入項目試點單位浙江店口鎮,全鎮13.3萬人中,一半是外來人口,倘若只以鎮財力安排外來工入籍,需要20多年才能消化完。
“戶籍確實固化了各種利益,但這是一個國家層面的問題,一個城市或者村鎮是無法改變的。”魏劭琨對此種現狀也頗為無奈。
今年“七·一”前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和《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的出臺,有望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逐漸剝離部分附著在戶籍上的公共福利,這對解決“人”的問題無疑是一大利好。
如果說以鄭各莊為代表的農民自主城鎮化,避免了傳統城鎮化模式下政府的巨額財政負擔,保護了農民本身的利益,進而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所造成的差距,是一種方向的話,那么,現在刻不容緩的就是要讓人真正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