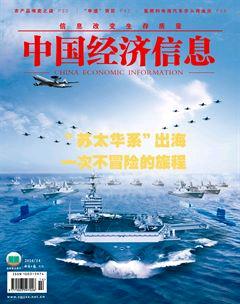“申遺”背后
錢玉娟
進入世界文化遺產之列,只是發展景區經濟的起始并不是目的,如何優化保護與再開發才是接下來的更大考驗。
卡塔爾時間6月22日, 中國的大運河項目通過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的審議,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與此同時,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也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并成為首例跨國合作成功“申遺”的項目。
大運河與絲綢之路兩處遺址,一處為南北走向并橫亙我國南北的水路,一處為東西走向且橫跨了亞歐大陸的陸路,這兩個項目的“申遺”成功,讓中國的世界遺產數增加到了47個。
在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春河看來,“這兩處遺址的‘申遺成功,是對大運河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認同,也能夠更好地保護兩處歷史文化及相關遺址。”財經評論員吳其倫也認為此次“申遺”成功,對于中國意義重大,“既彰顯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勤勞與友好,更會促進大運河及絲路沿線的經濟文化發展。”
然而,隱憂漸露:在運河和絲綢之路一線,地方政府正在籌建一些以運河和絲綢之路為由頭的景區,“申遺”成功后,遺址相關區域的開發和保護成本會否暴增?沿途景區會否出現借機抬價?背后又有著怎樣的經濟動機?
“申遺”潮涌
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地方,不僅可獲得世界遺產基金會提供的援助,更可由相關單位招徠和組織國際游客進行游覽活動,對國內外游客的吸引力則是不可小覷。
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已有百余個。按照現行的一個國家一年只能申請一處的規則,這些項目可能要等待幾十年甚至近百年。
這邊我國的“申遺”熱潮涌動,那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卻潑來冷水:世界文化遺產沒有終身制,如保護不善,即使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也將被清掃出庫,即“摘牌”。
對此,張春河強調,其實“申遺”就是接過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保存人類文化的類別與差異,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明的多樣性,使人類文明長存。“無論物質還是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或是自然遺產,任何‘申遺都是為了保護,其承擔的都是服務于全人類的義務。”
從這個意義上看,各地涌現的“申遺”熱潮理應予以肯定。然而,他指出,在這股熱潮之下,還須警惕遺產相關管理部門所謂的“重視”背后可能暗藏的急功近利。
在吳其倫看來,“跟風申遺不可取,更不能為了申遺而申遺。”對于申遺,他建議遺產所在區域仔細研究申遺規則,研究部門更應深入挖掘世所罕見的遺產,并要經過科學論證后成立申遺領導小組專司申遺。
喜憂參半
毋庸置疑,對于地方經濟來說,“申遺”成功必然會帶動旅游,從而帶來經濟利益的有效增多。正如張春河所言,“世界遺產”這一稱號就像個招牌,在吸引外商、擴大旅游的同時還可以帶來其他消費。就像當年鮮為人知的平遙、麗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不僅霎時間遠近聞名,還給當地創造出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
的確,“申遺”一旦成功,相關項目的知名度將會大幅提升,項目所在國家對于項目所涉區域的支持力度也將加大。吳其倫對《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分析到,“申遺”成功對于世界遺產項目所涉區域的旅游、文化、招商等產業及事業發展都會有所幫助,“遺址區域內的項目在獲取國際及國內資本投資方面的可能性或將變大。”
不過,根據公開數據顯示,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之后一年的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驟然躍升至500多萬元,翻了近30倍。再如陜西省的秦始皇陵申遺成功后,每天中外游客絡繹不絕,不僅增加了當地的就業機會,也帶動了周邊村民致富。還有2008年申遺成功的福建土樓,在隔年的6月,南靖土樓田螺坑景區門票由50元調整為100元,華安大地土樓群門票竟由30元上漲為90元,連翻兩倍。
此外,云岡石窟、敦煌莫高窟、廬山、九寨溝、皖南古村落、曲阜的孔府、孔廟、孔林等,伴隨著“申遺”的成功,幾乎一律是門票大幅上漲。
針對一部分景區成為“世遺”后,“暴利”頻仍的問題,張春河指出,從相關事例中看,確實存在這般情況。而像絲路所涉及的陜西7處文物點中,目前除了小雁塔、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免費外,其他景點都收取門票,有的只有10元,多的幾十元。“而從當地文物局在‘申遺后作出的規劃預案來看,漲價問題是不存在的。”
其實,旅游景點漲價與否,取決于諸多因素,比如景點知名度、客源、物價、運營成本等,“申遺”成功只是其中之一。
再開發后路漫漫
盡管“申遺”成功的喜悅仍舊高漲,毋庸置疑,這只能說是保護的階段性成功。吳其倫如此分析,“我不擔心‘申遺后帶來的景點漲價,更為擔憂的是之后可能進行的非理性開發。”
“如何讓運河和絲路保持完好,怎樣將遺產完好地交給子孫后代,是亟待思考的問題。”張春河指出,“申遺”成功后對遺址如何繼續進行保護和開發,這才是更為嚴峻的任務。
那么,“申遺”之后,如何確保遺址相關的各個城市之間的聯動仍然有效?對此,張春河認為最緊迫的便是在國家層面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得到相關水利、交通、文物等各部門的有利支持。
另外,世界文化遺產的確定勢必會給區域城市的再開發建設帶來一些限制,但張春河指出,“并不能因為‘申遺成功,相關方面就完全不建設或不發展旅游。”他認為,合理的開發利用才是最有效的保護,絕非竭澤而漁。
“‘申遺之后,首先要研究世界遺產的規則,將古城遺產保護的管理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接下來則要拉近公眾和遺產的距離,讓公眾走近遺產;最后才是將申遺成果融入當地的經濟文化中。”在張春河看來,這三點對于大運河和絲綢之路沿線的區域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最后,吳其倫還對遺址的再開發問題提出兩點建議:其一是對于絲綢之路而言,當前,我國已經啟動對這一經濟帶的規劃,“需要重在‘走出去,引進來,促進國際間經濟合作與交流”;再者,他建議在國家層面啟動對大運河經濟文化帶的規劃,“可以主打文化牌,把大運河沿線打造成為中國文化產業集聚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