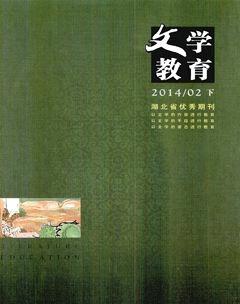《生死疲勞》的荒誕暴力與禪意內涵
鄢玉菲
內容摘要:佛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莫言的《生死疲勞》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描述了中國農村從解放后所經歷的傳奇發展和變化以及過程中的種種苦難和血腥。
《生死疲勞》展現了中國50年來農村的發展史和農民的生命狀態。它是對一個時代的解讀,是對一段歷史的解讀,更是對一個時期人性的解讀。
關鍵詞:《生死疲勞》 暴力 荒誕 六道輪回
佛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莫言的《生死疲勞》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運用天馬行空的想象,以佛家的六道輪回輔以古典的章回體模式為結構,描述了中國農村從解放后所經歷的傳奇發展和變化以及過程中的種種苦難和血腥。下面,就小說中的荒誕暴力和禪意內涵做一個簡要的闡述和分析。
1、極強的視覺沖擊——血腥而躁動的暴力
莫言一直追求一種“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的矛盾思維,偏好用惡心的事物、血腥的東西來映襯世上最圣潔、純凈的美好事情。敢于撕開現實血淋淋的外衣,直擊最深處的、最本質的人性。
書寫暴力一直是莫言小說的一大特色。《生死疲勞》中,作者的這一特色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字字挑戰著讀者的神經,一幅幅血腥的畫面自覺地浮現在眼前,給人極強的視覺沖擊。
小說的開篇,作者就為讀者上了一道大餐,呈現了人鬼受難的暴力場面。首先敘述西門鬧受盡了地獄里面的酷刑——“他們使出了地獄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將我扔到沸騰的油鍋里,翻來覆去,象炸雞一樣炸了半個時辰……我的身體滴油淅瀝,落在臺階上,冒出一簇簇黃煙。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發出肌肉爆裂的噼啪聲,頭顱似乎隨時會從脖子處折斷。”本來在油鍋里被炸就是一件極其殘忍的酷刑,作者還針對它用過分細膩的文字來描敘整個細節,讓人不自覺地感同身受,仿佛聽到了油炸所發出的噼里啪啦的響聲,雞皮疙瘩驟起。
除了開頭,后文中有關暴力的情節比比皆是,給了我們一個有一個赤裸裸的視覺沖擊。如第二世西門驢竟讓人民公社社員給活殺分食,第三世西門牛慘遭西門金龍折磨至死,第四世西門豬遇大水災救人而溺亡,第六世西門猴被派出所副所長藍開放用槍擊斃,無不以枉死告終。并且每一世都擁有著前世的記憶,給予生命重生的同時也賦予慘痛的回憶,這是對心靈的施暴。一世世的輪回,也是一世世被迫接受暴力變相凌遲的過程。另外,也可以看出,《生死疲勞》中死亡與暴力是緊密相連的。
作者描寫的暴力不是他的臆造,而是時代和生活以及個人經驗所賦予的,對于經歷過文革的作者來說,這僅僅是對歷史的一種適當夸張的再現罷了。這樣一想,突然會覺得小說原本讓人感到惡心和無法忍受的暴力竟然這樣真實,讓人在歷史的鏡子里窒息般難受,心酸地痛苦。
2、哭笑不得的無奈感——莊嚴而夸張的荒誕
正如開篇血腥的暴力給了讀者一個極強的視覺沖擊一樣,小說中荒誕的言行也讓人哭笑不得的同時深深反思。小說開頭,西門鬧對著閻王申訴冤屈,閻王卻回應他:“好了,西門鬧,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許多人該死,但卻不死;許多人不該死,偏偏死了。這是本殿也無法改變的現實。”閻王本是公正無私,嚴格執法的,卻說出了這樣一番與他身份不相符合的話語,實在是荒誕可笑。該死的人未死,不該死的人卻死了,可見連專門主宰人間生死的閻王也深感無奈,從側面表明世間已經善惡不分,混亂無章,歷史無常,生死不由人。西門鬧善行沒有善報,反而世世遭受慘絕人寰的痛苦,這甚至可以說是善有惡報了。從更深層次思考,這一設定可能是作者對歷史荒誕的一種控訴和無奈。
歷史的荒誕還表現在藍臉和洪泰岳這兩個人物遭遇的描述上。在小說的前三部中,洪泰岳是眾人所推崇的對象,而藍臉則是被當做反面教材。被孤立被排擠。可是到了第三部,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局勢有了大逆轉。生產大隊開始土崩瓦解,人民公社名存實亡。洪泰岳被迫卸任,借酒消愁。大半輩子的辛苦和堅持到頭來竟然是個笑話。而以前被認為落后的藍臉則一下子成為了典型的智者,成了先鋒,走在時代的前流。兩個人的命運發生巨大的逆轉。這與其說是命運的無常,不如說是歷史的荒誕。
除卻歷史的荒誕,小說中對人性的荒誕的描寫也觸目驚心。比如說,弒父情節的設定-西門金龍虐殺西門牛,并率領社員展開翦滅野豬的運動;藍開放槍斃西門猴,一次又一次做出吃了父親的不肖行為。這一違反倫理的行為反映了那個時代背景下荒謬的人性,在利益面前六親不認,以自我為中心的本質。又比如說,四人幫倒臺之后,人們就好像忘卻自己曾經支持人民公社化的熱情和堅決,忘卻自己曾經做過的種種冷漠之行,而是立馬轉身開始支持生產責任制,開始又一輪的熱情和堅決。不得不說,人性的確是涼薄與冷漠的。
3、生死疲勞皆因貪欲——六道輪回的清遠禪意
縱觀小說全文后,似乎理解了扉頁上的題詞——“生死疲勞,由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這四句話是佛教的經典《八大人覺經》第二覺經中的一句話。告訴我們,眾生之所以會在生死道上疲勞奔波,就是由于貪求五欲而來的。在生活的環境上,隨遇而安,不要貪得無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自在。但是莫言進一步把它和“六道輪回”聯系在一起,就賦予了生與死更深層次的內涵。
小說寫六道輪回,從投身為驢寫到投身為猴,再寫到再投生為人,是一個逐漸向人靠近的過程,有一種內在的邏輯。并且寫到身為猴子的一世時,結局和為畜之前遭槍斃的結局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也彰顯了一個輪回的終結。由此可見,小說也是對中國人半個世紀人性的發展和生存狀態的一種描述。在歷史的洪流中,人只有在經歷了驢一樣的盲目反抗、牛一樣的倔強抗擊、豬一樣的無知狂歡、狗一樣的忠誠跟隨、猴一樣的麻木與游戲著的生存,最終才能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真正聰明的、適應時代發展的,但是卻沒有靈魂的人。作者用動物的視角展現了人性的變化過程和最終結果,也可以說是人們半個世紀以來對生命和生存的思考結果。
莫言借助佛教里的六道輪回,為小說提供了立體的框架結構,讓敘述者西門鬧的靈魂附著在驢、牛、豬、狗、猴身上,以動物的眼光看人的世界,而各種動物的視角又各不相同。這種視角的處理增強了小說的形象性、直觀性和趣味性,讓讀者自行想象,創造性地理解作品所具有的反諷意味。
當然,無論從小說的命名,還是從小說的結構,我們都可以看出作者對時代洪流里人性變化的思考和人們從經受的苦難的同情,同時,也明白了貪欲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在苦難中不斷輪回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生死疲勞》用一場刺激感官的視覺沖擊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時代的暴力;用讓人哭笑不得的情節設定為我們再現了歷史與人性的荒誕;用細膩清遠的佛家經典為我們講述了“生死疲勞”和“六道輪回”的涓涓禪意。它們共同譜寫了一首時代和歷史的華章,讓我們聽到了背后所蘊含的深刻人性。
《生死疲勞》用第一人稱講述了西門鬧在解放后被槍斃,轉生為驢、牛、豬、狗、猴以及大頭嬰兒藍千歲的所作所為以及所見所聞。期間跨越了土地改革、十年動亂、包產到戶、全面改革開放等主要歷史時期,展現了中國50年來農村額發展史和農民的生命狀態。它是對一個時代的解讀,是對一段歷史的解讀,更是對一個時期的人性的解讀。小說用荒誕的語言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反思歷史、反思人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