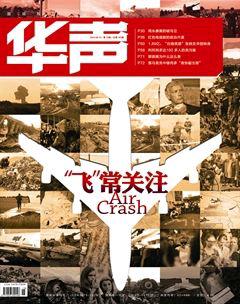檢察系統躋身“反腐主力軍”
沈念祖+趙冰潔
中國的反腐有這樣一句俗語:中紀委打虎,最高檢收籠。
近期,這一“路徑”有望被優化調整。
長期以來,中國式反腐有一條固定的“路徑”:先由同級紀委雙規、調查取證、發現基本犯罪事實或線索后,經黨內處理后再“建議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將案件交由檢察院偵查起訴。近期,這一“路徑”有望被優化調整。
《人民日報》7月28日刊發的《檢察機關反腐開啟新模式》中,首次將“反腐敗主力軍”的稱呼同時給了紀檢監察和檢察兩個系統。“今年以來,我國反腐明顯提速,紀檢監察和檢察兩支反腐敗主力軍頻頻發布案件查處通報,大批貪腐官員落馬。”此前,唯有紀檢系統被認為是反腐的核心與主力。
在去年年底最高檢關于如何提升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辦案能力研討會上,已有學者透露,中央計劃對紀委和檢察機關的辦案流程做出優化調整。與種種跡象相對應的是,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明確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這為推進新形勢下的反腐及廉潔政治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舊有路徑
長期以來的固化路徑,讓中國的反腐有了這樣一句俗語:中紀委打虎,最高檢收籠。即先由中紀委對官員“違紀”問題立案“審查”,中紀委設有案件審理室,負責對黨內官員的違紀問題進行審理,然后再由檢察機關對其“違法”問題立案“偵查”。
梳理十八大以來3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的落馬,無一不是遵循這一模式。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解釋稱,中國反腐的第一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反腐敗的權力結構上,中央紀委處于最高地位。紀檢監察機關是我國反腐敗工作機構和監督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紀委辦理一件貪腐案件時,一般需要經過案件受理、初步核實、立案審批、調查取證、案件審理、處分執行等多道辦案程序,再移交司法機關。
并非所有到了紀委的問題官員都需要被移送司法機關,近期就有兩個意外,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和江西省委原秘書長趙智勇未被移交司法機關,只給予了黨政處分。不過,只要在紀檢機關接受組織調查時提到涉嫌“嚴重違法違紀”的,一般均會被移送司法機關。
長期以來,對于紀律檢查部門和檢察院之間的職權如何劃分一直有爭議。
趙中權在《反腐敗要走法治化道路》一文中指出,在處理腐敗案件中,大量涉法案件使紀檢監察機關常常干了司法機關的事。在監督檢查中,由于大量涉及政府及其部門執行法律法規的問題,使紀檢監察機關又干了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事。一些重大案件,由紀檢監察機關牽頭協同辦案,實質上逾越了紀檢監察機關依法履職的邊界。這種機制弱化了人大及其常委會、司法機關的法律功能,不利于共產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基本方略的實施。
去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研討會,研究檢察院如何提升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辦案能力時,就已涉及紀律檢查部門和檢察院之間的職權重新劃分問題。當時參與研討會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透露,為了減少“重復勞動”,中央計劃對紀委和檢察機關的辦案流程做出優化調整。即紀檢部門在查處黨員領導干部違紀的案件中,一旦發現其涉嫌違法犯罪,立即移交檢察院偵辦。
姜明安還表示,紀檢部門不是司法機關,沒有司法調查權(包括凍結銀行存款,秘密監視居所以防止轉移財產和跟蹤同案阻止其掩藏銷毀證據等),此時具有合法偵查手段的檢察院又無法介入,可能造成證據滅失,不利于懲治腐敗打擊犯罪。另外,法律對司法機關辦案期限,如何調查取證都已做出明確的規定,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更規范,有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上述檢察院工作人員認為,讓檢察院直接介入辦理,是對其功能性的極大發揮,也是對檢察權和審判權獨立性的極大尊重,有助于將司法反腐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同時,作為一種國際性慣例,檢察院直接介入辦理也符合反腐體系調整的趨勢。
新的力量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這對于最高檢與最高法來說,意味著更加廣闊的空間。
從4月開始,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在官方網站、微博、微信上公開落馬省部級高官立案偵查及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信息,并將貪腐案件所涉罪名、辦案流程、時間節點等關鍵信息公之于眾。與之相呼應,江蘇、河南、江西等多地檢察機關,也紛紛公布省內大要案信息。
從今年3月最高檢官微開通至今,共發布了16件由最高檢立案偵查的大要案信息。
據悉,全國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系統于7月底分別在山東、四川以及北京、上海、黑龍江、河南、甘肅分兩批進行試點運行,并將于今年9月底在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全面部署使用。屆時各級人民檢察院將通過該統一的平臺,向社會發布重要案件信息,公開法律文書,向相關人員提供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詢服務等事項。
同時,為了規范重大案件信息發布,最高檢7月份出臺了《職務犯罪大要案信息發布暫行辦法》,對應當發布信息的職務犯罪大要案范圍進行了界定,將省部級、廳局級官員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縣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主要領導涉嫌職務犯罪案件,重大責任事故、重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等產生重大社會影響事件背后的職務犯罪案件均納入信息發布范圍。
今年以來,檢察機關還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打擊力度,力圖改變查辦賄賂案件時“受賄‘罪大惡極,行賄‘罪輕一等”的現象。
最高法還在推進司法反腐方面下了功夫。7月30日,全國四級法院舉報網站正式聯網,為上級法院紀檢監察部門實時察看下級法院處置舉報線索的情況提供了技術保障,有利于上級法院紀檢監察部門充分發揮監督指導職能,有效防止個別下級法院隨意處置舉報線索,甚至出現瞞案不報、壓案不查等問題。
反腐法治化
除了注重司法反腐的具體實踐,反腐敗法治化理論研究也在今年被最高檢提上議程。
6月22日,國內首家反腐敗法治研究機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宣布成立。與此前成立的北大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側重于紀監反腐不同,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是側重反腐敗司法研究,尤其是檢察系統的反腐敗司法研究。
姜明安介紹,“目前研究中心還沒有布置明確的研究任務。預計該中心將側重研究并推動將反腐納入法治的軌道,既涉及理論問題,也包括具體的技術問題。”
姜明安認為,理論問題將涉及如何理順紀檢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關系以及職責權限等。從未來的趨勢來看,紀委和檢察院的工作銜接將進一步優化,檢察院將更多擔負起對涉案官員是否犯罪及其相關事實認定的責任。技術問題則包括進一步加強對職務犯罪的研究,包括罪與非罪的認定、調查取證的技術等。
紀委和檢察院在反腐中分工明確,有利于打擊貪腐犯罪,但不會削弱紀委進行黨內監督和預防犯罪的地位。當檢察院可以直接介入辦理之后,反而意味著各級紀委的事務性工作會得到極大的緩解,使其有更多的精力轉向黨內的監督和預防犯罪制度建設,更多地充當指揮者而不是裁判者的角色。并在此基礎上,通過逐步的放權,最終達到查處分離的轉變。
趙中權對此也持相同意見。他在上述名為《反腐敗要走法治化道路》的文章中還建議:“我國現行反腐敗機構設置較為分散,缺乏統一、相對獨立的反腐敗部門的狀況,難以適應法治化反腐敗的要求。有必要,而且必須從機構設置上解決反腐敗法律的執法主體問題。根據我國國情和實現法治化反腐敗的需要,可考慮對現有分散在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局)等反腐敗專門機構進行整合,建立‘國家反腐敗委員會,作為反腐敗相對獨立的專門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