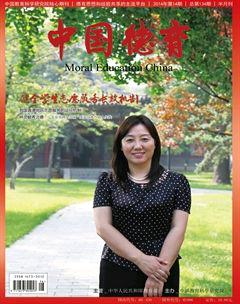談仁德
肖群忠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孝與中國文化》《中國道德智慧十五講》等。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諸多歌星就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每一個人都在內心涌動著對愛的渴望。建立一個充滿愛的和諧社會,是我們的理想。“愛”是我們生活中最常用的語匯,用儒家學說的范疇和德目來表達的話,那就是“仁”。反過來說,“仁”就是儒家所說的“愛”。今天,我們就來學習儒家所倡導的仁德。
仁德的內涵
那么,仁作為德性和品質規范,它究竟包含哪些品質或者說有哪些道德內涵呢?在《論語》中雖然言仁之處很多,但并未給仁下一個定義。這里,我將以自己粗淺的學養,斗膽對此進行必要的歸納與概括。根據經典論述,我個人理解,仁德內涵似乎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仁者愛人的道德情感,親愛同情的人性根源,忠恕之道的行仁方式,克己復禮的修養實踐,博施濟眾的奉獻精神。下面,我們從上述幾方面分別展開分析。
1.“仁者愛人”的道德情感
仁是什么?孔子、孟子明確指出了仁就是“愛人”的道德情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以“愛”釋“仁”是歷代儒者論“仁”的不二法門,從一開始就奠定了中國倫理的利他主義價值導向。
仁者愛人,仁愛的感情,是對他人的一種喜歡、親近、需要、依戀、關懷、體貼和愛護,即竭力不使對方受到傷害的溫和友善態度。儒家的仁愛強調等差之愛,即親親-仁民-愛物,儒家認為,愛的這些層次、差等,表現了人的自然真實感情,是由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乃是人本性的有序擴散。仁愛最根本、最核心的是親親,即愛父母。“愛莫大于愛親”,盡管如此,儒家并不主張將仁愛止于親親,而是提倡將愛按層次層層推開,也提倡“泛愛眾”,以至于“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達致“民胞吾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之境界。但這種推擴卻是有順序、有先后、有差別的,如人首先要愛父母勝于愛妻子,愛家人要勝于愛他人,否則就會亂倫而不合儒家之等差之愛原則,從而是不道德的。
由于儒家思想的基礎是建立在血緣宗法關系基礎之上的,因此儒家的等差之愛雖然顯得有私情的偏向,但仍因為它的合人情性,比較適應于傳統中國的文化土壤,為民眾所信服,最有實踐性和操作性,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儒家思想長期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的原因。當然,我們在建設現代化的今天,要樹立一種公意精神,汲取墨家與西方博愛思想的合理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我們只愛家人和熟人,而不愛生人和大眾,那么,公意精神和公民社會就難以建立。
2.“親愛同情”的人性根源
仁是愛人的情感,那么,這種愛人的情感源自于哪兒?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孝為仁之本”,孝即愛親,也就是說愛親是愛人的精神根源,仁是對愛親感情的一種擴充。孟子說“親親,仁也。”(《孟子·盡心上》)“仁之實,事親是也。”可見,“親親”是“仁”的要旨和根源,血緣親情是“仁”的自然基礎,仁產生于愛親之孝,實踐仁也須從“愛親”做起,故《禮記·祭義》述孔子之言曰“立愛自親始”,《論語·學而》亦載有子之言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從愛的精神源頭上,我們認為仁是產生于愛親之孝。那么,從眾人人性的角度看,仁愛的道德情感產生于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即人對他人痛苦的一種同情與關切。作為“同情”,就是指他人的痛苦也到了我這里,而我的心也到了他人那里,這就是心靈相通。富于同情心是個人道德意識的源頭,是道德行為活動的最初動力。經驗也證明,如果一個人對人類這個同類的痛苦缺乏基本的同情心的話,就會“麻木不仁”了。
對別人的不幸感同身受,對他者的受苦心懷不安,僅此還不夠,作為一種道德感情的同情心還包含在看到人們遭到嚴重困厄與痛苦時,去主動關懷和協助,即積極行動。
3.“忠恕之道”的行仁方法
那么,如何去愛他人呢?這在思想上首先要有一個普遍的思考方式,這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實現“仁者愛人”的途徑和方法,是通過將心比心的體驗去愛人,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考量。所謂“恕道”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說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加給別人。“忠道”是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自己有所樹立,也應要別人有所樹立;自己有所通達,也應要別人有所通達。簡單地說,恕道就是理解人、包容人,忠道是關心人、幫助人。仁愛之心告訴你要愛護幫助他人,而忠恕之道給出了明確的指令,使仁愛之心變為明確的義務意識。
《大學》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所謂絜即度量。矩即制作方形的方尺,引申為法度、準則。絜矩就是以法度度量事物,以自心感受衡量、理解他人,并要求自己,從而遵循道德規范。這種絜矩之道與忠恕之道的實質是相同的,也就是要求將心比心,善待他人,嚴格要求自己,換位思考,反復體驗,推己及人,以己度人,通過這種交叉體驗,多方理解他人,并嚴格要求自身。因此,它既是實現仁德的方法、途徑,也是自覺修身的方法和要求。
4.“克己復禮”的修養實踐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這就是說,克服、戰勝自己的私心、私欲,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于禮,便實現了仁。仁是禮的內在基礎,一旦具有仁的品德,便能自覺遵守禮制。另外,仁又必須以禮為表現形式,通過禮來節制、規范,即按禮的規定去愛人,遵守人倫之禮是仁的外在體現和行為規范。或者說,仁者愛人,就是要求人們以禮待人。
從仁愛之心的基本倫理精神的角度看,儒家強調“仁”與“禮”的結合,即“克己復禮為仁”,也就是說,克己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社會道德義務,也是人在道德上自我實現的唯一途徑或行仁之方。既然人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角色,是生活在社會關系之中的,那么,人們就必須遵守一定的社會規范和行為方式—禮。守禮就是遵循通行的道德規范,實際就是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會的良好秩序。
仁愛不僅要復禮守禮,而且要以克己為前提,即克制自己的私欲。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如果出于自私、利己之心,就不僅不能愛人、利人、助人,甚至還會損人、傷人、害人。因此,要培養仁愛之德,就應首先從克制自己的自私利己之心做起。重“克己”,這是儒家仁學的又一重要內容。隨著利己與愛人的矛盾沖突愈益尖銳,宋代理學家對“克己”更為重視,他們大都直接以公釋仁,以去私作為為仁之方。如朱熹說:“公而無私便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朱子語類》卷六)事事出于私心就不能愛、不能仁,所以,“無私是仁之前事”(同上),離開無私這一前提就沒有仁。因此,要做到仁,不僅要遵守社會道德規范,而且要從克己做起。當然克己不僅是指在思想上克制自己的私心,而且,也指在行為上克制自己言行上的任意偏私,這實際上是與復禮或守禮相一致的。
5.“博施濟眾”的奉獻精神
人不僅要遵守社會道德,還要奉獻社會,促進社會進步。孔子要求君子、賢達、君王要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高尚道德品質。《論語·雍也》載:“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對于統治者來說,愛人即表現為愛民。孔子曾一再希望統治者應養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不僅要在思想上具備這樣的德性,而且要在政治上實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要統治者不僅“不嗜殺人”,還要“省刑罰,薄稅斂”,無奪農時,使民“不饑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進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為民父母,在政治層面上施行仁政。
另外,作為一種廣泛的道德要求,博施濟眾要求一切“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都要把仁愛之心不斷擴充,盡可能做到為天下蒼生謀利,一切行為均以老百姓得到實惠為宗旨。在儒家仁愛精神引導下,古代的許多仁人志士堅持天下為公、奉獻社會、造福民眾。這些都是以仁愛精神為基礎的,也是“仁愛”精神之自然的擴充與提升的必然結果。
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弘揚仁德
上面,我們分析了仁德的內涵,那么,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弘揚仁德呢?
1. 以同情愛人之情喚醒我們的道德良知
對他人的愛和同情,是產生對他人善意(而非惡意)的精神源頭。人如果對自己的同類,甚至是動物和生命缺乏基本的同情和愛心,那么,這個人可能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人性。“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在孟子看來,人有惻隱之心,是人的本性,而無惻隱之心,就不是人。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因此,人總要有一種類意識,對同類的不幸懷有一種惻隱同情之心,由這種同情之情而激發了對他人的愛、關懷與幫助。仁德是儒家之源,而這種惻隱之心與愛心又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仁的道德情感不僅包括同情心,而且,也包括積極的愛人、助人精神,這更是道德精神的原發性、動力性的根源。我們不僅要對他人有同情心,而且要有愛心,愛人是一種積極的情感,它會把人引向對他人的善意、關懷和幫助。
2. 以忠恕之道培養我們的他人意識
心有他人是道德在人際關系上的最直接的體現。明代思想家呂坤在其著作《呻吟語·應務》篇中曾說:“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我們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要與他人打交道,能否心有他人,是一個人有無道德素質的表現。在生活中要常想想,你有沒有給別人添麻煩,比如,在人家午休時或其它不適當的時間給別人打電話?是不是請求別人替你辦事,為難別人了?等等。總之,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要想想對別人是否造成不便與傷害,這就是恕道的根本精神。而有了這種恕心,實際上就是進德之門了。
清末學人石成金編了一本書很有名,叫《傳家寶》,在該書中,他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將心比心,強如佛心。”(《傳家寶》初集卷六《天福編》)他還說了一句話:“惟恕可以成德。……恕則無人我之私,故能進于德。”(《傳家寶》三集卷二《群珠》)這句話是說,恕心之所以能進德,就在于在人我關系上,恕心能處處想到別人而無私心,所以能進德。
另外恕道還有一種根本精神就是要嚴己寬人,反求諸己。恕道要求我們對他人應寬容,得饒人處且饒人,當然這種饒人不是無原則的縱惡,而是在同情了解的基礎上對他人的體諒和理解。但對自己則是要嚴格要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待人接物的高尚道德品質。韓愈說:“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則不怠;輕以約則人樂為善。”嚴以律己是道德修養過程中追求道德進步與完善,攀登道德高峰的階梯;處理人際關系嚴以律己能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友好情感,有矛盾時有利于化解矛盾。寬以待人,要有恢弘的氣量,寬廣的胸襟。對人寬容大度,往往會使環境寬松,氣氛和諧。人在寬松的環境里,在和諧的氣氛中,會心情舒暢,“人樂為善”。人有個性差異,在人際交往中應當承認這種差異,要尊重不同的個性,求大同存小異。不能強求別人與自己一樣,不能容不得不同意見,更不能排斥異己。道德高尚的人應該胸襟寬廣,氣度恢弘。古人說“量小非君子,德高乃丈夫”,就是要我們提高道德修養,待人寬容大度。待人寬厚隨和,與人為善,人亦與己為善。對待他人寬容大度,有利于他人進步,苛求刁難會妨礙他人進步。
他人意識不僅包括恕道即同情、寬待別人,而且要有忠道即盡己利人,與人為善,助人為樂。時時處處不僅心有他人,理解他人,尊重他人,而且要為他人積極奉獻,周窮濟困,財以濟人,力以助人,智以勉人,德以化人。
3. 以博施濟眾提升我們的奉獻意識
仁德既是道德的起點,又是一個不斷追求的很高的境界,因此,孔子也不輕易以仁許人,甚至認為自己也還達不到仁的至高境界。相對前面所說的同情仁愛、忠恕之道來說,博施濟眾就是一個更高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我們要以天下蒼生為念,以天下為己任,以奉獻民眾為樂。愛最終就要體現為奉獻精神,“仁愛”精神倡導博施濟眾、天下為公,與我們今天所講的為人民服務有內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一個人如果立志做一個仁人志士,那么,就一定要拋棄一己之私,要有寬闊的胸懷和為天下蒼生和人民謀福利的理想。一個偉大的人,就是一個仁心廣施的人,如佛祖為什么要普渡眾生,就是基于他對眾生所受苦難的關切。樹立奉獻意識固然要從人生實踐中不斷的努力,但從傳統仁德中汲取博施濟眾的思想資源也是提升我們的奉獻意識的重要途徑。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孔子說:“仁離我們很遠嗎?我想要追求仁,仁就會來到的。”也就是說,只要我們下功夫,就一定能追求到仁,即使不能成為仁人志士,也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從而成為君子。仁就是愛,愛就是奉獻,讓我們從自己、從現在做起,多點愛心,去愛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同事,我們的同胞以及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責任編輯/楊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