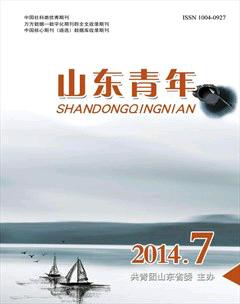論藝術構思與想象
劉雅麒
摘 要:《神思》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六篇,主要探討藝術構思問題。從本篇到《總術》的十九篇,是《文心雕龍》的創作論部分。《神思》篇是劉勰創作論的總綱,主要介紹了劉勰對藝術構思與想象的看法。本文分析了“神思”的概念,就其中的“神與物游”、“貴在虛靜”、“博而能一”幾個方面試論析劉勰對外物、作家情感氣質、“虛靜”、學習積累等問題與藝術構思、想象關系的認識。
關鍵詞:劉勰;神思;藝術構思;想象
一、何謂“神思”?
《文心雕龍·神思》開宗明義,篇首就提出了“神思”的概念:“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①王元化先生認為“神思”是劉勰“對想象所作的定義”。[1](P 129)筆者認同此觀點,認為劉勰的“神思”,指的是作家的創造構思活動,進一步說就是作家創作構思中的想象活動。“神思”既包括形象的物,也包括抽象的情感,是從事文學創作,是溝通客觀和主觀世界的橋梁。[2]
“神思”最早見于南朝畫家宗炳的《畫山水序》:“完趣融其神思。”這里的“神思”,即指的是以想象為中心的藝術思維活動。陸機《文賦》首次把神思引入文學領域。如“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②,劉勰《神思》在陸機的基礎上,對藝術構思與想象的理論方面有更加深入地理解與說明。如“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這也正是“神思”的神奇魅力之所在。
二、“神與物游”
《神思》說“思理為妙,神與物游。”“思”的產生有感于“物”,而“物”的變化則引起了“思”的變化。但這里的“物”不是客觀外界廣泛的事物,而僅指不包括社會生活在內的自然景物。如“有形貌有聲響,可以耳聞目睹之物。由人們活動所構成的事實,并無形貌,就不屬于物。”[3](p79)
王運熙認為,由于漢魏到南朝的文學創作以詩賦為文學作品的主要樣式,寫景狀物的山水詩又是詩賦的重要內容之一,故劉勰在文學批評方面也以詩賦為主,在討論藝術構思與外界事物關系時,單獨強調代表自然景色的“物”。[4](p80-83)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中的山川河海和“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中的“風云之色”,皆自然界之景物。王元化也認為,“物”在《文心》中幾乎都作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稱謂”。[5](p83)
在作家構思與“物”的關系方面,劉勰認為,“物”是創作者藝術靈感的出發點,可以激發想象,是構思得以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如“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神思”是以審美情思為運思動力,以事物表象為運思“實體”的“神”與“物”相互融合的過程。[6]筆者認為,劉勰的“神與物游”不僅是藝術構思的方法,也是藝術構思可以達到的境界。如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說:“神與物游……必令心境相得,相見交融。”[7](p118)這就是主客觀世界相通的“神與物游”正是藝術構思與想象達到的最佳境界。
三、“貴在虛靜”
劉勰認為作家進行藝術構思與想象時,很重要的前提是“虛靜”。“虛靜”即為一種不受主客觀因素干擾、心無旁騖、專心致志的精神狀態。陸機最早將“虛靜”說引入了文學創作,在《文賦》中提出創作主體應““虛靜心以凝思”。劉勰吸收此前歷代諸家有關“虛靜”說的精神內核,明確指出的藝術構思“貴在虛靜”,這既是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后人創作實踐的指導。
虛靜可使作者心胸拓寬,容納萬物,激發想象,提高作者的藝術開闊能力,有利于創造靈感的激發。上文提到的“神與物游”實質講的是主體的心境自由,不為世事與天地萬物所束縛的自由精神。而虛靜恰恰可以使創作者掃除雜念,保持心境寧靜專一、情思凈化,讓心靈獲得自由,充分調動思維的活躍性,達到“神與物游”之境,產生出絕妙的藝術構思。
四、“博而能一”
劉勰在比較了藝術構思“遲速異分”的兩種情形后,提出了“博而能一”的主張。黃侃認為:“博而能一 四字最重要。不博,則苦其空疏;不一,則憂其凌雜。”[8](P120)博,是見識廣博,知識深厚。“能一”有兩層意思,既指在廣泛學習的過程中要守住一點深入研究,也指在創作過程中,應有重點、中心突出。劉勰告誡寫作者只有加強平時的日積月累,寫作時才可能文思泉涌。
在“博而能一”的具體做法上,劉勰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積學”是指積累寫作素材。“酌理”指吸取思想觀點。“研閱”,是學習寫作藝術。“馴致”是說恰到好處地組織言辭,正是上面三種準備工作做好的基礎上對藝術構思的表達。[9](P85)
一些研究者認為“研閱”是“研究生活經歷”,如牟世金、陸侃如等就持有此論點。但王運熙認為,“研閱”應表示閱讀他人的文章。魏晉南北朝文學偏重抒情寫景,文人多不重視反映社會現實的敘事作品,不關心社會現實情況。《神思》篇談創作學習,只強調從書本中吸取養料,而不重視作者的生活經驗。這并不是劉勰的個人局限,而是整個時代的風氣,也是文學創作影響到文學批評的結果。[10](P85-87)
五、結語
《神思》是劉勰創作論的總綱,反映了劉勰對藝術構思與想象問題的理論性認識與總結“神思”中既包括形象的物,也包括抽象的情感,是從事文學創作時溝通客觀和主觀世界的橋梁。劉勰認為,創作者只有通過博學、積累,在情感凈化、專心無騖的“虛靜”狀態下,通過思想感情的激發與推動,才能達到“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神與物游”之境,獲得絕妙的藝術構思與想象。劉勰的《神思》為中國早期文論中系統論述藝術構思與想象的經典之作,他提出的有關藝術構思與想象的理論認識,對今天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注釋]
①頁下注:本文中所引用的《文心雕龍》原文,均出自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之后不再另作注釋。
②頁下注:本文所引用的陸機《文賦》原文,均出自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不再另作注釋。
[參考文獻]
[1]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9.
[2][6]李金坤.<文心雕龍·神思>創作要義新繹[J].江蘇:江蘇大學學報,2005,(2).
[3][4][5]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9,80-83,80.
[7][8]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118,120.
[9][10]參見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5,85-87.
[1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2]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王利器.文心雕龍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選譯[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
[15]陸侃如、牟世金.劉勰和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 文化傳播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