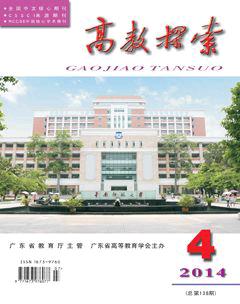大學生就業:愿景與現實
收稿日期:2013-11-18
作者簡介:吳迪,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1)摘要:我國大學生就業存在著愿景與現實的沖突。在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的雙重影響下,國家和個人共同構筑了大學生美好的就業愿景:人力資本理論為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從不同角度驗證了教育程度與終身收入的正相關關系。然而,在過度教育和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的雙重作用下,卻導致了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本來由于過度教育就已經導致了大學畢業生就業競爭壓力的增加,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中,這種就業壓力又被濃縮在了主要勞動力市場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內,加之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作用,主要勞動力市場由外部市場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生的就業壓力。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人力資本理論;篩選理論;過度教育;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實行“雙向選擇”、自主擇業以來,大學生就業問題便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進入21世紀,伴隨著高校的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迅猛增加,就業壓力日益突顯,“大學生就業難”越來越成為困擾教育主管部門、高校和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主要問題,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于是,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便成為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的頭等大事,就業率成為考核高校以及高校考核二級學院的重要指標。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紛紛出臺政策鼓勵和引導大學畢業生創業、面向西部和基層就業,高校紛紛開設就業指導課程、開展創業教育、拓展就業市場、舉辦校園招聘會。雖然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但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似乎并未從根本上得以破解。大學生就業依然存在著愿景與現實的沖突。本文擬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對其進行分析。一、大學生就業的愿景——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的雙重影響“一系列范圍廣泛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中的教育、職業、以及工作收入間存在正相關關系”[1]。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有很多種,其中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人力資本理論正式創立于20世紀60年代初,其標志是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的一篇題為《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演講,他認為: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以這一演講為開端,逐漸形成了一股人力資本研究熱潮。早期對人力資本理論做出貢獻的還有貝克爾(Gary S.Becker)、明塞爾(Jacob Mincer)、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等人,“他們彌補了舒爾茨只注重宏觀分析忽視微觀分析的理論缺陷,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諸項因素的具體化、數量化分析”[2]。舒爾茨等人區分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并認為人力資本雖然既有量的方面又有質的方面,其基本的數量特征表現為人口數量、投身于有用工作的人口比例及實際勞動量,但是可以忽略數量的因素,只考慮技術、知識及影響人的生產能力的屬性之類的質量成分。由于提高人的這種能力的費用也增加人類活動(勞功)的生產能力的價值,所以,它們將產生一個正數收益率。[3]貝克爾對人力資本進行了界定,認為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資本,而人力投資是指“通過增加人的資源影響未來貨幣與心理收入的活動……這種投資包括正規學校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健、遷移,以及收集價格與收入的信息等多種形式”[4],并且特別強調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的重要作用。
人力資本理論關于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的主要觀點是:勞動力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個體在特定工作崗位上的勞動生產力主要依賴能力,而能力主要是通過教育獲得的。個體通過接受教育,可以增加知識和技能,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與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個體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個體在教育方面投資的不同導致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位置和收入的差距。此外,人力資本投資對個人和社會都有益處,對個人而言,教育能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終身收入;對社會而言,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的經濟增長。“這一理論暗示由于投資收益是教育決策的根本驅動力,因而家庭和社會在投資時將努力確認教育與就業的相關性。”[5]
篩選理論是由斯賓塞(A.Michael Spence)等人于20世紀70年代創立的。它由一系列理論構成,如信號理論、過濾理論、篩選理論、檸檬理論、文憑主義、威爾斯假說、羊皮理論等等。篩選理論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挑戰的焦點在于教育能否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否認教育對個人收益的積極作用。篩選理論分為強篩選理論和弱篩選理論。強篩選理論認為教育只是獲取某些職業的門票,教育僅僅能鑒別學生的特質,并不能導致或改善這些特質,對勞動生產率沒有直接的影響,“只不過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因此純屬浪費”[6],這種觀點難以使人信服。弱篩選理論認為教育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更主要的是提供能力方面的信息。強弱兩種篩選理論的分歧“不是在于教育是不是一種分類機制,而在于分類是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7]。
?教師與學生?大學生就業:愿景與現實篩選理論關于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的主要觀點是:雇主總希望挑選到具有高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力,但在勞動力市場上信息是不對稱的,雇主在掌握自身對勞動力需求方面的信息占有優勢,而求職者在掌握自身出賣勞動力的意愿的信息方面占有優勢。當雇主與求職者相遇時,雇主缺乏對求職者過去表現的精確測定方法,因此無法了解求職者的真正能力,難以預測求職者未來的表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雇主會使用一些“過濾器”來挑選勞動者,如天生的“標識”——性別、種族、家庭背景等,后天的“信號”——婚姻狀況、工作經歷、教育程度等。而教育則從所有“過濾器”中被分離出來成為受法律許可并被廣泛接受的篩選機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能夠發出一種信號,即較高的學歷文憑攜帶著較強的能力、較強的紀律性、努力工作的素質等信號,這些信號預示著求職者在未來的工作表現中會有較高的水平。因此,雇主們非常樂意采取這種“統計判別法”從社會群體中分離出非典型的成員;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數人都認為按教育程度錄用是完全公平合法的。這樣做的結果是,雇主們通過教育程度篩選勞動者,較高的教育程度便會帶來較為理想的崗位和較高的收入,激勵著求職者發出相應的“信號”,以增加被選中的機率,導致了人們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此外,教育作為篩選機制具有“配置效應”,“即使教育本身沒有促進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它能夠把勞動者分到各種工作崗位也可以促進勞動生產率”,因此,“從教育得來的信息對社會也是有價值的……它防止了盲目的非最優的人才配置”[8]。
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大學生的就業愿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國家層面看,人力資本理論提供了大力發展教育的充分理由: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進而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舒爾茨采用收益率法測算了人力資本投資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資對美國1929~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其比例高達33%”[9]。教育的這一功能恰恰與我國經濟建設的大環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吻合。教育是一種投資行為,既然是投資,必定會有收益。薩卡羅普洛斯(Psacharopoulos)測算出了發展中國家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小學教育為27%,中等教育為15%,高等教育為14%,而且做出判斷:教育投資的各種收益都大大超過了10%的資本的機會成本的一般標準,并且不發達國家的教育收益率比發達國家高。[10]高等教育的社會收益率雖然沒有初等和中等教育高,但仍然是具有較高收益的投資行為。上世紀末我國啟動的高校擴招,儼然是將高等教育看作了投資行為,其目標是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擴招的確使得大量原本高中畢業后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進入了高校,減少了勞動力市場上與因國企改革而下崗的大量工人的競爭,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國家沒有考慮到四年后第一批擴招的大學畢業生大量涌入勞動力市場而帶來的壓力嗎?人力資本理論給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認為“勞動力市場有能力持續吸收教育水平較高和培訓程度較高的勞動力,只要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資可以靈活下調”[11]。此外,我們還有兩個信念,一是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就業崗位會隨之增多;二是高等教育是“蓄水池”,可以減緩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流入量,使勞動力市場保持適度的壓力,充分運用市場的調節功能,可逐步實現良性循環。繼本科擴招后的研究生擴招便是實例。
endprint
從個人和家庭的層面看,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均給出了美好的就業愿景,雖然在教育能否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存在分歧,但是二者均揭示了教育程度與終身收入的正相關關系。不管雇主是看中了由較高程度的教育帶來的較高的工作能力,還是看中了較高程度的教育發出的信號所蘊含的較高工作能力的預期或帶來的較低的培訓成本,也不管個人和家庭是否知曉這兩個理論,總之他們都確切地看到較高的教育程度會帶來較好的工作崗位、較高的工資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越來越多的家庭和個人已經把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種投資行為,對較高的個人收益充滿著期待。即使是在目前大學生就業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熱情仍然有增無減,因為人們始終追求著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接受高等教育至少還有機會達到這一目標,不接受高等教育則達到這一目標的機率為零。
此外,雖然人力資本理論的實證研究也揭示了教育的個人收益率大于社會收益率,這種差距在高等教育階段更大,[12]國家對發展高等教育的愿望沒有個人強烈,但是迫于公眾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壓力,為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加之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教育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篩選理論告訴我們“配置效應”也可以促進勞動生產率,國家發展高等教育何樂而不為呢!于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和篩選理論的共同影響下,國家和個人的相互作用構筑了大學生就業的美好愿景。二、大學生就業的現實——過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的雙重作用大學生就業的現實狀況似乎并沒有設想的好,“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最主要的是過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共同帶來的擁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勞動力的相對過剩。
美國著名教育家、教育經濟學權威亨利?萊文(Henry M.Levin)指出,過度教育包括三個含義:一為對于歷史上較高水平者而言,指受過教育者的經濟地位下降;二指受過教育者未能實現其對事業成就之期望;三指工人擁有比其工作要求較高之教育技能。[13]根據這些標準,我國高等教育的確存在“高校畢業生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高學位低就業、盲目攀升教育層次、人才消費過高”[14]等過度教育的現象。那么,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現象呢?可以說,過度教育正是上文述及的國家和個人共同構筑的大學生就業的美好愿景帶來的直接后果。由于就業主要依賴于所接受的學校教育,獲得高收入和就業崗位的唯一必要條件是擁有足夠高的教育程度,因此,人們需要更大規模的高等教育。而國家出于提高國民素質,建立人力資源大國,發展經濟,以及滿足公眾對高等教育的需要,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也需要更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其結果便是勞動力市場上擁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勞動力人數的膨脹,超出了我國經濟體系適當的就業水平所能吸收的勞動力數量。
如果說過度教育加劇了勞動力市場中大學畢業生的競爭,那么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則進一步惡化了大學生就業的現實狀況。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多林格(P.Doeringer)和皮奧里(Michael J.Piore)于20世紀70年代創立的。他們在對20世紀60年代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經濟研究中發現,很難用傳統理論解釋那些高工資群體和低工資群體及失業者之間的區別,進而提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是由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組成的。主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業和大機構中的職業崗位,雇員工資較高,福利豐厚,工作和培訓條件優越,晉升靠資歷,工作有保障;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業的職業崗位,雇員工資較低,福利較少,工作條件差,培訓和晉升機會少,易遭解雇。在解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成因時,出現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工作競爭理論”和“激進的分割理論”等流派。“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以多林格和皮奧里為代表,認為市場分割的類別與數量取決于技術要求;“工作競爭理論”以瑟羅(Thurow)和盧卡斯(Lucas)為代表,認為工資是由工作特點而不是由人的特點決定的,將勞動力市場看作是匹配接受培訓人員和不同培訓面值的市場;“激進的分割理論”以雷克(Reich M.)、戈登(DordonD.)和愛德華茲(Edwards R.)為代表,認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由資本家為實現對勞動過程的永恒控制而有意識地分化工人階級隊伍,弱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敵對情緒所導致的。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主要勞動力市場與次要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彼此間極少存在人員流動。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內部勞動力市場,雇主會對雇員進行在職培訓以使其掌握公司所需的具體工作技能,而且培訓成本主要由雇主承擔,為減少因接受過培訓的雇員辭職帶來的損失,雇主會付更高的工資。而且求職者一旦進入內部勞動力市場,就會獲得優于“外部人”的被聘用的權利、接受培訓的權利、晉升和職業發展的權利。在雇主和雇員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人員流動是內部的、縱向的,極少在內部和外部勞動力市場間流動。為降低培訓成本,保證雇員對工作的投入,雇主會利用求職者所擁有的教育文憑篩選出具有較低預期培訓成本和較好行為品質的人。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中沒有形成內部勞動力市場,人員的流動是橫向的,而且比較頻繁。此外,主要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的教育收益較高,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的教育收益較低,甚至幾乎為零。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長能夠提高主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收入,而對提高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收入則沒有作用。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基于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提出的,那么,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嗎?有研究者通過對有關數據的分析,驗證了我國存在著二元制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勞動力市場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次要勞動力市場包括:生產運輸工人、服務性工作人員、商業工作人員、農林牧漁勞動者和不便分類的其他勞動者。[15]甚至還有研究者認為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呈現出典型的兩重“二元性”特征,即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中同時體現了“內外二元性”和“城鄉二元性”,而且兩大特征之間存在著“嵌套”關系,“城鄉二元性”體現在“內外二元性”的二級部分中。“內外二元性”即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勞動力市場,前者由大中型企業、事業單位構成,后者由前二者以外的勞動力市場構成。[16]
面對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大學畢業生如何進行就業決策呢?布羅(Bulow)和桑莫斯(Summers)認為:“勞動力市場上之所以存在工資差異主要歸因于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勞動者越是關心公平的相對工資,就越有可能期望得到主要勞動力市場的高薪工作。”[17]現實中,我國大學畢業生正如他們所描述的那樣,出于對教育投資收益的期待,更加青睞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天津工業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79%的學生對畢業后的首選行業是三資企業、國企、政府機關、事業單位;91%的學生選擇畢業后在大中城市及沿海等發達地區或省內工作。[18]另一項在鹽城師范學院的調查也顯示:在就業的地理區域方面,46.5%的學生選擇“北京”和“上海”,51.6%的學生選擇“蘇南”,只有17.2%的學生選擇“蘇北”,4.5%的學生選擇“西部地區”;在就業區域的層次方面,33.8%的學生期望到“省級城市”就業,56.1%的學生期望到“地級城市”就業,6.4%的學生選擇到“小城鎮”就業,只有0.6%的學生愿意到“農村”就業。[19]
endprint
本來由于過度教育就已經加劇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壓力,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面前,這種加劇的就業壓力又被濃縮在了主要勞動力市場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之內,加之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作用,主要勞動力市場由外部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進一步惡化了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狀況。
三、結論
首先,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是由國家和個人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國家出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考慮,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沒有錯,我們不能指望通過縮減高等教育規模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否則只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無異于因噎廢食、殺雞取卵;個人追求高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也沒有錯,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教育降低大學生就業期望值的方式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畢竟作為理性經濟人,大學生對高的教育投資收益率的追求是合理的。既然二者都沒有錯,那么問題的癥結在哪里呢?恐怕經濟發展水平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不足和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難辭其咎。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其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要打破勞動力市場被分割的局面,尤其是制度性因素導致的分割局面,縮小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差距,最終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期的過程,也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需要足夠的耐心與勇氣。
其次,應當看到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實質不是就業難,而是擇業難,有研究者將其描述為“自愿性失業”。自愿性失業是大學生理性選擇的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20],不必將其視為洪水猛獸。正如國外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失業作為求職的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視為合理,特別是在勞動力市場信息匱乏的國家情況更是如此……雖然人們為了找到高收入工作而付出時間,但現實中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可能將‘不適宜的期望轉變為更加‘現實的水平上來。”[21]
最后,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治理,政府、社會、用人單位、高等學校、大學生及家庭都要做出努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將大學生就業難的責任全怪到高校的頭上,也不能將促進大學生就業的重擔全壓在高校的肩上,高校實在是承擔不起。令人欣慰的是各級政府都在出臺各種政策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那么高校是不是就沒有責任和義務呢?當然不是。但這種責任和義務不能靠將大學蛻變為職業培訓機構的方式來實現。理想的方式是:一方面,著力促進和實現高等教育多樣化,每所高校均合理定位,追求特色發展,以適應勞動力市場中對勞動力需求的多樣性;另一方面,高校要培養可被訓練的人、具有較高培訓潛質的人,而不是單純的職業教育。當然這需要內部勞動力市場、終身教育體系的完善和配合。
參考文獻:
[1][11][21]K?辛奇利夫.教育與勞動力市場[A].[美]Martin Carnoy.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Z].閔維方等譯.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3,25,27.
[2][9]王海杰.人力資本理論研究[D].廈門: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2006.20,20.
[3][美]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吳珠華等譯.北京: 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90.8-9.
[4][美]加里?S?貝克爾.人力資本[M].梁小民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1.
[5]H?M?列文.工作與教育[A].[美]Martin Carnoy.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Z].閔維方等譯.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15.
[6][7][8]W?格羅特, J?哈特戈.篩選模式和教育[A].[美]Martin Carnoy.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Z].閔維方等譯.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41, 44, 42-43.
[10][12]N?L?西克斯.教育和經濟增長[A].[美]Martin Carnoy.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Z].閔維方等譯.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43, 244.
[13][美]亨利?萊文.高科技、效益、籌資與改革——教育決策與管理中的重大問題[M].曾滿超等 譯.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5.22.
[14]趙修渝, 陳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與我國教育相對過剩[J].重慶社會科學, 2005(7): 20.
[15]郭叢斌.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在中國的驗證[J].教育與經濟, 2004(3): 9.
[16]張昭時, 錢雪亞.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兩重“二元性”:理論與現實[J].學術月刊, 2009(8): 77.
[17]G?佛雷塔.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和教育[A].[美]Martin Carnoy.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Z].閔維方等譯.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51.
[18]王宏偉.當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調查分析[J].高教論壇, 2009(8): 118.
[19]徐偉.大學生就業問題調查及解決策略[J].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8(6): 103.
[20]吳克明, 賴德勝.大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 2004(2): 41.
(責任編輯陳志萍)2014年第4期高 教 探 索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