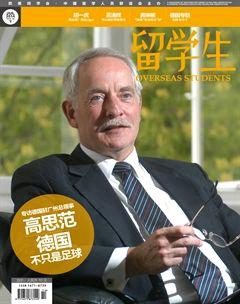柏林蒼穹下
孟捷
文章題目借用了文德斯名片《柏林蒼穹下》,把柏林當做德國的全部,因為柏林對德國電影的重要性,以及,德國電影恰好起始于柏林。德國發明家馬克思·斯科拉達諾斯基(Max Skladanowsky)在電影技術的曙光時期第一時間發明了放映機Bioscop,德國電影的第一次亮相正是在柏林蒼穹下
文章題目借用了文德斯名片《柏林蒼穹下》,把柏林當做德國的全部,因為柏林對德國電影的重要性,以及,德國電影恰好起始于柏林。
德國發明家馬克思·斯科拉達諾斯基(Max Skladanowsky)在電影技術的曙光時期第一時間發明了放映機Bioscop,德國電影的第一次亮相正是在柏林蒼穹下,1895年11月1日,斯科拉達諾斯基在柏林向付費觀眾播放了15分鐘電影,共8個短片。這比盧米埃爾兄弟同年12月28日的公開放映要早近乎兩個月,是歐洲最早的一場付費放映。但斯科拉達諾斯基專程去觀看盧米埃爾兄弟的放映會之后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放映技術比自己的優越。這大概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歷史把創始者的光環給予了盧米埃爾兄弟。緊隨其后的德國電影先鋒也是在柏林,奧斯卡·麥斯特(Oskar Messter)和馬克思·格里沃(Max Gliewe)都為德國電影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德國電影的草創階段可以按照目標對象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段電影人以吸引社會上層為目標;但上層有太多消遣,這個新玩意兒沒有讓他們著迷多久,必須尋找新客源的電影行業這時才把目光放在社會中下層身上。但我們又要再次驚嘆于德國人對文學的全民興趣,即便是給中下階層觀看的電影,往往也改編自文學名著,比如愛倫·坡的小說。
從草創一直到“一戰”前這段時期,德國電影發展很快,就從電影院這個硬件指標來看,1906年曼海姆出現了第一家專門的電影院,但不到五年時間,電影院的總數已經超過1000。電影院的飛速增加代表著飛速增加的觀眾,可德國的本土電影并沒有足夠的數量去滿足觀眾的要求,而且當時引進電影非常普遍,所以有許多意大利和丹麥電影進入德國市場。“一戰”爆發后,出現了普遍的抵制,作為敵對國的法國的電影也因此不再被引進。這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某種程度上來說傷害了德國的電影市場,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德國本土電影的一次機會。“一戰”結束后“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電影的重大發展也與此不無關系。
“一戰”最終以德國失敗告終,德國政府決定用印制紙馬克的方式支付各種債務賠償,這直接導致馬克迅速貶值,電影工業也在這里面看到了一些可供利用之處,他們以此借貸,等到需要償還的時候,馬克早已貶值不少,償還壓力大減。但總體來說,經費仍然是一個大問題,面對永遠短缺的資金,電影人想出了一個給電影藝術打上深刻烙印的應對方式:用象征性的布景替代實景。這個運動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名字:德國表現主義。
德國表現主義與電影的結合現在看來是振奮人心的藝術創舉,但在當時更多是出于囊中羞澀。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名片我們無法一一列舉,姑且以幾個最有代表性的電影為例——羅伯特·維納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20年),弗里德里希·茂瑙的《諾斯費拉圖》(NOSFERATU,1922年),弗里茨·朗的《大都會》(1927年)——以點概面回顧一下這個偉大的傳統。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可說是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代表,片中的場景非常幾何化,高度象征性,往往用圖片和光影來表現墻上和地上的物體。這樣的方式與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大相徑庭,原因不言而喻,做這樣的布景比實景拍攝或實景布景成本低得多。但這種半被迫的無奈選擇,反倒成就了電影史上的一大風潮。要說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影響,整個20世紀都不絕如縷,比如法國的讓·考克多,他的《俄爾甫斯三部曲》可以說是超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的結合,當然,更為表現主義的當屬《美女與野獸》;再比如瑞典電影大師伯格曼,他的《第七封印》把表現主義的手法用到了極致;如果不說這些“藝術電影”,說說電影工業中的大多數,我們也可以舉出美國數量極大的恐怖電影和黑色電影,這些影片,多多少少都借鑒了德國表現主義的手法,這種借鑒也不純粹是出于美學上的考慮,德國表現主義電影本來就有許多是以犯罪和恐怖為題材,后人向前人取經、致敬,也在情理之中。
茂瑙的《諾斯費拉圖》雖然現在成了一代名片,但反諷的是,當年茂瑙卻因此卷入一場官司。這部電影改編自布拉姆·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說《德庫拉》,但因為沒法獲得授權,最后電影只能更換題目和主角名字。盡管更換了名字,這部電影仍被斯托克的繼承人告上法庭,控訴侵權,最終法庭宣判制作方敗訴,必須銷毀全部拷貝。幸而此時電影已在各國上映,靠著這些海外拷貝后人方得以一睹馬克思·施萊克(這個名字就是“嚇人”的意思,光看名字就是扮演此角色的最佳人選)扮演的吸血鬼的“芳容”。這場官司也讓電影人對電影改編變得更加謹慎,要么是改編沒有版權問題的名著,比如弗里茨·朗的《尼伯龍人》,要么干脆自己編劇。
當然,劇本還有另外的特殊解決方式,《大都會》的劇本是弗里茨·朗和他夫人一起以他夫人的小說為基礎改編的,這當然就完全不會有侵權問題了,而且如何改編也變成了小夫妻自家家門內的事情。這部電影前兩年推出了修復版,又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新的觀影熱潮,一部80年前的影片能有如此魅力,正說明了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持久生命力。這部影片本身人們已經說得太多,不如說說這部影片的制作場所——“巴別山”(Babelsberg)。我們現在都知道“好萊塢”,但這一類大型電影基地并非始于“好萊塢”,而是始于德國創建于1912年的“巴別山”。巴別當然是巴別塔的那個巴別,所以這個名字本身就帶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早有電影研究者提出德國早期電影中“觀看樂趣”的追求(Schaulust),這種對觀看的視覺興趣可以說非常古老,不僅觀眾在意“觀看樂趣”,制作方也對視覺特別強調,象征著“共通語言”的巴別塔注定倒塌,但也許人類可以有另一個更穩定的共通交流方式,影像與觀看。也許這正是“巴別山”這個名字的用意。
表現主義的風潮很快就過去了,人們開始對這種夸張的手法有些厭倦了,歷史總是這樣,一個風潮之后往往是另一個相反的風潮來回應、中和其影響。表現主義之后出現的“新客體性”風潮把攝影機對準了街道和現實中的人們,但他們更注重表現靜止的物體,這和“街道電影”有很大差別,此外,也和現實主義的“勸誡片”很不一樣,“勸誡片”在我看來其實有點像中國明清的艷情小說,說是要勸人向善,道德說教,其實中間主要是為了表現另外一些東西,這些“勸誡片”充斥著聳人聽聞的主題,墮胎,賣淫,同性戀,吸毒,這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早期那些以犯罪和恐怖為主題的電影。
魏瑪共和國倒臺之后,希特勒上臺。希特勒本人非常喜歡《大都會》,戈培爾也對《大都會》贊譽有加,以至于他想請弗里茨·朗做他宣傳部的電影部門首腦。朗并未接受這份青睞,反而流亡美國,但另有一些電影人接受了與“納粹”合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女導演萊尼·里芬施塔爾(Leni Riefenstahl)。《意志的勝利》與《奧利匹亞》是她最出名的電影,前者記錄“納粹”1934年的紐倫堡大會,后者記錄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里芬施塔爾影片中體現的攝影和剪輯技術至今仍然受到觀眾和眾多電影人的推崇,但她的電影對人力物力財力的要求都非常高,如果沒有“納粹”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她也一直因此受到批評,真可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二戰后德國陷入長期分裂,東西德各自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之內拍攝影片,給自己意識形態內的觀眾。但國家的分裂和重重社會矛盾與危機對藝術家來說反而是一種痛苦的機會,德國電影的第二個高峰期“新德國電影”正是出現在6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這一時期出現了現在影迷們津津樂道的一些優秀導演,包括這篇文章標題借用片名的導演維姆·文德斯。
我們在這些導演的影片中還是看到大量怪誕的情節和場景,似乎德國電影一直深深沉浸在這一氛圍之中。兩德統一之后也出現了許多反映了“傷痕”的電影,其中最清新歡快又不失反諷和反思的,當屬《再見列寧》,這部電影也因此成了中國影迷特別追捧的一部影片。
今年年初剛剛頒布的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給了一部中國影片,刁亦男的《白日焰火》。這部懸疑犯罪片的獲獎讓人不禁感嘆,德國人對黑色的熱愛實在是經久而不衰。不過,如果人類負面的精神能量能夠在觀看這些電影時得到某種亞里士多德“凈化”式的洗滌,這類黑色影片倒也不妨來得更猛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