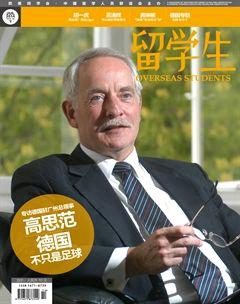總體藝術與藍
橘生
現代藝術的開端究竟可以從哪里開始?這個故事可以有很多個自圓其說的版本,從康定斯基1912年那本劃時代的著作《論藝術中的精神物》說起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康定斯基把人類的精神生活比作一座金字塔,藝術家的使命就在于用他們的作品把人們帶到這個金字塔的頂端,故而在金字塔尖端的是少量偉大的藝術家,而在頹蕩墮落的時代,精神就降低到金字塔的低端,人們只知道追求外在的成功,忽視精神的力量。但即便是在這樣的墮落時代,也會有先知一般的藝術家引領著人們向頂峰上升,這些藝術家保持著上升的態勢,即便有時候非常緩慢,看起來幾乎像是靜止。康定斯基把自己和伙伴看做這種引導性的藝術家,他在書中引用了神智學家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話,然后非常樂觀地預言,百年之后的21世紀一定是一個充滿精神追求的未來新時代。可惜,我們在百年之后的此刻無法對他的美好預言做出肯定。
但20世紀的現代藝術確實有很大一部分擁有了康定斯基的這種精神性追求,我們可以按照精神追求這個線索把整個20世紀藝術史串起來。康定斯基的這種訴求其實是對現代性虛無主義的一種回應,整個語調讓人想起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導言里的判斷:精神的目光本來在天上,希臘人花了無數精力才把這目光從天上轉移到人間,也就是蘇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但兩千年之后,精神已經深陷泥潭,目光所及之處只有地面的污泥,不再能看到天上的星辰,我們現在需要花費巨大力氣才能讓精神的目光再次向上。只不過,黑格爾那里是由哲學家來引導和改變精神的目光指向,而康定斯基這里變成了藝術家去做向導和引路人。康定斯基的這種訴求其實是對黑格爾另一個著名斷言的回應:藝術死了。在沒有上帝和信仰的時代,藝術不再關涉最重要的人類問題,現代所謂的“藝術”起始于文藝復興,可以說這樣的“藝術”從它出生的那一天就帶著死亡的烙印,它本身就起源于上帝的死亡和世界的祛魅,起源于現代性在近代的重要發端,這樣的藝術,注定會“死亡”。但康定斯基雖然同意黑格爾對時代的診斷,卻顯然不同意黑格爾對藝術的否定,在他看來,恰恰是這樣的物質和黑暗時代,才更需要藝術和藝術家對人類和精神進行指引。
康定斯基的這種想法貫穿一生,但最主要表現在他參與德國現代藝術重要流派“藍騎士”的階段(1911-1914年)。“藍騎士”和“橋”是德國現代藝術兩個最重要的流派,而且“藍騎士”的建樹應該說比“橋”更大,“橋”主要貢獻是讓人們重新發現木刻這種藝術形式,而“藍騎士”則出現了康定斯基這樣的重要藝術家,對20世紀的藝術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藍騎士”這個名字的起源,按照康定斯基自己時隔二十年之后的回憶,與康定斯基和馬克兩個人對馬和騎士的共同興趣有關,也和兩個人對藍色的共同喜好有關。當然,對康定斯基來說,藍色另有深意,他認為藍色代表著精神性,在《論藝術中的精神物》中他寫道,藍色越深,這顏色就越有力地勾起人類對永恒的欲求。這當然要結合康定斯基的顏色理論來看,在他看來,顏色會影響人,會觸及人的精神,讓人的精神產生共鳴。不同顏色會產生不同的精神共鳴,藍色會讓人產生對永恒的精神追求。
康定斯基對藍色的偏愛讓人想起德國浪漫派作家諾瓦利斯小說中著名的“藍花”,這正是美和精神的象征。不過康定斯基的藝術基本還在架上繪畫領域,而精神和人類的物質生活,明顯有更廣闊的天地,因此有另外一些藝術家以另外的方式關心人類和時代的精神狀況,這就是德國的“總體藝術”傳統。說起“總體藝術”的傳統,不能不提兩位和浪漫派有莫大關系的藝術家,一個是瓦格納,另一個是約瑟夫·博伊斯。
諸藝術的結合是德國浪漫派的一個重要議題,蒂克和諾瓦利斯都就此發表過意見。瓦格納接續了這種“諸藝術結合”的思想傳統,并將之付諸實踐。他先是在《藝術與革命》和《未來的藝術作品》中用到了“總體藝術”(Gesammtkunstwerk,瓦格納的拼法和現行拼寫方式不同)這個詞,后來他又在《歌劇與戲劇》這本書中詳細展開并發展了他的“總體藝術”理念。他認為,“總體藝術”在人類歷史中的典范是古希臘悲劇,尤其是埃斯庫洛斯的悲劇,而從歐里庇德斯開始,這種“總體藝術”就開始敗壞,藝術開始分崩離析,詩歌、音樂、舞蹈的綜合(古希臘人說到“音樂”時真正指涉的正是這種詩歌、音樂和舞蹈的綜合)開始瓦解。瓦格納想要重建一種新的“總體藝術”,他想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歌劇”,不像當時時興的意大利歌劇那樣只注重表演性的花腔和炫技,而是讓音樂為戲劇服務,讓情節為理念服務。
瓦格納靠著他的《尼伯龍人的指環》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全靠君王的支持,沒有專門建造的拜洛伊特劇場,恐怕瓦格納的歌劇也沒法真正按照他的理念和構想去實現。但他的“總體藝術”理念還是局限在“藝術作品”之內,而博伊斯的“總體藝術”則再次解放并擴大了“藝術”和“藝術作品”的概念。
博伊斯對“總體藝術”的癡迷也與他對諾瓦利斯等浪漫派作家的喜愛密切相關。他的“總體藝術”不再是追求某個具體的作品,他完全革新了“藝術作品”的概念,在他看來,整個人類的行為的結果是一個巨大的藝術作品,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在為這個作品添磚加瓦,都在參與這個作品的形成。也正是基于這個獨特的“藝術作品”理念,他借用了諾瓦利斯的名言:每個人都是一個藝術家。這句話我們現在經常聽到,這是在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不只是一個孤零零的個體,我們每個人都屬于更大的整體,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為人類歷史或人類文明這個巨大的藝術品添上一筆。
博伊斯的這個觀念與德國思想家魯道爾夫·史坦納的思想有很大關系,史坦納認為人類社會可以分成三個領域,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并非互不相關,在比較良好的情況下,三個領域可以相互影響,相互“更正”。博伊斯的藝術理念其實是要借用藝術來影響經濟和政治層面的東西,用藝術來改變社會中的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
博伊斯最有名的作品是“7000棵橡樹”。1982年的卡塞爾文獻展(當代德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展之一)邀請博伊斯創作一個作品,博伊斯選擇施放7000塊巨大的黑色玄武巖,然后逐漸在這些玄武巖旁邊植樹,每塊石頭旁邊種上一棵。開始的時候,他的計劃遭受了政治層面的阻礙,經濟上,他的計劃也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后來這些問題逐漸解決,人們也開始在審美上接受他對當地環境的改變。
博伊斯把社會整體看做是藝術作品,這也就是他著名的“社會雕塑”觀念。“社會”本身成為雕刻的對象,而且不僅僅是藝術家去雕刻它,每個身處社會之中的人也都參與到這一雕刻行為中,這樣的理念可以說和博伊斯推崇的席勒的“審美教育”理念頗為相近,但博伊斯的觀念自有他獨特之處,可以說,博伊斯的觀念又在某種程度回到了康德。歷史不再僅僅是歷史的狡計,歷史和社會也是人類自身對自身的構造和完成。但博伊斯畢竟還是一個藝術家,他雖然沒有像康定斯基那樣明說,但他那樣的藝術家,明顯是在引導更普通的“藝術家”,也就是,社會中的每個人。
這樣的自我期許并不讓人反感,相反,藝術也正是靠了這樣的藝術家,才不僅僅是資本與市場的玩物,藝術家也才真的成為同類的向導,向時代和世人證明,藝術并未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