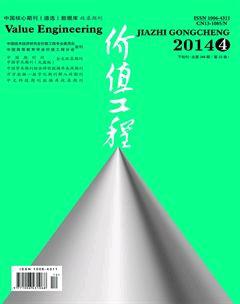基于收入差異下的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研究
關佩儀GUAN Pei-yi;馮劍鋒FENG Jian-feng
(①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廣州510641;②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300071)
0 引言
中國從2000年開始逐步進入了人口老齡化國家,過快的老年化現象導致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支付壓力。因此我國在2004年4月出臺了《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初步確立了企業年金作為養老保險第二支柱的基本框架,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企業年金的發展狀況并不理想。由于目前我國實行“一刀切”的稅惠模式,收入水平較低的企業員工根本無法吸引到企業年金計劃當中。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后工業化國家企業年金制度的建立及其發展均與這些國家采取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政策密切相關。因此,本文主要從收入差異的角度出發,在現行個稅征收標準的基礎上討論不同稅收征收模式對參與年金計劃的企業員工所帶來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為未來中國企業年金的發展提供新的政策與建議。
1 我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模式
一般來說,政府對企業年金的稅收政策主要集中在三大階段:繳費階段、投資階段和領取階段。三個階段對應不同的納稅環節,一般的做法是根據稅收是否征收,分為征稅(T)和免稅(E)兩種,按照不同的階段是否采取優惠減免計劃,可細分成8種稅收優惠檔次,分別為熟知的EEE、EET、ETE、ETT、TEE、TTE、TET 和 TTT 模式。而我國主要采用TTE模式。
2 我國企業年金現狀及分析
從現階段來看,我國企業年金的發展不容樂觀。企業年金資產占GDP比重僅為0.76%;而全球企業年金約占全球GDP的38%,即使“金磚四國”中,中國企業年金占GDP比重也是最低的,巴西、印度、俄羅斯這3個國家企業年金占GDP比重分別達到17%、5%、2%。而從企業員工參與的覆蓋率看,中國的企業年金計劃參與率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企業年金參與率僅為2.1%,而英國為8.7%、法國為10.6%、加拿大為39.4%、美國為46%①。
2.1 從人力資源角度分析我國企業年金的現狀 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其本身是一個非競爭性的群體,他們在就業市場上處于壟斷位置,具有較強的薪酬議價能力,因此如果以企業年金形式發放和以直接薪酬發放其區別并不大,只要企業年金的投資報酬高于其持有現金時所獲得利率,那么高收入群體就會愿意參加與到企業年金計劃中。從企業管理層面上來說,高收入群體其在企業中一般處于較高的管理部門或者掌握了重要的企業資源和技術,企業更愿意留住這些人員,以免出現企業競爭力下降的情況。而企業年金作為企業管理中的一項重要激勵機制,它比股權激勵和經理人持股或技術入股模式更有優勢,因為后者需要分攤企業未來的盈利,無形中加大了企業的成本,而企業年金具有時間長而且成本較低等特點,給員工帶來的福利更為實際,讓員工更能感受到企業的關懷,而并非是單純像股權激勵那樣帶有明顯的經濟利益行為,于是從企業角度上來說,為了留住這些優秀的人員,企業會與企業員工簽訂企業年金計劃。
因此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即使稅負再高,企業和員工都愿意參加到企業年金的計劃當中,但是這里必須注意的是高收入群體的比例占整個勞動市場的比例是十分的少。
對于中低收入的員工而言,他們的情況就跟高收入群體存在很大的差異,由于企業處于買方壟斷位置,而中低收入群體往往處于一個競爭性的勞動市場,對于薪酬的議價能力幾乎沒有,所以員工在參與企業年金的積極性就會有所降低。而對于管理層而言,由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員工替代性較高而且流動頻繁,企業并不愿意去選擇為員工開展企業年金計劃。所以在現行模式下很難刺激到中低收入員工參與到年金計劃當中,但這個部分的比例卻占了勞動市場上大多數。所以這樣一來,企業年金的參與者往往只是高收入群體而沒有考慮到中低收入者,參與年金的覆蓋面就會大大降低。
2.2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現行的企業年金TTE模式 以下部分將進一步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為何在現行的TTE模式下為何無法吸引中低收入水平的員工參與到年金計劃中,而在討論前本文進行適當的假設:
①由于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模式中,只有繳費和領取階段涉及到個人所得稅②的征收,因此在以下討論中不考慮投資階段,并假設企業員工的壽命分為t和t+1兩期,t期為繳費階段;t+1期為領取階段;②企業員工的收入M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原有的基本可支配收入G,另一部分是額外的薪酬P,P這個部分的薪酬可以以直接薪酬、福利待遇進行發放,同時也可以將其支付于企業年金;③假設在繳費階段不參加企業年金計劃,采取以直接薪酬發放時,其對應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t1,而參加企業年金計劃時對應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t2,由于我國暫時是以年金收入單獨計費為標準,即年金收入繳費部分不需要并入原有工資、福利等項目中,可單獨計費,所以在原有收入的基礎上,直接以薪酬發放與參加企業年金的計劃存在計稅檔次的差別,實行累進制后,t1≥t2;④假設企業年金的整體報酬率為r,而員工不進行企業年金時其投資報酬為i,并假定r≥i。
假設員工選擇當期以直接薪酬P發放時,則當期收入為 N=G+(1-t1)P=G+kP,到期后的收入為 A=(G+(1-t1)P)(1+i);而如果員工選擇當期以P參加企業年金計劃,則當期收入就變為N=G,到期后收入為B=[G+(1-t2)P](1+r)-P(1+r)t3=[G+(1-t2-t3)]P(1+r);當實施TTE模式時:B=[(G+(1-t2))P](1+r)。
從圖1可以看到,如果要實現參與企業年金部分比直接支付薪酬要好時,A點必須要遠遠高于B點,這時需要r>>i,t1>>t2,即享受企業年金過程中所享受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要低于在以直接薪酬計算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這時可以從圖1得出:BN為參與企業年金計劃后的預算線,AM為不參與企業年金計劃的預算線,E和F分別為兩種情況下滿足帕累托最優條件的最優點,很明顯E點比F點要好,說明參與企業年金計劃優于不參與企業年金計,但這里需要t1>>t2,這個條件很明顯對收入越高的群體越有利,因為按照這種企業年金與原來薪金分開的計稅基礎,收入越高的群體,其t1會遠遠高于t2,所以在現行的TTE模式下一般對于高收入群體來說,他們往往會有很大的動力參加到企業年金中。
但是對于中低收入群體來說t1不可能太高,當t1與t2相差不大時,A與B之間的差距過小就會很容易掉入所謂的“稅收優惠陷阱”當中,其結果是導致大部分的中低收入者放棄參加企業年金計劃。具體看圖2:很明顯從這里可以看到:雖然B點已經在A點的上方,但是由于稅收優惠并不能帶來較高的效用水平,單靠投資回報率并不能有效地吸引中低收入的員工參與到企業年金計劃當中。因此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高收入個體在現行的TTE模式下能得到較高的效用收益,其參與企業年金計劃的積極性要高于中低收入者;而對于中低收入者則剛好相反,由于享受稅收優惠的效益不大,中低收入者往往會選擇放棄參加企業年金計劃。
由此可以看到:現行的TTE模式雖然在當期能有效地控制稅收成本支出,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收入水平的差異,所以導致了中低收入的企業員工并不愿意參加。這正是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參與企業年金計劃的只有是高收入群體,而占勞動市場主體部分的中低收入群體無法吸引到企業年金計劃當中。所以對于政府而言,要想廣泛地吸引企業員工參與到企業年金計劃當中必須要從模式選擇上注重收入群體的差異,實施有效的分類征收措施。

圖2 中低收入者的稅收優惠陷阱
3 企業年金政策建議
針對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結合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現行企業年金制度只有實施比例限制措施,卻沒有年度最大繳費額度的“封頂”的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給高收入群體提供了轉移收入的機會。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針對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限制高收入人士進行超額的企業年金支付,或者實施超額部分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②政府對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模式存在部門之間的矛盾,財政稅收部門一直堅持實施前端征稅(TTE模式),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相關部門則一直提倡實施后端征稅(ETT模式)。而本文的研究表明這種“一刀切”的模式并不有利于解決當前企業年金發展困難的難題,政府應立足于地區與行業收入水平的差異,對中小企業低收入人士實施ETT模式同時加大對企業推廣和宣傳力度。而對高收入群體則實施TTE模式,并加大監督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程度和懲罰力度。
注釋:
①資料來源: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9/26/c_123762240.htm).
②傅安平、劉云龍(2004)的研究表明在效率工資模型下,員工參與企業年金計劃不受企業所得稅的影響.具體參考《企業年金-模式探索與國際比較》第115-118頁.
[1]陳佳,朱銘來.中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比較與選擇[J].當代經濟,2007(4):29-34.
[2]傅安平,劉云龍.企業年金-模式探索與國際比較[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3]汪晶晶.中國企業年金EET稅收模式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金融學,2012.
[4]張蕾.稅收優惠經濟成本分析[D].廣州:中國海洋大學金融學,2011.
[5]張彤.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財政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