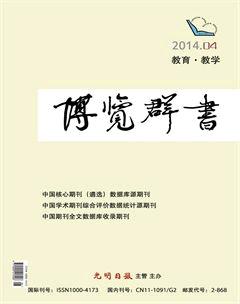漂浮的“風(fēng)”
段健
摘 要:人們常說電影是光影的藝術(shù),以光影的變化來(lái)表現(xiàn)時(shí)間的流逝。傳統(tǒng)的電影中,在對(duì)光影的把握上,往往將時(shí)間與空間嚴(yán)格區(qū)分,也就是在什么時(shí)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導(dǎo)致了什么結(jié)果。而杜可風(fē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傳遞出一種打破時(shí)空的光影觀念,在展示某一主題的時(shí)候,杜可風(fēng)通過光影把故事的時(shí)間、空間切割成零星碎片,展現(xiàn)出特定的某種狀態(tài)和氛圍,碎片般的段落正好配合主人公所處的境遇,使整部影片呈現(xiàn)出虛幻之感。
關(guān)鍵詞:杜可風(fēng);光影;鏡頭畫面
攝影師對(duì)光影的追求、摸索是永無(wú)止境的。光,不僅是電影獲得影像的必要物質(zhì)條件,更是構(gòu)成電影作品的重要造型因素,是塑造電影形象的基礎(chǔ)。同其它藝術(shù)相比較,光在電影藝術(shù)中占據(jù)著尤為重要的地位。光具備一個(gè)良好的造型功能是對(duì)時(shí)間和空間的描繪,它側(cè)重藝術(shù)的真實(shí),側(cè)重作者意識(shí)的主觀體現(xiàn),要求光線效果必須是在更深一層意義上對(duì)時(shí)間的表現(xiàn)。
杜可風(fēng)(Christopher Doyle)是澳大利亞籍華裔世界知名攝影師,他的藝術(shù)人生是伴著香港”后新浪潮”及臺(tái)灣新電影運(yùn)動(dòng)一起成長(zhǎng)的。多數(shù)從杜可風(fēng)的世界里走出來(lái)的人,倘若循著原路返回自己的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他拍攝的大量影片中,對(duì)光線充滿了宗教般的迷戀和虔誠(chéng),法國(guó)影評(píng)界高度評(píng)價(jià)王家衛(wèi)和杜可風(fēng),稱他們是開創(chuàng)現(xiàn)代中國(guó)電影視覺與語(yǔ)法的大師。他們共同的創(chuàng)作不僅提升了香港電影的視覺品位,而且極大的豐富了電影語(yǔ)言的表現(xiàn)力。
杜可風(fēng)的動(dòng)態(tài)鏡頭中,作品多表現(xiàn)出迷離、頹廢的光影效果。在《東邪西毒》中的整體基調(diào)是由黃藍(lán)光構(gòu)成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開場(chǎng)張國(guó)榮的打斗鏡頭中,昏黃的場(chǎng)景光加上跳躍的火光輔以搖移不停的鏡頭,使整個(gè)搏斗場(chǎng)面異常混亂與激烈,雖未曾見真正的一招一式,但月光穿透茅草房所形成的黃藍(lán)光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使得整個(gè)畫面顯的異常犀利與躁動(dòng),配合人物表情的特寫,一種生死垂危感迎面朝觀眾撲來(lái)。
而在杜可風(fēng)鏡頭定格的時(shí)候,他的光影同樣營(yíng)造出一種夢(mèng)境感,當(dāng)然在他的攝影中鏡頭不動(dòng)極其之少,時(shí)間也極其之短。其中有一個(gè)片段描述黃藥師(梁家輝飾)騎著馬去看桃花(劉嘉玲飾)的時(shí)候,鏡頭給出的是桃花頭部特寫和虛幻的背景,而片中的心理狀態(tài)就是通過光影來(lái)展現(xiàn)的,整個(gè)畫面以藍(lán)光為主,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夢(mèng)境之感,而黃光透過樹林在她臉上閃爍,既加強(qiáng)了畫面的動(dòng)態(tài)感和旋律感,也逐一呈現(xiàn)出桃花的心理狀態(tài):從驚訝、欣喜到茫然、失望的整個(gè)心態(tài)的展露過程。在《墮落天使》中他大膽的運(yùn)用了彩色和黑白的調(diào)度,使整個(gè)畫面可以脫離影片的故事表象和人物表演來(lái)展現(xiàn)。例如金城武和楊采妮在餐廳打架逃出來(lái)之后,畫面馬上以黑白系列呈現(xiàn),鏡頭是定格的,而畫面上背景人物移動(dòng)造成的光影班駁感和鏡頭的虛實(shí)交替,營(yíng)造出詭異和迷離之感,而此時(shí)楊采妮因?yàn)槭俣斐傻男撵`創(chuàng)傷,和金城武因?yàn)槌鯌俣纬傻拿篮妹噪x幻想,在這亦真亦幻的光影中表達(dá)的淋漓盡致,影片中也大量使用了表現(xiàn)主義的視覺風(fēng)格,畫面多次呈現(xiàn)黑色電影畫面的視覺特征。如在片中通往殺手黎明家的地鐵站里,攝影機(jī)以廣角鏡頭和低機(jī)位仰拍,強(qiáng)化了屋頂上的日光燈由于曝光過度形成的光暈,并隨著攝影機(jī)的移動(dòng)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輻射感和流動(dòng)感。在《春光乍洩》中,光線造型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對(duì)時(shí)間的表現(xiàn)。梁朝偉住所光線的處理故意”沒有時(shí)間”,有意的讓它”無(wú)始無(wú)終”。日或夜都不重要,影片里無(wú)關(guān)日夜的時(shí)間性。杜可風(fēng)在影片中賦予環(huán)境一種特定的時(shí)間,這種時(shí)間是劇中人物的,是主觀的。故事的發(fā)生地點(diǎn)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推到了后景,僅作為一個(gè)元素存在,同時(shí)地理上的時(shí)間也被推到了后景。梁朝偉的住所是影片重要的場(chǎng)景之一,杜可風(fēng)通過燈光照明處理,運(yùn)用色光和區(qū)域打光的方法,構(gòu)成畫面大的明暗反差和色反差,從而使狹長(zhǎng)、封閉的空間總是充滿了燈光,當(dāng)然這里的時(shí)間不與外界發(fā)生交流,空間被燈光支離破碎分解著,隱喻的體現(xiàn)了存在于時(shí)空之外主人公梁朝偉、張國(guó)榮的心靈世界無(wú)法溝通。他們的敏感脆弱,也讓這個(gè)房間成為構(gòu)架他們內(nèi)心狀態(tài)的重要依托。接著在《花樣年華》里,他對(duì)于光影的把握更加純熟了,收斂了放肆的靈感和炫耀的企圖,完全讓光影為人物和情節(jié)服務(wù),出現(xiàn)了一種更平穩(wěn)的美感。在電影《花樣年華》的許多鏡頭里,我們可以看到,畫面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是黑暗的,只有一個(gè)光源照亮了一小塊地方,而人物就在這小塊的亮處活動(dòng),或站,或坐,或者從黑暗中來(lái),又走進(jìn)黑暗里去。這種對(duì)于黑暗的使用,對(duì)于空間的省略,明暗的對(duì)比,使得畫面出現(xiàn)了一種奇特的效果,讓人聯(lián)想起倫勃朗的版畫,他們處理光影的風(fēng)格幾乎是一致的。如當(dāng)張曼玉和梁朝偉擦肩走過面攤前的石板階梯,鏡頭移到路邊那盞昏暗的路燈上。整個(gè)畫面都是黑暗,只有那么一點(diǎn)不清晰的黃光亮著——這個(gè)畫面停了很長(zhǎng)很長(zhǎng)時(shí)間,長(zhǎng)的讓每個(gè)人都覺得這黑暗在醞釀著什么,然后,突然就下雨了。在黃色的逆光照耀下,雨點(diǎn)顯的格外的大,格外的晶瑩。這段鏡頭當(dāng)然有著導(dǎo)演想表達(dá)的意境,但這意境就是因?yàn)楣庥暗募尤耄棚@得那么強(qiáng)烈,動(dòng)人心弦。在電影《2046》中光影的隱喻手法更加常用了,如王菲日復(fù)一日的在陽(yáng)臺(tái)上背日語(yǔ)的情景,鏡頭通過仰拍大半的天空留黑和極眩的燈光的拍攝,透過傍晚的氣息營(yíng)造了一種無(wú)奈與探尋之感,而正好也給王菲這個(gè)角色鋪墊了一個(gè)整體的精神寄托。《2046》的主色調(diào)是藍(lán)色,似乎在《花樣年華》中紅色的東西幾乎都在《2046》中變成了藍(lán)色。紅色代表激情,而藍(lán)色代表憂郁,從而使故事穿插和人物透過光影也恍若隔世。所以在他的攝影中光影是他敘事流程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人物環(huán)境的重要載體。
杜可風(fēng)的攝影是關(guān)注生活的,是尊重生命的。但每每曲終人散,它始終也沒有給出對(duì)“自我意義”問題的解答。也許它只是想向我們展示一種“永恒的人性困境”,而不愿對(duì)具體的人事妄加褒貶。這“不下定論”的姿態(tài),拒絕了斬釘截鐵的答復(fù),與此同時(shí),另一個(gè)更為意味深長(zhǎng)的啟示逐漸浮出水面——我想,每個(gè)人的價(jià)值取向,是無(wú)從對(duì)他人解釋清楚的。也許是不切實(shí)際的理想主義;也許眼高手低沒有能力實(shí)現(xiàn);也許只是自欺欺人的堂皇藉口;亦或根本只是迷戀虛無(wú)——但是每個(gè)人獨(dú)特的靈魂,都應(yīng)該得到尊重——尤其是對(duì)他自己的尊重。
參考文獻(xiàn):
[1]宮林, 《電影色彩的意義》[J], 北京電影學(xué)報(bào),1999年
[2]張健, 《(聲光電影里的社會(huì)與人生)影視藝術(shù)論》[M],中國(guó)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