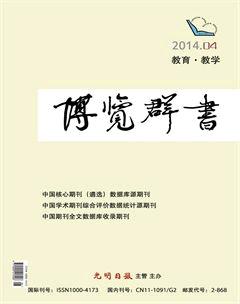濃厚的雜文情結
劉曉霞
摘 要:牧惠一生與雜文有著深厚的情結。本文旨在梳理牧惠雜文創作歷程中,挖掘其雜文創作特點和思想內容。
關鍵詞:雜文情結;牧惠;雜文思想
1942年春,僅僅十四歲的牧惠,就開始發表小說、新詩、評論及帶有雜文味的短文。自此之后,牧惠就與文學,尤其是雜文,結下了深厚的情結。縱觀其雜文創作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學步階段(40年代)。中學時期,十四歲左右,牧惠就在報刊上發表了文章;但是,由于閱歷少,積累少,所以此時期他的雜文便帶有“為寫而寫的味道。”⑴
第二,追跑階段(50-60年代)。從入游擊區到解放后這段時間,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牧惠無法把主要時間和精力用于寫作,直到1958年,他才得以把主要精力轉向創作,并且逐漸以雜文為主攻方向。此時,他的思想較之前成熟了一些。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和追求總是不可避免地帶有他那個時代的特色。對此,牧惠在他的《學寫雜文的三個階段》一文里說:“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特點是思想比較單純因而也可以說比較幼稚,對黨的文件的正確性堅信不疑,因而也可以說帶有盲從因素。”⑵牧惠二三十歲時,寫于五六十年代的雜文,大都是闡釋黨的政策和宣傳極左思想的遵命之作。對于這些速朽之作,他后來流露了反悔之情,即“要做一個雜文家,他首先得有正確的思想,得有自己的腦子。而我當時的弱點恰在于自己沒有或者說很少有自己的腦子,輕易地相信了一些同自己目睹的實際情況不符,同人民群眾利益相悖的錯誤思想。”⑶當然,在這個歷史階段,牧惠并沒有完全失去自我的思維和聲音。他的《夜談晨錄》就抨擊了當時盛行的那些歪曲別人言論而硬扣上帽子的惡劣風氣;他的《屈萊頓和馮道》揭露了那些見風使舵的人的丑惡行徑。這類文章雖只占他此時期雜文創作的百分之八九,但在那個“天啞地聾”、“十億人都失去腦袋”的年代,有自己的想法,并敢發出自己聲音的人,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發展階段(七○年代末至八○末)。“文革”結束之后,很多作家都相繼獲得了“解放”和自由,并紛紛投入到“新時期文學”建設中。牧惠在老上級和同志們的鼓勵下,又寫起了雜文,并且越寫越猛。自1979年到1989年,他寫了八十萬多字的雜文,主題是反封建愚昧和反腐敗。對“文革”的反思,使他認識到,封建愚昧是阻礙歷史前進的主要惰力之一,于是,他把反對封建愚昧作為主要斗爭目標呈現在雜文里。對于越來越嚴重的腐敗問題,有些雜文家都不想再寫了,因為他們覺得寫了也是白寫,所以干脆就不寫了;而牧惠卻依舊堅持寫此類雜文。⑹八○年代,是新時期雜文的繁榮與發展階段,也是牧惠雜文事業的上升期。他的雜文集《湖濱拾翠》、《碰壁與碰碰壁》、《且閑齋閑話》、《當代雜文選粹·牧惠之卷》等相繼出版。其中,《湖濱拾翠》還榮獲了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首屆優秀雜文(集)獎。牧惠勤奮耕耘在新時期的雜文園地里,以創作實績確立了他在當代雜文界的重要地位。他擁有豐富的史學知識和敏銳的眼光,這在他的雜文中有充分的表現。他總是透過重重歷史迷霧看到社會的本質;看到封建主義的根深蒂固;看到傳統文化的劣根性;看到中國歷史里沒有人的位置。他善于從紛繁的史料里攫取雜文題材,在古與今的縱深對比中,讓歷史成為現實的鏡子。關于歷史和現實的關系,他在《關于<華表的滄桑>》里有這樣的認識:“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歷史,這是一面多么寶貴的鏡子!當我們把現實和歷史兩相對照,又會產生多么強烈的戲劇效果!”牧惠的《華表的滄桑》等雜文,被稱為“史鑒體”雜文,深得“春秋筆法”的精髓。這類“史鑒體”雜文,在牧惠此階段的雜文創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追究其中的緣由,大概有三點:首先是因為牧惠涉獵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并有深厚的歷史積淀,所以可以信手拈來,為其所用。或者說這種曲筆是他的一種雜文藝術;其次是因為中國素有以文字治罪的傳統,再加上牧惠因為雜文而在“文革”中挨批的親身經歷,讓他心有余悸。所以熾烈的感情常常被內斂在對歷史的評論中。當然,對“文革”這段歷史,牧惠還是難抑其憤怒之情和批判的鋒芒;但卻多停留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批判上;而少理性的反思與深刻的認識。這或許對一個“文革”受難的親歷者來說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馮英子所說“人的感情,其實是同他的經歷、遭遇聯在一起的。比方說十年動亂時期,被折磨的人當然不會對‘文革有什么好印象。”⑺最后是因為時代環境使然。生活在體制之內的人不免受一些約束;所以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總是相對的,而不是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就像生活在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要受重力的影響一樣。任何時代都不會讓老百姓有絕對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正如牧惠在《新時期的雜文》中所說:“‘文革之后,講真話也并不那么容易”。或許是由于這些緣故,所以牧惠此時期的雜文給人的感覺是如骨梗在喉,知有不言,意有不達之處,讀來無痛快淋漓之感。這也是整個新時期雜文的不足之處。
第四,飛躍階段(1990-2004年)。九○年代以后,牧惠雜文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兩千年之后,更是有了一個飛躍的高度:思想上有深度,藝術上有提升。這是他多年積累的必然結果;也是他退休后獲得更大心理自由的表現。對此時期的心理狀態,他的《難得瀟灑編后記》一文中有過表述,即“開放改革以來,特別是‘告老還鄉之后,可以讀點自己喜歡讀的書,講點自己想講的話,寫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干點自己想干的事。”除此之外,比較寬松的文學環境也是原因之一。九○年代以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漸漸疏遠,而文學與市場的關系卻走近了。洪子誠說,九○年代后,意識形態對文學的監管方式是“采用更具彈性,并更多運用經濟集團活動的方式,來影響、規范文學的取向。”⑻在以上種種因素的影響下,牧惠此時期的雜文呈現如下特點:題材廣泛,既有敏銳的社會批評,也有深刻的文明批評,還有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寫得大膽、真誠、尖銳、深刻,改變了八○年代那種簡單批判的作風,既指出了病因,也開了治療藥方。或者說批判與反思更理性、更深刻了,更加重視雜文的文學性。總而言之,牧惠這個時期的雜文,讀來比較酣暢淋漓。這就是他飛躍階段的雜文風貌。
梳理牧惠雜文創作歷程,可知他的一生與雜文有著不解之緣。這不解之緣,讓他與雜文結下了深厚的情結,并贏得了當之無愧的雜文家稱號。
注釋:
[1][2][3]牧惠.學寫雜文的三個階段.見.趙元惠編.雜文創作百家談.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頁138,頁139.
[4]牧惠.風中的眼睛.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326.
[5]牧惠.滄海遺珠.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238.
[6]牧惠.風中的眼睛.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275.
[7]朱鐵志.中國新文學大系·雜文卷(1976-2000).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頁52.
[8]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32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