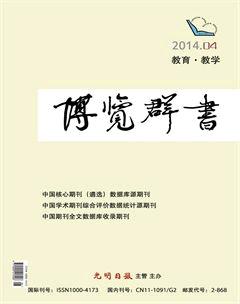論《穆斯林的葬禮》中作為隱喻符號的月意象
竇琪玥
摘 要:霍達(dá)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善用隱喻的藝術(shù)手法。書中的月意象作為獨(dú)特的隱喻符號,在結(jié)構(gòu)全書,暗示并升華主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shí),月意象的使用是作家個(gè)性和民族共性的體現(xiàn)。
關(guān)鍵詞:《穆斯林的葬禮》;月意象;隱喻符號
黑格爾探討過隱喻,“把意識中顯得很清楚的意義表現(xiàn)于一種相關(guān)的外在事物的形象,用不著讓人猜測,只是通過譬喻,使所表現(xiàn)的意義更明晰,使人立即認(rèn)識到它的真相。”(《美學(xué)》)作者使用隱喻符號造成文本與意義之間的審美距離,讀者通過聯(lián)想與想象的方式逐漸使這段距離彌合,文本背后潛藏的深意隨之顯現(xiàn),美感便產(chǎn)生了。
在《穆斯林的葬禮》一書中,月意象的隱喻使用既源于對回族文化傳統(tǒng)的傳承,又源于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借鑒。意象的多義性與朦朧性使得讀者不斷拉近其與文本的審美距離,在思索中體味作家深沉的情感。
一、月意象呈現(xiàn)的時(shí)空意識
《穆斯林的葬禮》中的月意象,是中國人長期以來審美經(jīng)驗(yàn)積淀的產(chǎn)物,以其獨(dú)特的隱喻符號作用貫穿了文本的始終,呈現(xiàn)出一種獨(dú)特的時(shí)空意識。
《穆斯林的葬禮》對月意象的使用呈現(xiàn)出一種時(shí)間意識。序曲“月夢”,講到梁冰玉長滯國外,思女心切,夢中念月,故而回鄉(xiāng)探望,卻發(fā)現(xiàn)物是人非,她在門外徘徊,恐懼又充滿希望。尾聲“月魂”接續(xù)序曲,照應(yīng)序曲,終于敲響大門的梁冰玉在圓夢后破夢,新月早已化作一屢月魂而去。十五章的正文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的變化與轉(zhuǎn)折,卻只是夢與醒之間一個(gè)渺小的縮影,人生的無常感融合在了時(shí)間的回環(huán)感中。月還是別時(shí)之月,人卻已成月之魂,時(shí)間的間隔被磨滅了。
月意象的使用呈現(xiàn)出一種空間意識,使讀者建立起空間與意象的關(guān)聯(lián)。六十年后的故事雖然發(fā)生在承載玉文化的“博雅”宅,但玉都被塵封在了密室里,它們喪失了作為敘事主體的地位,新月成為了新的主體,此時(shí)發(fā)生的故事,都是月的故事。
二、從女性意識角度解析月意象表達(dá)的深刻內(nèi)蘊(yùn)
在《穆斯林的葬禮》中,月意象以其復(fù)雜的指向,為多元化題旨的逐步求解提供一種可能性。
月意象以其純潔、自由、陰柔與美麗,象征著女性,于是“月”的變遷代表女性命運(yùn)的沉浮。“月清”、“月明”、“月情”、“月戀”貫穿起了主人公美好的經(jīng)歷,韓新月成功入學(xué),在學(xué)校收獲了學(xué)業(yè)的成功與友情的溫暖,她在病中不間斷學(xué)業(yè),收獲了甜蜜的愛情。而“月冷”、“月晦”、“月劫”、“月落”、“月魂”象征著不幸與死亡,貫穿了梁冰玉與韓子奇愛情的悲劇,韓新月生命與愛情的悲劇。月的狀態(tài)就是女性命運(yùn)的狀態(tài)。月戀代表女性的愛戀,在病房中,新月與楚雁潮朦朧的師生戀終于明朗起來;月落代表女性的離愁,新月得知親母身份卻無法與其相見,兩地人都在傷感離別。月魂代表女性的死亡,新月死了,給活著的人留下無盡的傷痛。月的陰晴圓缺與女性命運(yùn)的起落沉浮具有了一種同構(gòu)性。
三、從命名符號角度解析月意象表達(dá)的深刻內(nèi)蘊(yùn)
“新月”的命名有相反相成的兩重含義:一是希望,二是殘缺。
由于進(jìn)入齋月和開齋節(jié)要進(jìn)行望月活動(dòng),月牙便成了伊斯蘭教建筑的標(biāo)志之一。新月象征著穆斯林文化的延續(xù)、變革與新生。尾聲“月魂”提到莊子的《起死》,在艱難而可貴的人生中,莊子要喚醒骷髏“沉睡的人生”,讓他“重新生活一次”,這也昭示著回民精神的死而復(fù)生。
殘缺是新月的另一個(gè)特性,“我的生日,月亮是圓的;你的生日,月亮是彎的。”作家借天星之口,昭告韓新月出生的非法性,新月的隕落,一是先天的悲劇,即出生不合于伊斯蘭教教規(guī)的悲劇,這象征著伊斯蘭民族內(nèi)質(zhì)的流失;二是后天的悲劇,即回族文化沒有和漢文化結(jié)合以延續(xù)自身生命的悲劇。新月作為一個(gè)全新的穆斯林,喪失了伊斯蘭教的精神與信仰,其作為自我文化載體的肉體便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于是,整個(gè)穆斯林文化隨新月的逝去而舉行著全民的葬禮,表達(dá)著全民的哀悼。同時(shí),在現(xiàn)代社會,穆斯林文化必須融入現(xiàn)代元素,才能延續(xù)其自身生存。而由于代表穆斯林保守勢力的梁君璧的阻撓,韓新月被迫與代表漢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的楚雁潮分開,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四、顯現(xiàn)民族共性與作家個(gè)性的月意象
《穆斯林的葬禮》中的月意象并非孤立存在于此書中。作家對意象的選取既能體現(xiàn)她獨(dú)特的民族身份,又能體現(xiàn)作家個(gè)人對漢文化的借鑒與學(xué)習(xí)。
回族作家馬麗蓉說:“‘月亮的色、形、質(zhì),分別負(fù)載了中國回民尚潔、喜白、思鄉(xiāng)、念親與堅(jiān)韌內(nèi)隱等獨(dú)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月亮意象便成為回民心象的最恰切的載體。”(《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伊斯蘭文化》)因此,“對月的吟詠,不僅傳達(dá)出回回民族歷史的苦難肅穆,表現(xiàn)出回族信徒信仰的虔誠篤敬,而且還將其作為人性高潔清透的象征。”(《當(dāng)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評析》)
回族文人對月的吟詠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唐代,李珣就用月寄情。詩人們在關(guān)注月的不同樣態(tài),他們寫涼月、明月、落月、新月、昏月,《穆斯林的葬禮》中有“月冷”、“月明”“月落”、“新月”、“月晦”。月的不同樣態(tài)蘊(yùn)含著古代回族詩人的不同情感,也能對應(yīng)《穆斯林的葬禮》中不同的象征意味。當(dāng)代回族作家古原、查舜、了一容用月意象襯托親情、心靈的高貴,表現(xiàn)堅(jiān)韌挺拔的回民精神。
霍達(dá)喜月,也喜寫月。她在《未穿的紅嫁衣》的第九章引用了《水調(diào)歌頭》中的“月有陰晴圓缺”作為題名,以“月”象征女性命運(yùn)。郁瑯?gòu)衷谝惶熘校?jīng)歷了從準(zhǔn)備出嫁到失去心智的大起大落。《秦臺夜月》在有月的夜晚展開回憶,全文籠罩著憂傷,卻又充滿希望。月是可愛的、詩性的,因此嚴(yán)歌苓是“美洲月”,女兒是“明月在天”,李白是“江上月魂”。
五、小結(jié)
從結(jié)構(gòu)分析,月意象用獨(dú)特的時(shí)間敘事鏈表達(dá)了作家的空間意識。從內(nèi)容分析,在表層意蘊(yùn)上,《穆斯林的葬禮》展現(xiàn)了一個(gè)回族玉器世家的生命史,展現(xiàn)了不同人物在歷史中的沉浮與生命的悲劇;在深層意蘊(yùn)上,《穆斯林的葬禮》展現(xiàn)了月意象背后的回民共性,同時(shí)展現(xiàn)了霍達(dá)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
參考文獻(xiàn):
[1]黑格爾.美學(xué)(第一卷)[M].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2]馬麗蓉. 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伊斯蘭文化[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 霍達(dá).穆斯林的葬禮[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
[5]朱昌平.吳建偉.中國回族文學(xué)[M].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6]李純子.淺析小說《穆斯林的葬禮》的敘事結(jié)構(gòu).湖北.華中師范大學(xué).20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