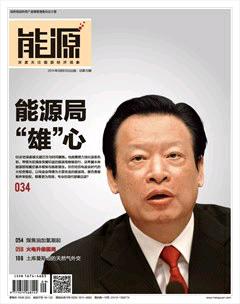“上大壓小”政策的綜合評估
張樹偉+陳曉娟


我國的電力系統結構經歷了從火電主導到火、水主導,進而多種電源快速發展的階段。最近10年,在電荒緩解之后,機組容量偏小、效率偏低的問題日益暴露。2004年,國家發改委出臺了新建燃煤電站的技術標準,要求新建火電單機容量原則上應為60萬千瓦及以上,發電煤耗要控制在286克標準煤/千瓦時以下,從而開啟了中國火電的“大機組”時代。在能源強度下降20%目標的壓力下,從“十一五”開始,小火電關停,代之以大機組(稱為“上大壓小”)的政策開始推進。
“十一五”期間,全國累計關停小機組7700萬千瓦。其中油電大約700-1000萬千瓦,其余均為煤電機組。2011、2012年進一步關停350萬與200萬千瓦,而2013年關停也達到450萬千瓦。大部分關停煤電壽命超過20年、容量低于20萬千瓦,但是也有一些建成時間很短的。而新上的大型機組,主要是60萬千瓦超臨界與100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2006年初,單機20萬千瓦及以下小火電機組容量超過2.2億千瓦,占比為47%。而通過這些年不斷地上大壓小與上馬大容量機組,到現在,我國電力系統60萬千瓦以上的大機組,已經占據了1/3的份額。
在一個主要由大機組構成的系統中,單純看大機組本身,的確具有比小機組更好的能源利用與排放績效。但是,如果擴大到系統的角度,很顯然,大機組更適合工作在基荷;負荷尖峰時刻則更適合小機組,特別是投資成本小、啟停非常迅速的天然氣機組。因為它的利用小時數非常低(通常一年內只有幾十到幾百個小時),燃料成本低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效率高低變得無足輕重,而投資成本大小成為關鍵。一個合理的電力系統,對應于負荷曲線的特性,應該是大中小各種機組配合的系統。如果說從電力系統運行角度,電力系統“電源結構”很難存在最優標準,但是不同單機容量機組間的配合,以更好地契合峰荷、腰荷與基荷的特性,往往存在實用性的標準。
而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對過去一段時間小火電提前退役的影響進行了評估,特別是燃煤消耗與污染物排放方面的評估居多。但是,這些評估基本是靜態評估,基于一個2005年假想的“效率不變”基準線。這一上大壓小帶來了可觀的能源節約與排放減少。但是,如果從靜態變為動態評估,也就是考慮機組的年齡(Vintage)結構帶給整體能源與環境的影響,那么結果可能并非如此。
既有小機組已經運行了一段時間,很可能在未來10-15年就會到期關閉,而新建大機組無疑將有很大可能性運行到設計壽命結束,比如30年以上(否則意味著再一次的提前退役)。如果10年之后新增火電就出現了政策上的限制,那么“上了大機組”的累計排放將可以預計的要高于“小火電正常到期”的假想情況。這種累計排放的增加,其實是與最初關停小火電的初衷相矛盾的。
上大壓小的環境產出
中電聯(2011)的報告測算,“十一五”期間,電力化石能源排放減少17.4億噸(相比2005年效率基準線),其中小火電關停是一個主導的因素;而Price等(2011)在《能源政策》雜志的文章計算表明,2006-2008年,通過小火電關停,節省了7500萬噸標準煤(相比2005年效率)。但這些研究,都是靜態的測量。
如果我們考慮到整個煤炭裝機的年齡結構,如此大規模的小火電關停與大機組替代(8000萬千瓦以上,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的總裝機量),動態的結果可能與靜態完全不同。
基于年齡結構與30年設計壽命進行測算,在未來,如果一直沒有新建煤電機組的限制政策,那么提前退役小火電將取得長期的減排結果。相比小火電到壽命自然退役的情況,提前關停小火電提高了2005-2012年的總體煤電效率0-0.7%。2005-2050年累計,關停小火電使得累計CO2排放減少0.1億噸以上。
但是,如果在2020年,煤電行業出現了政策限制。那么,自然退役與提前退役的情況就可能反過來。最為激進的,就是2020年后不再新建燃煤電站。自然退役條件下,大量的小機組在2020年左右將退役,從而在總的電源結構中,煤電的比例將出現大幅度下降。而提前退役情況下,由于2006-2013年巨量的煤電大機組的建設,這部分機組到30年后,也就是大約2030-2040年間,才有大量的電廠到期退役,排放將持續30年。2005-2050年累計,其CO2排放將比正常退役情況多出5.3億噸。如果沒有局部污染物排放體系的升級,本地污染物的累計排放情況也大致如此。這一測算并沒有考慮加裝CCS的可能性,因為這很可能會從經濟上讓煤炭進一步喪失競爭力。
那么,2020年后不再新建燃煤電站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這不是一個預測問題,而是一個政策問題。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已經推出了2030年電力行業相對2005年減排30%的行政命令,煤炭發電不加裝CCS很難有它的位置,加裝了CCS在成本上更難跟天然氣發電競爭。
從這種意義上以及我國重度霧霾的嚴重影響來看,環境資源是比能源資源更加稀缺的。如果環境約束是緊的,可能相當一部分化石能源的命運將是永久地留在地殼之中。煤電自然也就沒有了它的位置,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提前退役,成為“擱置”資產(stranded asset)。面臨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新的信息與政策出臺的可能性,大量大火電機組的上馬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浪費”的風險。
在我國,2020年是否頒布這樣的限制法令,將更多地取決于其他競爭性電源是否可以彌補火電空缺的問題,特別是核電與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態勢與成本競爭力。至少從最近幾年看,由于整體經濟處于“換擋期”,總體需求增長緩慢,非火電機組快速增長,火電機組會從總量增長減弱與結構調整兩方面受到擠壓。大機組的年負荷因子也只在50%左右,開工不足問題嚴重。
小機組的優勢
長期來看,一個基于大比例(比如超過80%)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系統越來越成為人們的期待。但是,可再生能源隨機性、間歇性的特點決定了系統總是在或大或小的概率上,存在可再生出力無法滿足需求的時刻。這種情況下,儲能或者其他化石能源備用機組就顯得愈加不可或缺了。
在我國云南、遼寧,甚至甘肅等地區,由于各種能源資源極其豐富,一個純非化石能源系統是完全有可能產生的。在一個起作用的電力系統中,火電機組有可能進一步降低負荷水平,甚至完全“淪為”備用。這種情況下,無疑小機組具有緊密跟隨負荷、風力出力變化更好的靈活度,其深度調峰的代價相比而言也較低。
過去,我國風電的布局思路延續了傳統的大機組模式,集中開發、匯聚上網、升壓外送、降壓使用,走了一條與國際可再生能源發展不同的發展道路。由于嚴重棄風、系統靈活性下降等問題的暴露,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風電分布式接入、就地利用模式的優勢。
而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并不局限于風電,傳統的電源也一樣。分布式電源基本都是滿足小范圍需求的小機組,并且構成了智能電網系統重要的組成部分。
上大壓小的減排成本
“上大壓小”即使就其靜態減排效果的取得來衡量,可以預計其減排成本將非常高,因為小機組的固定投資已經屬于沉沒成本,其增量成本將是新增機組的全部成本(固定投資+運行+燃料)與小機組的可變成本(運行+燃料)的差值。據測算,其實現單位CO2減排的成本在800元以上,比CCS還高。其他的局部污染物(比如二氧化硫與氮氧化物),由于基于已有的80%左右的脫硫率,以及一定水平的脫硝率,其減排成本也將高于其他煤炭利用設施,比如鋼鐵與其他燃煤鍋爐行業。
這一測算,還僅是項目本身的成本變化,沒有考慮其帶來的就業變化等社會影響。作為一項“命令-控制”型政策,上大壓小的減排成本不低。
目前系統中的大、小機組,無疑都具有滿足電力需求、提供調峰服務等功能,而大機組在滿足需求快速增長、提高系統整體效率方面居功至偉。未來不需要建設小機組(因為效率低),但現存的小機組在系統中將越來越有價值(因為靈活、只有可變成本故經濟性好),這應該是共識;而現在大機組可以說已是火電主體,未來是否需要繼續建設煤電大機組應當審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