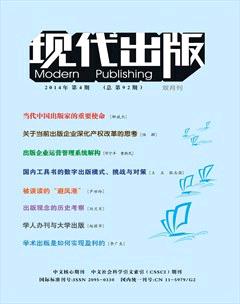出版觀念的歷史考察
◎ 劉蘭肖
出版觀念的歷史考察
◎ 劉蘭肖
本文從我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入手,考察出版觀念的萌芽以及由此形成的古代出版傳播觀念的特點;通過對儒家文化價值觀和傳統四部之學學術體系的考察,梳理經世致用思想在古代出版活動中的發展以及古代出版學術思想的演進;結合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考察愛國主義、出版自由、版權意識等近代出版觀念的輸入與衍變,以期揭示出版的觀念與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從中尋找出版學的學科發展淵源和思想發展脈絡。
歷史意識;經世致用;出版學術思想;近代出版觀念
按照學術界以關鍵詞為中心的觀念史研究路徑,從思想社會史和語境主義的視角考察一個詞的流行及其涵義的變遷,對出版領域一些關鍵詞進行發生學和傳播學的研究,無疑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不過,就出版學的研究現狀而言,當前也許更加需要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一些重要歷史問題作出回答。因此,本文試圖從幾個不同側面大致梳理從古代到近代出版觀念的衍變與出版實踐的關系,以期厘清出版學的學科發展淵源和思想發展脈絡,從而進一步明確學科的發展途徑。
一、歷史意識與出版傳播觀念
出版觀念的產生,始于人類自覺進行的歷史記錄。殷商時期,人們對于重大活動均用占卜方式作出決策,并把占卜的事項、結果或應驗,用文字符號記錄在龜甲和獸骨上。這種被稱為甲骨文的文字,是我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依據。西周時期,人們選擇在青銅器上鑄或刻寫文字,以之記載重大事件,被后世稱為鐘鼎文。這些銘辭的結尾常常刻有“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字句,也即希望承垂后世。從這個意義上說,青銅銘文比甲骨文前進了一步,被賦予了有意識地進行歷史記載的性質。而這種歷史意識,就是出版觀念的源頭。
歷史意識是出版活動得以產生的深刻動機。人們把某一文本或記錄通過一定的載體或復制形式進行傳播,其深層的觀念依據,是試圖超越個體的有限生命,把人的活動和思想保存下來,流傳下去。“子子孫孫永寶用”的銘文,即是這種觀念的具體體現。與我們今天的傳播觀念迥然不同的是,這是一種縱向傳播和代際傳播的深度傳播觀念。《禮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①《墨子》的《尚賢》《明鬼》等篇更加明確地說:“古者圣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于竹帛”,“咸恐腐蠹絕滅,后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②。《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三不朽”的價值觀,尤其為后世推崇和遵循。特別是對于“立言”的重視,引導歷代知識分子著書立說,“文以載道”。他們把文字和文字傳播看得尤其重要,即便不能在當代彰顯,也要傳諸后世、以待知音。司馬遷在《史太史公自序》中談及自己寫《史記》的動機就是為了“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論斷。劉知幾寫《史通》,因擔心此著不能流傳“淚盡而繼之以血”。明代學者何喬遠寫的分類體明史著述,書名就叫《名山藏》。歷代文士更是熱衷于把自己的文字結集刊刻。據《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統計,僅宋代就有739人的詩、詞、文別集(或合集)流傳至今。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去世前作《白氏集
后記》中說:“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禪林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圣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于家,傳于后。”③用五本分藏的方法讓自己的作品最終得以保存,古人為文字傳世而費盡心機由此可見一斑。而中國古代出版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寺院刻書等四大刻書系統中,以家刻系統的文化屬性更為突出,也是因為那些成就卓著的私人藏書和刻書家參與刻書事業的目的,考慮更多的是傳承文化,而不是市場需求。他們刊刻之書,多是經史子集及有用于世的實學之作,而非迎合大眾的通俗作品。在這一出版傳統的背后,其深層的觀念依據,就是長期以來起主導作用的代際傳播和縱向傳播觀念。
二、儒家文化與經世致用思想
講究經世致用,是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儒家文化創始人孔子在鬼神問題上提出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等觀念,特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哲學,引導古代知識分子沿著由內而外的路線,以積極入世的心態在現實世界中建功立業。
作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價值觀,經世致用的觀念在出版實踐中不斷豐富起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意識到書籍具有彰往察來、垂法萬載的功效,通過整理匯編《六經》,保存了許多有助于治理國家的歷史文獻,并且通過確立一系列編輯原則以別善惡、寓褒貶,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如孟子所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④這不僅深刻揭示了《春秋》的政治功能,也深刻反映了人們對于書籍編纂和文獻整理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西漢時期,司馬遷自覺將經世致用作為《史記》的編輯宗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⑤在他看來,歷史是現實的鏡子,考察歷史重在“稽其成敗興衰之理”,把握古今盛衰的規律,尋求實現長治久安的方法。此后,經世致用思想在出版活動中獲得進一步發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觀點,一是劉知幾關于“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的論述,深刻揭示了編纂史書的社會價值及其與國家發展的關系。二是杜佑提出的“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鮮明地體現了經世致用的高度自覺。三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經世致用的實現路徑,就是要“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⑦及至清代,王夫之發展了司馬光的這一思想,強調史書必須信而有征,“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實”⑧。由此可見,作為我國古代出版觀念核心的經世致用,其思想內涵經歷了一個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體現在出版實踐中,一是在通經致用思想推動下形成了一批有影響的經注書籍,二是在以史為鑒思想指導下推出了一批歷史和史學著作,三是從現實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編寫刊刻了一批具有專業性和實用性的類書。明清以至民國時期,還持續興起了“經世文編”和“經世文續編”潮,也就是將各種經國濟世之文,主要包括治國得思想策略以及典章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編纂形式匯集起來的出版熱潮,被稱為清末民初“六大世風”之一。⑨
三、古代學術與出版學術思想
在歷史意識和經世致用思想主導下的古代圖書出版活動,直接推動了傳統學術體系的建構。從西漢以至清代逐步形成的圖書典籍四部分類,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精神內核。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也就是說,典籍是儒家進行王道教化的教材,學術的目的在于維護王道倫理的秩序,所有知識的界定及其展開都要以此為準繩。由此形成的以經為根,依經、史、子、集之次第排列的中國古代圖書分類體系,就構成了以經典中心主義為特征的中國傳統學術的主干。⑩
古代學者在整理圖書的出版活動中建構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同時也逐步形成了以目錄學和校勘學為特色的古代出版學術思想。孔子整理“六經”即以“仁”為中心,提出三項原則:一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有文辭;二是“不語怪、力、亂、神”,刪去蕪雜妄誕的篇章;三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刪除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言論。為實現這一編輯意圖,孔子還總結出“多聞闕疑、無征不信”的編輯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先秦以來藏書的過程中,提出了“校讎”的概念。對此,清代學者章學
誠曾作出全面的總結:“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這里的“部次條別”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對劉向、劉歆出版學術思想的高度概括。劉氏父子“參以司馬遷之法”,作《別錄》《七略》,后者用《輯略》作序錄,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用《六藝略》《諸子略況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諸子略》作為分類編目,這就屬于部次。在此基礎上再分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10家,按流別對圖書進行分類。此后,把劉氏思想發揚光大的第一人,是宋代的鄭樵。他在《通志·校讎略》中全面闡述了圖書目錄“通古今之變遷,明學術之源流”的思想,并在《通志·藝文略》中提出了實現這一思想的具體方法,被稱為創建圖書目錄學的先驅。鄭樵認為,目錄學的任務就是條理書中的學術,告訴人們如何治學,書的存佚是學術盛衰的表征,只有“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才能使人們“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這就從學術的角度辨明了整理圖書與制作官私藏書目錄之間的不同。及至清代,在考據學盛行的學術環境下,章學誠撰寫《校讎通義》,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劉向、劉歆和鄭樵的思想,提出三個方面的主張:一是全面總結目錄學的傳統,指出目錄學應以探討學術源流、考究其得失為宗旨;二是順應學術發展大勢,提出以類例申明學術,對四部分類法進行調整:“《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宗劉》)。三是推廣互著與別裁之法。“互著”“別裁”是分類著錄中的兩個重要輔助方法,前者是將同一書分別著錄于甲乙兩個類目,后者是把書中某一部分從本書析出,著錄于其他類目。這兩種方法,一為求“全”,一為求“備”,根本目的都在于使四部之法既能辨章學術,又能方便稽檢。對此,章學誠總結劉向、劉歆以來的學術成就,從理論上對互著別裁之法進行了系統論述,推動古代出版學術思想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四、西學東漸與近代出版觀念的輸入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后,在西力東侵和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西方近代出版觀念傳入中國,通過有識之士的傳播而深入人心,推動出版業呈現出不同于古代的近代特質。這里僅就其中的愛國主義、出版自由和版權意識三個方面作些梳理。
近代中國起支配作用的觀念形態,是以反抗列強侵略為主旨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觀念形態在出版實踐的表現,一是推動了翻譯出版,二是開啟了教育出版。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許多中國人認識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據學者統計,從1840年到1861年,有關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書籍至少有22種。創建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從1871年正式出書至辛亥革命前期,翻譯出版西學著作達200種。甲午中日戰爭以后,維新派更是高標“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的出版觀,大力宣揚譯書對于變法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天下識時之士,日日論變法。……故及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而國家將不能收一法之效。”戊戌政變后,東渡日本的留學生增多,掀起一波新的翻譯出版潮。僅商務印書館1902年到1910年間出版的譯作就達330種,其中嚴復的《群己權界論》《天演論》等譯作,大力傳播各種西方近代思想,切實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與此同時,被稱為中國近代“出版第一人”的人張元濟,懷抱教育救國夢想,成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大力編譯教科書,“篳路藍縷,煞費苦心,得成一種輔助教育的新事業”。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也清晰地表達了“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的出版觀,認為“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陸費逵從理論層面揭示了教育出版的意義和作用,在中華書局創立之初編寫出版一批新式教科書,與商務印書館共同開啟了近代教育出版的先河。
如果說愛國主義是以經世致用為特征的古代出版思想在近代的發展,那么伴隨著近代中文報刊這一新式出版物而輸入的出版自由思想則是近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出版觀念革命。1833年,馬禮遜在其主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刊登《新聞紙略論》一文,簡介西方社會自由發表言論和出版報刊的狀況。1838年,該刊發表《自主之理》一文,最早在中文刊物中談及“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的西方言論自由觀。1881年,由傳教士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介紹了被資本主義各國視為憲法藍本的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
與出版自由同時輸入中國的版權意識,是近代出版不同于古代出版的另一重要思想特質。在我國相沿成習的觀念中,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寫書刻書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為天下教化。因此,古代知識分子并不把未經授權許可而復制自己作品看作一種侵權行為。這種觀念直到宋代才發生了變化。根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南宋年間刻本有“眉山和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板”的字樣。朱熹也曾就打擊盜版偽書、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進行過嘗試。但這只是一種原始的版權意識,與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相聯系的近代版權思想,則是由西方傳教士輸入的。1903年《萬國公報》第197號《歐美雜志》欄中,刊載林樂知、范祎譯述《版權通例》,介紹西方各國版權保護通例。1904年,《萬國公報》第183卷發表林樂知《板權之關系》一文提出,所謂版權,就是指“著書者、印書者自有之權利”,“(版權)保護乃國家之責任,而非其恩私也”,呼吁清政府承擔起版權保護之責。近代中國人認識到版權保護的重要性,始于啟蒙思想家嚴復。他在翻譯出版《原富》的過程中,曾與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張元濟反復商討版稅問題。1903年,商務印書館在出版嚴譯《社會通詮》時,首次使用版權所有的“稿主印花”作為著作權的憑證。同年,嚴復上書學部大臣張百熙,闡述版權保護與國家的貧富強弱和人民的文明愚昧休戚相關,要求實行“版權立法”,保護“著、述、譯、纂”者權利。至1910年,清政府頒布《大清著作權律》,結束了中國單靠官府文告保護版權的歷史,為把版權保護正式納入法制軌道開啟了先河,也成為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影響下出版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劉蘭肖,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綜合處處長)
注釋:
①阮元.十三經注疏[Z].北京:中華書局,1980:1606.
②諸子集成[Z].北京:中華書局.1986:41,147.
③白居易文集[Z].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4758.
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19.
⑤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3:1044.
⑥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M].北京:中華書局,1980:206.
⑦陳垣.通鑒胡注表微[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0.
⑧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M].北京:中華書局,2013.
⑨張枬、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Z].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740-743.
⑩左玉河.典籍分類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演化[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48-59.
雙擁辦是該區對口解決退役軍人問題的部門之一。這些年一起走過的風風雨雨,讓這些退伍老兵已經把這里當成了“娘家”,一有空就前來扎堆,互訴衷腸,互相鼓勵。他們對杏花嶺區為他們千方百計排憂解難的做法非常認可,對王業發這樣肯撲下身子實干、能不畏艱難敢于擔當的干部很是欽佩。王業發得到了部隊官兵、家屬、復退轉軍人、軍烈屬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