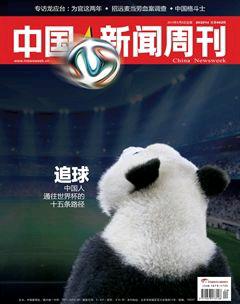從要電話到人性異化
李松蔚
長期的宗教體驗已經剝奪了這些人感到痛苦的能力,人已經被異化成了非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離苦得樂”這種幻覺的孜孜追求,所釀出的惡果。
聽說過這樣一類培訓,專門幫助那些不善于社交,尤其是害怕異性的男士們提高勇氣。課程的設計中,最核心的環節是這樣的:上街找一百位異性,開口要她們的電話號碼。這個過程中,學員難免被拒絕個八九十次,甚至一百次通通鎩羽而歸也未可知,但這不妨礙訓練達到效果——因為要的就是“被拒絕”。它背后的理念在于:學員們之所以在社交中感到緊張,就是因為他們還不能適應被拒絕的痛苦。這時候,就要讓他們長時間地反復暴露于被拒絕的刺激下,習以為常就可以波瀾不驚。
這套方法和心理治療中的“暴露治療”技術很像。后者是用來幫助那些恐怖癥患者的,也就是過度強烈的驚恐造成了臨床意義上的功能失調的病人。將這種治療手段拓展到日常應用中時,我認為需要特別慎重。——打個或許不恰當的比方,就像用于鎮痛的鴉片,雖然會幫助病人減輕病痛,但也是有代價的。
我們可以用它隔離自己不喜歡的感受,但隔離之后又會如何?在社交場合中,被拒絕或是被低看的滋味的確很難受。以至于大家都認為,如果能找到一種方法,一勞永逸地“離苦得樂”,人生豈不是會美好很多?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的確如此。但是另一方面,這些糟糕的情感本身,也是正常人在生活中正常經驗的一部分,正如身體受傷就會疼痛。假定這種痛苦被隔離,是否我們自己也會被異化?
進化心理學告訴我們,藉由痛感,才可以及時發現潛在的威脅或身體的傷損。那些感覺不到疼痛的人,也許已經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被自然淘汰。同樣的道理,負面的情感體驗雖然糟糕,實則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適應性成分。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們與感興趣的異性搭訕時,縱然面紅耳赤,心如鹿撞,其實也是一種與對方的潛在情感交流。相比而言,像機器人一樣程序熟練地、直勾勾地走過來握手,露出設計好的微笑,口若懸河地大聲念誦之前背好的臺詞,這種搭訕姿態反而讓人渾身發毛。這種感覺,你也許在接受過類似培訓的傳銷人員身上有所體驗:說不上哪里不對勁,但肯定是不對勁。
這種“不對勁”的感覺,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們感受不到情感的正常交互。在應該緊張的時候,沒有緊張;應該煩惱的場合,不曾煩惱。更看不到有反思或自我覺察的內省。一切都是冷而僵硬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像一臺高效能的機器自動化地執行操作指令,讓旁觀的人不寒而栗。我有一回在公交車上,看見一位老大媽中氣十足,聲情并茂地向全車人宣講信仰,演說“生命的意義在何方?”講到她曾經恥于在人前開口講話,現如今借著信仰之力,何等自信云云。等她下了車,全車人面面相覷,相視苦笑。這一車人,我估計后半輩子都會對那個信徒的形象心懷戒懼。
如果再拔高一點,這種“不對勁”的感覺,是覺察到了人性中的異化。人性深沉復雜,因此必定也包含痛苦。但痛苦又實在是我們平時太想逃避的一種感受。因此無論課程也好,傳銷也好,或正或邪的信仰也好,往往都會把“離苦得樂”作為噱頭。一個人在生活中的煩惱越大,越可能依賴于這樣的“解脫”。其危險在于,對快速和簡便的執著,最后常常落于對情感的否認之上。我過去接觸過一些帶有洗腦、靈修性質的培訓,不止一次看見信眾們時而失聲痛哭,時而幡然頓悟,明明受人愚弄,卻將導師的教誨奉為圣旨,將同道間的相互鼓舞看作精神源泉,自以為開啟了與人間苦痛絕緣的新生。殊不知,只是扭曲了自己的情感體驗,變成了一個糊涂蟲而已。
敏感的人也許會從“要電話號碼”這個細節,聯想到發生在招遠市麥當勞的恐怖案件。要說明的是,雖然邪教的培訓常常也用類似的技巧,但兩者的性質始終有天壤之別。在招遠案件中,信徒“離苦得樂”的需求已經發展到病態的極致,以至于根本無法容忍對方說一句“玩去”的拒絕。其實人們遭到拒絕時,有的會死皮賴臉,有的一笑了之,也有的郁悶不已,甚或傷心欲絕。但只有最病態的人,才會從根本上否認這一事實,如精神分裂癥患者,或這樣的邪教信徒。給對方打上“惡魔”的烙印,如此一來,遭受拒絕的就不是我,而是我的神,而血腥的殺戮暴行居然也就成了“榮耀”之舉——這是何等扭曲的幻覺?
真正最讓人毛骨悚然的,還是面對淋漓的鮮血,信徒們那毫無罪疚或驚懼的一臉淡然。我想,長期的宗教體驗已經剝奪了這些人感到痛苦的能力,人已經被異化成了非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離苦得樂”這種幻覺的孜孜追求,所釀出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