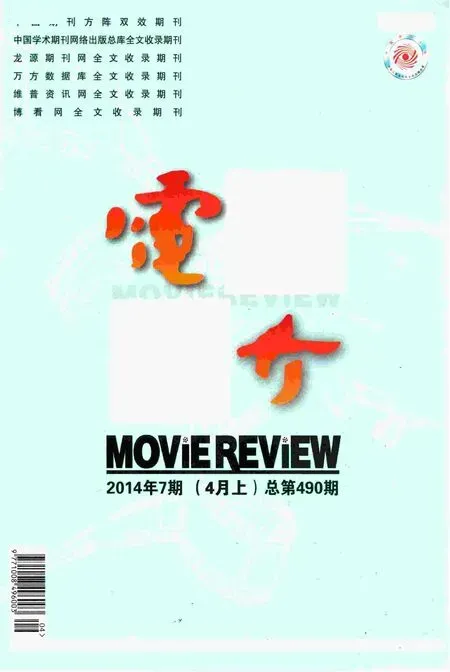從獵奇到常態的華語同性戀電影
□文/沈 麗,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電影《洞》劇照
所謂“同性戀電影”,是指包含同性戀角色、以同性戀為主要情節,并且以積極的、有作為的方式來處理同性戀主題的影片。華語同性戀電影,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人的自我意識的增強而逐步成形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華語同性戀電影“出柜”以來就大行其道,逐漸從小制作登上大雅之堂,甚至有專門為同志電影而舉辦的電影節。華語同性戀電影中的酷兒形象,從以往的壓抑迷茫轉向堅持真我,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吸引人們的關注。
一、敘事策略:從現實倫理到以愛動人
(一)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同性情誼
縱觀我國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電影創作,同性戀華語電影微乎其微,多是對于曖昧的同性情誼的觀照,即使是少數涉及同性戀題材的影片對同性戀的表現也是拘謹或者變形的。早在1934年,孫瑜導演的《大陸》就暗含了同性戀亞文本,其中大量關于男性健美形體的鏡頭以及女孩親吻、擁抱的場景都帶有同性導向的暗示。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尤其是50年代后的“十七年”電影、文革電影、80年代電影等特殊階段,《戰火中的青春》、《舞臺姐妹》、《大閱兵》這些影片都忽略了性別差異,更多地表現政治意圖和“純潔”的同性情誼。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階段同性戀題材電影的失語呢?考察中國歷史會發現,從商代的“比頑童”到魏晉的“狎昵孌童”再到清代的“私寓”制度,“男風”從來沒有間斷。對于同性戀的稱謂也非常豐富,如龍陽、斷袖、分桃等。可是,近代以來的中國卻從道德和法律上對同性戀進行制約,使同性戀題材在電影領域處于失語狀態。
(二)20世紀90年代的人性探討
20世紀90年代,華語電影在“同性戀”題材上有了質的突破。不管是同性戀的非刑事化還是港臺的電影分級制,都為華語同性戀電影的“春天”營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這類影片逐漸被大眾接納,一度成為電影節上的熱門,柏林影展甚至在1998年第一次增設“最佳同性戀影片”銀熊獎:《喜宴》獲得1993年柏林影展金熊獎、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獎項;《愛情萬歲》獲得1994年第51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臺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獎項;《東宮西宮》獲1996年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春光乍泄》獲得1997年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愈快樂愈墮落》摘得1998年柏林影展首個“最佳同性戀影片”銀熊獎。這些在國際、國內獲獎的同性戀電影足以說明“同性戀”題材以一種開放的姿態進入大眾視野。
這一時期,華語同性戀電影開始觀照這一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但仍然沒有直接為同性戀群體敘事,而是將同性戀視為用來探討人性、民族、文化的載體,將同性戀情節隱匿在家庭倫理、時代命運、自我抗爭等題材背后,表達導演個人抗爭、追求人性自由等超越“同性戀”的更廣闊意義上的主題,當然也不排除部分影片以“同性戀”為噱頭博取關注。
《喜宴》是李安走向國際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導演借由同性戀話題、以輕喜劇的形式引發東西方文化的博弈,企圖尋找一種跨文化背景下愛情和倫理的調和。影片中父親的妥協以及贏得勝利的高偉同和同性愛人賽門,象征著中國傳統倫理觀的瓦解,對個人追求自由、幸福的禮贊。該片雖然以同性戀為表現對象,但根本上還是表現了導演“突破傳統、實現個體價值和人性自由”的主題。
這一時期的華語同性戀電影僅僅將同性戀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進行表達,同性愛在電影中并未得到正面、真實的展現,反而是利用同性戀來反映主人公的心理狀態,比如張元的《東宮西宮》、蔡明亮的《洞》等。
(三)2000年以來的純愛路線
自從2001年荷蘭成為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開始,到2014年4月已經有29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與民事結合。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同性戀越來越能被人們所接受。而社會環境的寬松、商業利潤的驅使,使得華語同性戀電影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2005年底李安的《斷背山》席卷全球。影片講述了1963年至1981年的美國懷俄明州,兩個男人之間情愛與性愛的復雜關系。該片在威尼斯電影節奪得金獅獎,在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了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與最佳電影配樂三項大獎。《斷背山》不僅在商業上獲得成功,還在社會上掀起了對同性之愛的大討論。在華人文化圈,“斷背”一度成為同性之愛的代稱。相比于將《斷背山》定位成一部同性戀電影,李安更強調這樣一種普世價值觀:“愛是可以超越文化差異的,當愛降臨時,異性之愛與同性之愛是毫無差別的。”《斷背山》雖然以愛情悲劇收尾,但是這一段傷感卻美好的同性愛情無疑感動了萬千觀眾。
這種反映同性戀者感情和生活的影片正在逐漸增多,這種電影普遍展現了同性戀人“正面”的、現實主義的形象,講述他們的愛情故事。譬如關錦鵬的《藍宇》、陳正道的《盛夏光年》、周美玲的《刺青》等。這些影片大都講述學生時代懵懂而無謂的愛情。這種主題往往會使觀眾忽略性別、社會等外在因素,沉浸在影片營造的真切情感之中。
二、欲望表達:從隱晦走向直白
福柯在《西方和性的真相》一文里認為“我們的社會好幾個世紀以來多么熱衷于增多法規,以便強行取得性的真相,并從中產生一種特殊的快樂……我認為,我們的社會與其說是一個注定要有‘性壓抑’的社會,倒不如說是一個注定要‘性表達’的社會。”世界各國的同性戀電影最具有顛覆性的努力正體現在“性表達”方面。[1]在華語同性戀電影中,對于性問題的表現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情欲的展現
從古希臘開始,人的身體就成為了人們的審美對象。在2000年以前的華語同性戀電影中,由于社會、文化等原因,直接表現同性性愛的場面太過超前,身體的展現就成為了欲望的表征。從《大陸》中數名男演員赤裸上鏡、展現健美的肌肉到《喜宴》中對男主角高偉同在健身房的一系列特寫,都是利用身體來表現性感、暗示性欲。
新世紀以來,華語同性戀電影驟然增多,對于情欲的表現也由原來的隱晦逐漸直白起來。《藍宇》中,陳悍東和藍宇赤裸的身體、親密的愛撫鏡頭,和異性戀電影一樣,都是作為一種升華情感、剖析內心的手段。在電影《蝴蝶》中,無論是對年少的蝶同真真還是成年的蝶和小葉之間的同性性行為的描寫,無疑都是大膽、顛覆的。性的問題與人的快樂有關[2],電影正是用這類鏡頭來把握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轉變。
(二)方式的多樣
華語同性戀影片中每段感情中主角對于自身的情感表達不一而足,因此對于欲望的表現方式也是多樣的。“柏拉圖式”的、脫離性欲的影片在新世紀的同性戀影片中逐漸讓位于對性欲的直白表現,表現的方式也多種多樣。
蔡明亮的“愛情三部曲”就展現了不同類型的欲望表達。在《青少年哪吒》中,阿澤在旅館里跟阿桂做愛,而小康則在雨中弄壞了阿澤的摩托車;之后,小康走進旅館而阿澤走出來。小康與阿澤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卻通過阿澤與阿桂的異性情欲暗示了小康對阿澤滋生的同性情欲。到了《愛情萬歲》中,當阿澤與林小姐在床上做愛時,小康恰恰躲在床下自慰。床上床下兩個世界,將小康的同性欲望揭示了出來。《河流》中,在同性戀聚集的三溫暖里,父親和得了歪脖子病的兒子于黑暗中把對方作了性伙伴,昏暗中的一場同性亂倫的戲將同性之欲表現到了極致。
與異性戀影視的影像表達一樣,同性的情感或欲望也是通過親吻、愛撫、性愛這些符號來表現。
三、“柜子”外面:從自我認同到社會認同
近幾年來,國內媒體對于同性戀的正面、中性報道日益增多,部分受眾對于影片中同性戀角色的接受度也在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環境下,影片中的同性戀形象也在發生著改變。與21世紀之前那些華語同性戀電影中壓抑、迷茫的同性戀形象相比,新世紀以來的這類影片開始傾向于塑造性向懵懂、張揚自我的青少年同性戀形象。
(一)成長中的自我
在哲學、心理學領域,認同主要指自我意識的萌生與成熟,從而形成穩定的身份感——自我認同。[3]21世紀以來的同性戀華語影片中,主人公對于自身性別身份的確認,探尋“我是誰,要向何處去”等問題的影片比較多。
2006年,陳正道執導的《盛夏光年》中,康正行和余守恒原本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而惠嘉的出現,糾結的三角關系最終使得康正行表明了對余守恒的喜歡。從懵懂無知到直面自身,這種自我認同的青澀情感在臺灣同性戀電影中占據了很大比重。主人公經過一段時間的困惑與掙扎之后,往往會通過自我主動宣告來表達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自豪。《少年不戴花》就呈現了一個男孩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從否認、隱瞞、回避到自我認同的過程。還有《藍色大門》里孟克柔迷茫的青春愛情、《十七歲的天空》甚至營造了“天下大同”的男男世界。
(二)人文關懷的立場
今天很多的同性戀者只是為得以在保障婚姻權利下安居樂業而爭取。為大家所知的美劇《同志亦凡人》塑造了各種類型的同志形象,有事業有愛情有家庭,扮裝者有之,濫交者有之,這些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不同側面,這種心平氣和展示一種生活的態度正是華語同性戀電影所需要的。華語同性戀電影中同性戀形象已經逐漸擺脫對性別的關注,轉而描寫或普通或理想化的同性戀群體,以積極的面貌給予同性戀群體以人文觀照。
在影片《海南雞飯》中,母親苦于三個兒子全是同性戀,但在與傳統道德觀磨合之后,母子最終達成理解,小兒子親手做的“鴨飯”送到母親口中,觀眾從中能感到一種親情的溫馨與偉大。從人文關懷的立場出發,將“同性戀”話語建立在溫和的政治話語之上,體現了對主流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尊重與人性道德的悲憫情懷。這種強調性別弱化而更重視情感體驗的態度,這是如今的同性戀影片需要的。
2011年上映的《命運化妝師》從頭到尾除了學校時期的幾場戲,并沒有特別強調同性問題的橋段。這種劇情發生在任意性別的兩個人身上都會讓觀眾產生情感共鳴。不刻意的強調,不將性別問題作為故事的主線,一切都自然且感人。同性戀題材退去神秘和新鮮感,作為愛情的一個分支,同樣值得長久地探討。
結語
雖然近年來港臺地區同性戀電影已經作為商業片登上了大銀幕甚至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和口碑,但是華語同性戀電影仍然是邊緣題材影片。2010年以后,內地幾乎沒有新的同性戀題材電影;而港臺電影也逐漸限于青春成長類題材中徘徊不前。華語同性戀電影要想走出小眾范圍、獲得主流價值觀的認可還需要更多努力。
[1]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392.
[2]李銀河.性文化研究報告[M].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3.
[3]姚文放.審美文化學導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