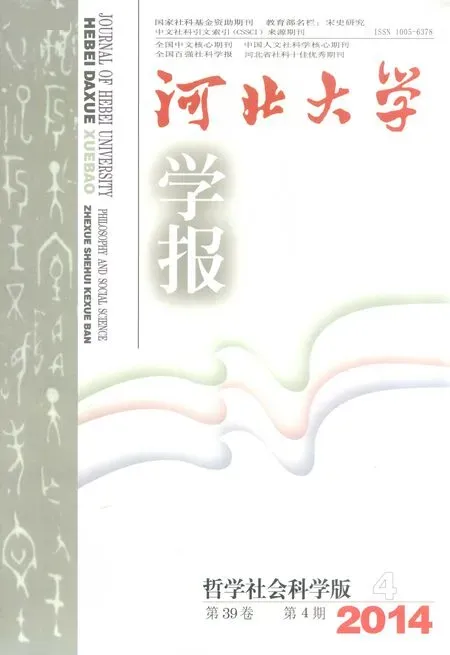維特根斯坦論自我
姚東旭
(南開大學 哲學院,天津 300071)
近代認識論轉向以來,關于自我的問題一直是哲學家們爭論的焦點。維特根斯坦對自我的考察大體繼承了近代以來自我理論的問題意識和思路。但是又由于其處于西方現代哲學的“語言轉向”之后,語言分析的方法取代了傳統的概念分析,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維特根斯坦的自我思想大體按照他個人思想的分期,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維特根斯坦以“界限主體”或“形而上學主體”來闡釋自我,并指出唯我論與實在論的一致性;而在中后期思想中,維特根斯坦區分了“我”在不同語言游戲中的差異,并指出,哲學家們在“我”的問題上犯的錯誤是由于表達形式相似性造成的聯想所造成的。本文將分別討論維特根斯坦前期與中后期自我思想,并簡要對維特根斯坦的自我思想作出評論。
一、前期維特根斯坦:唯我論與實在論的一致
(一)自我不是表象主體
簡單的回顧一下近代哲學中對于自我問題的討論有助于我們理解維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思想背景。笛卡爾肯定“我思”,即肯定一個意識活動在認識過程中的前提地位。但是,由這個意識活動出發,是如何認識到更復雜的知識的?它是如何表象更復雜的實在的?如果從“我思”出發,我們除了它自身以外,似乎再也無法更進一步。
洛克接過了這一問題,在洛克那里,自我首先是一個由諸多外感官集合而成的生命體,對外在刺激的接受形成的知覺活動是首先發生的,而對心理活動的反省則在知覺活動發生之后,這一反省意識可以通過回憶,當下認知和預期的方式與這一生命體的過去、現在、未來發生聯系。無論這一生命體如何改變,這一意識都可以保持同一,因此,這一同一的反省意識即是自我[1]。
洛克的思路大體是笛卡爾的一個逆轉,由一個能夠表象諸種復雜材料的反省意識取代貧乏的“我思”,形成了一個復雜表象主體的構建。但是,這一表象主體依然不是自我。休謨和羅素的思路中,洛克的反省意識沒有超出感覺經驗的范疇,而在經驗中人類形成的自我只是由習慣形成的知覺集合體。羅素認為對自我不能形成“親知的知識”,而只能形成對于個別思想和感覺意識的認識,是一種“描述的知識”,達不到前者的確實性[2]。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兩點:
(1)表象主體不能是簡單的,不然它將難以表象和認識復雜對象。
(2)如果自我是經驗的一部分,那么將不可能形成對它的確定的經驗知識。
維特根斯坦作為經驗主義思路的后承,面對著以上討論所帶來的問題:
(1)自我與表象主體的關系是怎樣的?自我是否是表象主體?(自我的本體論問題)
(2)自我與經驗的關系是怎樣的?自我是否是經驗對象?(自我的認識論問題)
維特根斯坦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首先否認了自我是一個表象主體。在命題意義的邏輯圖像論中,“每個命題都是對基本命題作真值運算的結果”(TLP 5.3)[3]69。但是,維特根斯坦對此提出了質疑:“初看起來,一個命題也可能以別種方式在另一個命題中出現。”(TLP 5.541)這類命題包括“某些心理學的命題形式”,如“A相信p是真的”,“A思考p”等。在這種形式中,命題的真值取決于主體A的命題態度。這就使得外延論點(Extensionality thesis)遇到了困境。表面上看,A是不同于命題p的主體,這也是心理學所設想的具備命題態度的主體概念。那么,心理學的主體是自我嗎?維特根斯坦對此批評說:“但是很清楚,‘A 相信p’,‘A 思考p’,‘A說p’都是‘p說p’的形式:這里涉及到的不是一個事實和一個對象的相關,而是借助于其對象相關的諸事實的相關。”(TLP 5.542)也就是說,表象主體與事實(事態)之間的關系即是借助共同關涉的對象A建立起的一個命題符號系統對另一個命題符號系統的具有同樣邏輯多樣性的描畫關系。即“‘p’說p”。命題態度“相信”“不相信”“思考”“懷疑”等都只是作為判斷要素而出現。這樣一來,心理學的主體—心靈就成為了具備復雜性的表象主體,而非一個不能被進一步分析的對象。但是,維特根斯坦評論道:“一個組合的心靈就已經不再是心靈了。”[3]81-82一個復合的自我不是自我。因此,自我不能是表象主體。
(二)由表象主體到界限主體
維特根斯坦對自我問題的回答是:“主體不屬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個界限。”(TLP 5.632)羅素對自我的處理方式是將自我看做是對我當下意識到的東西的意識,犧牲了自我的跨時間與空間的同一性,而使得自我有可能成為經驗知識。維特根斯坦則堅持了更徹底的經驗論:“如果我寫一本書叫做《我發現的世界》,我也應該在其中報道我的身體,并且說明哪些部分服從我的意志,哪些部分不服從我的意志,等等。這是一種孤立主體的方法,或者不如說,是在一種重要意義上表明沒有主體的方法;因為在這本書里唯獨不能談到的就是主體。”(TLP 5.631)也就是說,在經驗的成分中我們無法發現自我,自我不能被經驗或對象領域中的成分同一化。在接下來的一部分中,維特根斯坦更加形象的用眼睛與視域的關系來表達這一點:“你會說這就正好像眼睛和視域的情形一樣。但是事實上你看不見眼睛。”(TLP 5.633)“視域肯定不具有如圖這樣的形式”[3]85-86。

圖1 維特根斯坦的“眼睛”比喻的示意圖
這樣一個比喻可以類推到認識主體的任何一個領域。“如下之點是真的:認識主體不在世界之內,不存在任何認識主體”(NB 20.10.16)[4]244。
維特根斯坦這一思路受到了叔本華和康德思想的影響。康德將自我看做是屬于不在經驗之中的“物自體”的范疇,作用在于將經驗統攝起來,使其成為一個統一體。叔本華同意康德主體屬于物自體范疇的結論,并認為意志是世界的主體,世界只是同一意志在不同層面上客體化的產物,自我不是世界中的任何對象,而是意志主體。
維特根斯坦對康德和叔本華的思路有所繼承和綜合。他認為:“哲學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體,或者具有心理性質的人的靈魂,而是形而上學主體,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個部分)。”(NB 2.9.16)[4]237即以界限主體取代一切經驗的及對象化的成分,撇清了主體與表象主體的關聯。同時,維特根斯坦肯定了意志主體,“意志是主體對世界的一種態度。主體是意志主體”(NB 4.11.16)[4]245。但是,“作為倫理主體的意志是不可說的”。也就是說,叔本華肯定自我屬于物自體領域,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想法是正確的,但是他同時對只能“顯示”的自我有所言說了,即說了主體的本質是意志,這樣就使自我的本性歸之于意志,而“主體的本質 被 完 全 的 掩 蓋 起 來 了”(NB 2.8.16)[4]232。“意志是主體對世界的一種態度”(NB 4.11.16)[4]245。康德的“物自體”自我學說正確的把握了自我的“說出”與“顯示”之間的關系,但是康德的思路在于解釋自我是如何起作用的,即自我統攝經驗的知識論功能意義,而沒有對自我與世界的關系的本質進行說明。
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上的我是界限主體。用兩點來說明:“如果意志的善的行使或惡的行使影響到了世界,那么它們只能影響到世界的界限,而不能影響到事實,只能影響到不能借助于語言加以描畫而只能被顯示在語言之中的東西……可以說,它(世界)必定作為一個整體而增長或縮小。正如經由一個意義的添加或略去一樣。”(NB 5.7.16)[4]220自我是不能對世界中發生的事實產生影響的,它是屬于意義價值層面的范疇,而這些是不可說的,只能訴諸于神秘體驗。它改變的不是世界的內容。我們舉起手臂,發生的是手臂舉起來這一物理事實,而我的意志并沒有發生在經驗之中,也沒有對這一物理事實發生影響。自我改變的不是事實,而是事實的意義與價值。
另外一點,維特根斯坦強調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內在關聯。“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TLP 5.621)。 “我 是 我 的 世 界 (小 宇 宙 )”(TLP 5.63)[3]85。“生命就是世界,我的意志彌漫于世界”(NB 11.6.16)[4]219。也就是說,雖然我從我的世界中消失,不在我的世界中出現,但是世界仍然是我的世界。因為自我是不可言說的,自我唯有作為形而上學主體在不同的事實配置境況中才能夠顯示自己,即作為事實意義上“無”的“我”通過世界之中作為事實的不同的“有”而生成。
(三)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
以上兩部分分別討論了自我是否表象主體與自我的界限主體的內涵。這一部分討論的內容是唯我論與實在論的關系。在以上討論中,并未涉及世界和事實的表征問題。維特根斯坦是否在構架某種缺乏公共性的“私人世界”?從而造成了唯我論與實在論之間的不相容?如同經驗主義傳統中經常出現的“自我中心困境”?
維特根斯坦在這里采取的方式是揭示出唯我論的自我中心困境的內在矛盾:“我們不能思考我們所不能思考的東西;因此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所不能思考的東西。”(TLP 5.61)“自我中心困境”的根源在于沒有將唯我論堅持到底,“唯我論意味的東西是完全正確的,不過它不能說,而只能自己顯示出來”(TLP 5.62)[3]85。自我中心作為只能“顯示”的內容,雖然不能出現在經驗世界之中,但是因為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意義的邏輯圖像論,由于描畫世界所使用的語言是“我所唯一理解的語言”,因此,這種語言的界限即意味著世界的界限,從而保證了“世界是我的世界”。
維特根斯坦用一段話來表明唯我論與實在論的這種一致:“我所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唯心論將人作為唯一者從世界中挑選出來,而唯我論則只將我挑選出來,最后我看到,即使我也是屬于其余的世界的。因此,在一邊沒有任何東西存留下來,在另一邊所存留下來的東西是作為唯一者的世界。因此,唯心論,當其被徹底思考之后,導致了實在論。”(NB 15.10.16)[4]243
二、中后期維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推進
中后期維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由理想或本質語言的建構轉變到日常語言分析的思路。維特根斯坦試圖強調在使用之中的日常表達式的相對于各種理想語言或本質語言建構的優先地位。在唯我論與實在論的爭執中,維特根斯坦并不如前期一樣試圖建立一種自我理論,或試圖為兩者之間的融貫提供一種新穎的理想語言或理論構建。而是試圖指出唯我論、唯心論與實在論都是對日常語言表達的背離,是由于“表達方式所引起的各種各樣的聯想”[5]77的產物,是需要治療的哲學疾病。后期維特根斯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通過指出哲學對于日常語言表達式的諸種誤用(如對“我”的不同用法的混淆)來進行“哲學治療”。“你在哲學中的目標是什么?給蒼蠅指明從捕蠅杯中出來的出路”(PI 309)[6]177。
(一)“我”的兩種不同的用法的混淆
我們有兩種命題描述,一種用來描述外在世界中的事實,另一種描述感官體驗。在日常情況下,我們并不混淆兩種描述,令我們發生混淆的是我們就這兩種描述的表達方式的相似產生的聯想。比如,我設想一間“視覺屋”,這間房間是由我的個人經驗作為材料構成的,我們可以在描述它的時候使用習以為常的認識論術語,如感知到什么,看到什么等,但是維特根斯坦問:我們是否能擁有(have)這間“視覺屋”?我們能否看到一間房間而不能擁有它?我能否擁有一間房屋而不能在其中走來走去察看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形:在一幅畫上畫著一所房屋和一個農民,如果我們說“這所房屋屬于這個農民”,那么,這種“屬于”是哪種意思呢?這個農民不可能走進這所房屋,我們也不可能擁有一間由感覺材料構成的房間,在其中走來走去,買賣它,裝飾它等,因為“視覺屋的所有者必定是與它本質相同的;但是,他既不在它之內,也沒有一個外部”。這就是唯我論所導致的荒謬的結果。對于“有”來說,一個具有現實實在的“我”不可能有一間“視覺屋”。一個“內部”的東西如何走到“外部”?這條橫溝似乎永遠無法消除。除非我們承認,“有”從一開始就離不開它的“外部”含義[6]204-206。這里維特根斯坦反思的是以康德為代表的先驗自我對一切表象的統攝和伴隨理論,因為,我們不能事先決定一切都事先被自我“擁有”,只有一種“擁有”可被懷疑,可能是錯誤的,談及“擁有”才有意義。而唯我論的支持者恰恰忽視了這一點,因此才會談及到一種私人的“擁有”。即將“精神世界”看做是一個如物理世界一般的有廣延、可觀察、可所有的空間。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奇怪的假象。
維特根斯坦通過一系列的例子來指出關于“我”的諸種命題之間的差別。他區分我的“主體的用法”和“客體的用法”。我的主體用法中包括“我疼”,“我聽見如此這般”,“我看見如此這般”,“我牙疼”,“我感到你的牙的疼”,幻肢的感覺,感到別人身體的疼痛等,而客體的用法則包括“我的手臂斷裂了”,“我長了10厘米”等。前者與后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不可懷疑的,不存在識別錯誤的可能性,而后者則總是有識別錯誤的可能性[5]87。例如關于“我”的哲學困惑的根源就在于這兩種用法之間由于它們使用同一個詞“我”卻含有不同的含義而產生的混淆。他用“幾何學的眼睛”和“物理學的眼睛”來比喻這兩種用法,我們在談論“幾何學的眼睛”時,如我們談到在幾何空間中如何看待某個圖形,不同于我們用“物理學的眼睛”對事實進行觀察。這兩者之間的混淆讓我們誤認為自我是一個如“物理學的眼睛”一樣的對象,而去尋找它的經驗世界中的對應物,從而走上了將自我對象化的道路。或者以為“物理學的眼睛”實際上是“幾何學的眼睛”,即可以用主體用法取代客體的用法,那么將會導致唯我論的思路。
(二)“我”的主體用法
那么,“我”的主體用法與客體用法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在哪里呢?這里的回答是:我的主體用法中,“我”不是代表一個對象的名稱,但是卻與名稱有關聯。“我”的作用就像是“這兒”一樣,通過指示共同空間中的一個位置來標明自己。維特根斯坦舉了一系列例子來證明這一點。當我呻吟著說“我疼”的時候,我并沒有想要讓別人去注意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想要讓別人注意到自己。“我”并非用于區分兩個特定的人,而在于無條件的將別人的目光引向我,提醒別人注意自己,這就是“我”的作用。他設想了一個思想實驗:一群人圍成一圈,每個人都接上一個電極,電極會不確定的給某個或某些特定的人釋放電流。如果我們假定每次只有一個人會被釋放電流,那么感知到電流的人就可以通過說“我”把電流釋放的位置標記出來,而如果我們假定每次電極都無差別的釋放電流給每個人,那么說“我”則變的沒有意義。也就是說,“我”在這里不再起到標識或提醒的作用。“我”的主體的用法與客體的用法的關聯之處就在于:它不是一個名稱,但是它可以用來解釋名稱(PI 409-410)[6]208-209。
三、關于前期與中后期維特根斯坦自我思想的評論
從維特根斯坦前期與后期自我思想的關系來看。相同之處在于無論在理想語言層面還是在日常語言層面,都強調自我的非客體性,即自我不是一個經驗對象(可被考察的心理狀態、中立感覺材料、身體、物理對象等),自我不是經驗中出現的任何東西。前期維特根斯坦強調主體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主體是形而上學主體或界限主體。中后期維特根斯坦區分我的兩種用法“主體的用法”和“客體的用法”,并指出“主體的用法”的“我”在句子中的作用在于提醒或標識一個公共空間中自我的位置(這兒),同樣是來論證自我的非客體性。區別在于前期維特根斯坦立足于使得這一點與本質和理想語言的闡明相兼容,而后期維特根斯坦則轉為對日常語言實際用法的描述之中來。但是其前后期自我思想的整體傾向是一致的,就在于“反客體主義”(anti-objectivism)[7]。
維特根斯坦的這條思路被用于作為反對將自我作為某種經驗對象進行研究的各種進向。在當代,尋找古典哲學式的精神實體或某種直接經驗成分的自我的進向逐漸衰微,但是在神經科學和心靈哲學的討論當中,關于自我的討論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認知科學家通過對人類大腦的考察,推斷出某些與人類“自我”相對應的大腦機能,以內格爾為代表的自然主義二元論者,將自我等同于成為“像是”(What it is like to be)某個特定的有機體所是的東西。我們看到,這些討論雖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依然沒有擺脫客體主義的巢臼。Jesse Prinz將維特根斯坦的思路與當代神經科學中的各門進向進行對比后,發現,當代神經科學的思路大體還是其背后的傳統哲學前提的翻版,例如,Goldberg的“失去自我”的認知實驗是笛卡爾式二元論的一個翻版,Blakemore與Frith的斷定感覺內容與身體行為相互對應的實驗是梅洛·龐蒂的的現象學自我的一個證據,而Manos Tsakivis的更加新近的關于人能否“具有”一只假手的實驗是康德的“知覺意識集合體”的自我概念的一個證實[8]。而這些實驗所代表的思想范型都無法擺脫“客體主義”的巢臼。
值得注意的是由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的想法。內格爾在他的《成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樣子》[9]中,認為意識的主體性是實在的不可推斷的特征。雖然我們不可能感知到主體,但是我們會有一種無法脫離它的感受,這種感受就是“觀點”(point of view),即“像是”(What it is like to be)某個特定的有機體所是的東西。我們無法想象自己成為一只蝙蝠是怎樣的,是因為我們不具備蝙蝠的“觀點”。內格爾的看法似乎是在凝合維特根斯坦的“我”的兩種用法之間的溝壑,即為“主體的用法”的我賦予某種有機體的對象特征,但是這種凝合是不成功的。我們在日常使用“我”(Ⅰ)的時候,并沒有意味著有個有機體作為被指稱對象,相反,我們在說“我”的時候,并不考慮我是否是一個生物體或有機體。
當代另外一些學者并非如神經科學家一樣提出一種客體主義的自我解釋,而是另辟蹊徑,例如,丹尼特(Daniel Dennet)認為自我是人進化的產物,人形成自我是盲目的和缺乏思想及理解的,是大腦的一種本能和幻象,是由于人類敘述方式發展而產生的敘事重心(narrative gravity),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fit)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比如我們將大腦兩個半球在保留神經聯系的同時放入兩個不同的身體,那么每個身體都可以說它是原始的那個自我。因此,他認為自我和同一性問題無關,而只是與人類的生存問題有關[10]50-64。這些討論為我們討論自我問題提供了更為廣闊和深邃的思路。但是它們依然只是一種解釋,類似于叔本華的意志主體的解釋,而我們理解日常語言的用法之所以具有意義,不依賴于任何解釋,而僅僅在于我們能夠正確的在一定的情境下使用它。
漢斯·斯魯格(Hans Sluga)對維特根斯坦的反客體主義提出了一個質疑。他認為維特根斯坦只指出了自我并非一個對象,這是一個否定或消極性的表達,這里沒有正面的論證,即沒有對“真實的自我”,即歷史、道德、社會中的自我進行討論,從而混淆了“自我概念”與“真實自我”[10]349-350。在筆者看來,這一點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有關,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的功用在于澄清人們由于語言誤用而導致的理智疑惑,就如同醫生治療疾病一般。醫生無法對健康的人提出任何建議,就好像哲學家無法對不患理智疾病的人提出任何建議一樣。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如果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目標是給予蒼蠅以飛出捕蠅瓶的道路的指導的話,那么蒼蠅飛出瓶子后該往何處去,那不再是哲學家的工作。哲學家的工作只在于指出如“我”這類哲學問題中,人們犯下的各種思路上或語言使用中的錯誤,并幫助人們回歸到正常的語言用法中來,而并直接不對真正的人生、道德、歷史問題提供答案。這是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界限所持有的看法,這也使得他遭到了諸如以上提出的責難。
綜上,本文探討了前期和中后期維特根斯坦對自我問題的不同處理。前期維特根斯坦認為自我是界限主體或形而上學主體,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時,“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中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人們在自我問題上受到表面形式的相似性的誘惑而導致各種哲學疑惑,需要通過對語言日常用法的分析來得到澄清。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維特根斯坦前期和中后期自我思想所持有的是一種相通的反客體主義的思路,即指出自我不是經驗對象,這正是哲學家們討論自我問題時容易犯下的錯誤。總之,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維特根斯坦站在語言哲學的出發點,對自我問題這一傳統哲學問題作出推進。
[1]洛克.人類理解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76-83.
[2]羅素.邏輯與知識(1901-1950年論文集)[C].苑莉均,譯.張家龍,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96-200.
[3]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賀紹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4]維特根斯坦.戰時筆記1914-1917年[M].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5]維特根斯坦.藍皮書和褐皮書[M].涂紀亮,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6]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7]HANS SLUGA.Whose house is that?[M]// Wittgenstein on the Self/劍橋哲學研究指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345.
[8]JESSE PRINZ.Wittgenstein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the Self[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11(2):147-160.
[9]內格爾.成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樣子[M]//心靈哲學.高新民,儲昭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05-119.
[10]ROBERT ALLAN.Wittgenstein on Sensation and Self[M]//Master of Art Thesis.University of Calgary,Alberta,Canada,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