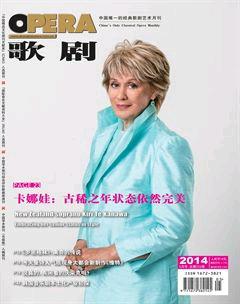20世紀歌劇巡禮
歐南
【歌劇內容】耶奴法是摩拉維亞山區的一個被人收養的姑娘。山區農民拉卡勤奮忠厚,他愛上了耶奴法,并請她幫自己家里干農活,但耶奴法并不理會拉卡的愛情,反而和拉卡同母異父的兄弟,不務正業的斯蒂瓦相愛,并生下一個孩子。耶奴法的養母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痛恨耶奴法犯下了傷風敗俗的事情。為了迫使耶奴法和拉卡結婚,養母競將孩子投入河中淹死。耶奴法屈服于養母的權威,只得和拉卡結婚,后來溺嬰被村民發現,他們以為是耶奴法所為,憤怒的村民想要用石頭砸死耶奴法,此時養母出面聲稱是自己所為。耶奴法也理解了深愛自己的拉卡。
進入到20世紀以后,民族樂派有了更大的發展。隨著西方現代音樂藝術的誕生,民族樂派的風格也和19世紀浪漫主義有所不同。在19世紀的民族樂派中,主要體現的是民族意識的覺醒,而作曲家們也將自己的視野滲入到廣闊的民族旋律中,通過對本民族音樂的挖掘和創造,以喚醒民族的自尊心從而反抗被奴役的命運。
但對于生于19世紀末期,創作活動在20世紀初的民族樂派的音樂家來說,單純對于民族旋律的運用已開始有所變化。在20世紀的藝術活動中,音樂家更關心的是對人的命運做出深度的思考,而不再是簡單的陳述。和20世紀西方音樂一樣,民族樂派的音樂也是復雜的,他們除了仍然扎根在民族音樂的寶庫中以外,對音樂的表達方式也顯得更為精湛和深刻,而從某種方面來講,他們的音樂已經不是單一的民族心聲的體現,而是通過民族化的音樂表達多維的、廣闊的人類世界。
20世紀民族樂派的主要代表人,匈牙利的貝拉-巴托克曾經說過:“以過去和當代西方藝術音樂的普遍知識作為創作的技巧:以新近發掘出來的鄉村音樂一種無可比擬的完美材料,作為音樂的靈魂。”在巴托克的音樂創作中,人們可以看出,它既是民族的,也是具有廣泛的、能引起人類內心普遍共鳴的、深刻的音樂語言。巴托克將音樂深入到人類的精神世界深處,從中挖掘出我們生存世界的真實。在他的獨幕歌劇《藍胡子公爵的城堡》中,他將一個孤獨而殘暴的人類內心世界刻畫得驚心動魄。巴托克的主要創作領域是在鋼琴、室內樂和管弦樂曲中,和匈牙利的另一個民族樂派作曲家科達伊一樣,他們代表了新一代的民族樂派作曲家在探索、挖掘和表現力方面的深化。
命運多舛大器晚成
在民族樂派的歌劇領域中,捷克作曲家雅納切克(1854~1928)是世紀之交時期最杰出的作曲家,他出生在摩拉維亞一個貧窮的鄉村小學教師家庭。他的音樂在生前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發現他作品的獨特價值。和巴托克等人一樣,雅納切克一生也是致力于民族音樂的挖掘和整理。1901年,他和民間歌曲與方言的收集者巴爾托什共同整理出版了兩卷《摩拉維亞民歌集》,其中收錄有民歌多達2000首。
在民族樂派的作曲家群落中,格林卡、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格里格、西貝柳斯等相對為我們所熟悉,雅納切克多少還是個令人陌生的名字,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的情況。
雅納切克,1854年了月3日生于捷克摩拉維亞的一個小村子里,他早年的經歷有些像舒伯特,父親同樣是小學教師兼校長,與舒伯特一樣早年也是因為嗓音美妙而進過唱詩班,也曾一度擔任過小學教師和合唱隊指揮。雅納切克早年的音樂教育正是從唱詩班里學來的,當時的唱詩班除了唱歌以外,還要學習鋼琴、小提琴和基礎樂理等相關音樂課程,而雅納切克的音樂才華正是從這時開始顯露出來。20歲時,雅納切克進入了布拉格管風琴學校開始系統地學習音樂,其后又在岳父的鼓勵支持下去萊比錫音樂學院學習,而他的鋼琴教師溫塞爾曾是門德爾松的同事,這種關系是微妙的,能受教于當代最偉大音樂家的同事,無疑具有激發自己的作用。比如他創作的鋼琴小品集《在簇葉叢生的小徑上》,就有門德爾松和舒曼鋼琴曲的痕跡。1880年,雅納切克又來到了維也納音樂學院繼續深造,在這里他學習了傳統回旋曲和弦樂四重奏的寫作技巧,但同時又熱衷于像德彪西的那種新音樂。而事實上,雅納切克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只待了2個月,在一次學生比賽中,他的一首小提琴奏鳴曲最終落選,雅納切克覺得學校的評委既保守又不公平,憤而退學。
這個事件多少能反映出雅納切克的性格,而他早年坎坷,落落寡歡的命運多少也來自強烈的不擅合作,絕對自我的性情。在經歷了這個事件之后,雅納切克認識到德沃夏克才是自己真正的榜樣,而自己的家鄉摩拉維亞才是自己精神的土壤,他回到了家鄉摩拉維亞最大的城市布爾諾,這正是他音樂生涯起步的地方。
雅納切克早年的聲譽是靠音樂評論起步的。在布爾諾,他寫了大量有關歌劇、民間音樂的評論文章,成了布爾諾音樂評論界的名筆。其間,他除了寫作大量的合唱作品之外,寫下了自己第一部歌劇《莎爾卡》,然而該劇的劇本作者朱里斯·斯耶并沒有同意雅納切克使用他的劇本(或許是捷克另一作曲家菲比赫也寫有同名歌劇的緣故)。所以,雖然歌劇已經寫出,但沒有上演的機會,這使得雅納切克沮喪之極。好事多磨,直到1918年,朱里斯·斯耶已去世了十幾年,官方這才同意雅納切克重新改編上演。
對雅納切克來說,他一生最重要的或許就是在34歲時遇見了捷克民俗學家費朗蒂斯克-巴爾托什。他的倡議深刻地影響了雅納切克,激發了他的民族思想,并改變了雅納切克后半生的創作軌跡。他跟隨巴爾托什來到摩拉維亞地區采集民間音樂和舞蹈,并為之深深吸引。在回憶錄中,雅納切克曾經寫道:“在哈拉皮史的小酒館里,我們觀看農民們變化多樣的即興舞蹈,這就是我的拉什舞曲和胡克瓦爾德民間詩配歌最初構思的來源。”他后來為此寫的管弦樂作品《拉什舞曲》是真正扎根民間音樂土壤的作品,其風格粗獷、節奏強烈。而他的個人風格和特點也在《拉什舞曲》中得以成熟,直到他1894年創作歌劇《耶奴法》時,都帶有《拉什舞曲》的特點。
雅納切克因為反對學院里的權威人物,對自己的音樂有著獨到的見解,故此一生的命運并不順利,直到50歲以后才逐漸確立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并開始被人知道。1903年,他的三幕歌劇《耶奴法》在布爾諾上演后,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聲譽,直到12年以后,《耶奴法》在布拉格上演后才為他帶來巨大的聲譽,但此時的雅納切克已經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真實主義歌劇《耶奴法》
歌劇《耶奴法》又叫《養女》,是雅納切克根據出生于波希米亞的女作家布里埃拉-普列索娃的同名戲劇改編的三幕歌劇。寫作過程長達9年。其間雅納切克的愛女去世,這使得中年喪女的雅納切克痛不欲生,他把這部歌劇題獻給女兒作為紀念,在歌劇第一次出版的合唱總譜上,他寫道:“這是給你的,我親愛的奧爾嘉,讓它永遠留在你的記憶中。”
雅納切克的這部歌劇是他的成名作。和斯美塔那以及德沃夏克有所不同的是,雅納切克的視角始終關注底層民眾不幸的命運和痛苦的生活。雅納切克是世紀之交的音樂家,在創作上無疑會受到瓦格納風格的影響,但他所要表達的不是瓦格納的那種崇高的理想氣質,而是對于人間苦難的同情。
耶奴法是個敢于反抗家庭,并堅持自己愛情選擇的少女,但她畢竟還是被殘酷的現實所吞沒。耶奴法的悲劇是令人同情的,而在這個世界上,弱者的種種反抗終究會被社會所吞噬。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耶奴法》是個社會問題劇,它和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欽斯科縣的麥克白夫人》有著異曲同工的地方,都是為了自己的愛和幸福而反抗社會習俗,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而有所不同的只是《耶奴法》最終還是屈服于命運的安排,她原諒了曾經因愛而傷害過自己的人,不像《姆欽斯科縣的麥克白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伊茲梅洛娃以死來抗拒不公平的命運。
《耶奴法》是一部具有現代風格的、出色的民族主義歌劇,這部歌劇以“真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來描寫,音樂顯得大膽粗獷,有著濃郁的、摩拉維亞的地域性特征。這部歌劇非常特殊的是,音樂的節奏緊密地配合了捷克的民族語言,更突出了它的民族特性,但歌劇的表現手法卻是現代的,它所刻畫的是一出養女耶奴法在愚昧落后的宗法制度下的不幸的悲劇。在作曲風格上,雅納切克成功地運用了散文體手法,使得歌劇在戲劇表現上獲得了更大的空間。有人評論說:“雅納切克是捷克歌劇創作中第一個將劇詞用散文替代韻文的作曲家,從而將他的‘語言旋律曲線在更大程度上運用到了他的這部歌劇創作中去。這種大膽的創新,自然使他進一步將傳統歌劇中的那種生硬劃分宣敘調和詠嘆調的、已經僵化了的格局徹底打破了,最終成為一種獨特的歌劇結構原則。”《耶奴法》不同于一般歌劇的特征是,全劇沒有歌劇中常見的煽情表現,音樂始終緊扣著劇情的需要而發展,他的音樂是服務于人物性格的,不是簡單的取悅觀眾那種膚淺的嗜好而刻意地去渲染,如果說這部歌劇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樸素,作曲家并沒有刻意去批判或者鞭撻宗法社會下人的愚昧和無知,而是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會讓人自己去思考。
雅納切克于1921年上演的歌劇《卡佳-卡巴諾娃》也是一部有關現實主義的悲劇,它的題材來自俄國劇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悲劇《大雷雨》。該歌劇結構緊湊,反映了作者對不幸婚姻和自我譴責的矛盾心態,以及細致深刻的表現與駕馭能力。而改編自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的三幕歌劇《死屋》,則用音樂揭示了犯人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這部小說是一部視覺獨特和苦難的作品,曾經對尼采產生深刻的影響,它真實地挖掘了身陷圖國的囚犯們內心深處的不幸和對苦難的體驗。雅納切克的音樂在描述這種苦難的時候帶著一種人道主義的信念,它在歌劇的總譜上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能煥發出神圣的火花。”表現出他對苦難的同情和對美好事物的信念。
雅納切克是個深刻、嚴肅的作曲家,他的歌劇有著人道主義的因素。但由于民族主義歌劇本身語言的關系,使得他們的歌劇傳播面并不廣。另外,意大利歌劇甜膩的煽情也使得這些寓意深刻的歌劇在傳播上存在先天的不足。但不管怎么說,嚴肅深刻的藝術總是要讓位于好聽易懂、內容淺顯的通俗藝術的。這仿佛是個不容分辯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