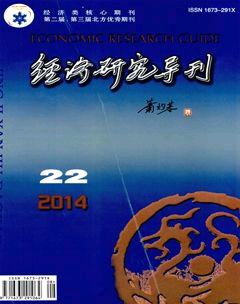論基本權利屬性的環境權與民事權利屬性的環境人格權
摘 要:環境權經常在不同層次上使用,或為應有權利或為法定權利,事實上環境權如果法定化后,只能作為基本權利而無法直接適用于具體的法律關系。在將環境權性質界定在基本權利和將環境人格權界定在民事權利的基礎上,分析二者的不同,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環境權;基本權利;環境人格權;民事權利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2-0298-03
中國學者在理論和實踐中,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將環境權適用于所有的法律關系,尤其是民事法律關系。但事實上,環境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在良好的環境中生存及享有環境人格利益、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但是環境權內容實在太過繁雜,就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環境權以性質為標準,可分為人權性質的環境權和法定性質的環境權,后者又可分為公權性質的環境權和私權性質的環境權。以內容為標準又可分為實體性環境權和程序性環境權,此外,甚至還出現了國家環境權、動物環境權等概念。環境權作為一項權利,其涵蓋內容實在過于寬泛,但是目前對環境權性質的界定上,無論是作為人權還是作為法定的基本權利,都是可以的,但是這兩種界定都不能直接適用于具體法律關系中,在具體的環境人格關系中,發揮作用的是作為民事權利的環境人格權,但是環境人格權與環境權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一、環境權的基本權利屬性
環境權在早期的人權立法中沒有被提及,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使得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達到對抗非常激烈的程度,再加上人類認為自己是萬物的主人,所以在法律上確立的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權利[1],這與環境權所要表達的理念完全背離,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環境權的建立只會束縛人類前進的步伐。顯然,這樣一項背離社會現實的權利是得不到確認的。但隨著人類對自然征服程度的深入,自然最終也不堪忍受,其對人類的報復也開始顯現出來。人類過去錯誤思想的指導使世界固定在一項悲劇性的行動方針中。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不能對環境無節制地開發利用,人類只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1]。良好的環境是人共同享有的東西,失去環境人將不能生存,人也就不再為人。環境權概念就是以人權的名義提出來的[2]。例如,《聯合國人權與環境原則草案摘錄》規定:所有人都對安全的、健康的和符合生態規律的環境享有權利。這一權利和其他人權,包括民事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權利,是普遍的,相互依賴及不可分割的。雖然人權論受到了廣泛的重視,但也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評:概念模糊、主體不確定、范圍不確定、無法具體化、司法實踐困難重重等[1]。所以環境權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具有強制力,其必須法定化,正如赫里曼所言:“人權的神圣名義,不論其可能意味著什么,都能被人們用來維護或反對任何一個事物”,“人權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3]。但是環境權的法定化進程卻要受到一定的阻礙,那就是環境權如需法定化的話,應是由什么層面的法律來對它加以確定,環境權的性質的多層次性,內容的多樣性導致其法定化的進程不可能由某一個具體的法律部門來承擔,環境權的人權屬性也導致其法定的高位階性,所以憲法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即環境權應被憲法所固定,成為基本權利。
二、環境人格權的民事權利屬性
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是不能具體適用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的,要想讓環境權在具體的法律部門中有所作為,即以具體權利面目出現,那就意味著必須在具體法律部門中找到能夠體現環境權理念的權利,環境權在人格權法中的體現,我們稱其為環境人格權,環境人格權是獨立存在的,是“自然人所固有的,以環境人格利益為客體的,維護主體人格完整所必備的權利。”[4]
所以環境人格權不是基本權利,其只是人格權的下位概念,是人格權一部分內容的民法體現,其不能成為一項基本權利,同時環境人格權也是環境權這種基本權利的下位概念,也是環境權一部分內容的體現。所以說環境人格權是人格權與環境權的融合,是這種融合在民法上的體現。誠然基本權利的功能和民事權利的功能是不一樣的,基本權利并不是個人用于對抗他人的工具,而是用以對抗國家權力,免受國家的侵害的工具。同時,國家也應為公民創造必要的條件確保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并隨時調整自己,法院解決糾紛時也應不偏離基本權利的精神。所以基本權利不僅僅是一項法定權利其還具有“客觀法”作用,基本權利整體構成一種價值體系,輻射于整個法秩序。因此基本權利可對民法產生效力,但是這種效力的發揮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呢?目前有三種學說:無效力說、直接效力說和間接效力說,通說采用了間接效力說。這是因為民法是體現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法,是市民社會的法,自主性是其必須遵循的原則,為防止對個人意思的阻礙,基本權利是不能直接適用于私主體之間,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基本權利與民事關系不產生任何的關聯,即基本權利應經由民法的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而適用于私法關系,畢竟基本權利作為價值體現還應對私法進行統攝,而不是漠不關心,只不過這種統攝是間接的,而非直接作為民事關系的安排的法律依據。
人格權和環境權作為自然權利而入憲,不管從理論上說還是從現實法律文本上都已得到證實(雖然中國憲法還沒有將環境權納入基本權利范疇但環境權的基本權利地位已得到多國憲法的承認),所以環境人格權不管是從人格利益享有方面還是從環境利益享有方面都包含在上述兩權利之中,其作為憲法基本權利涉及到的人之生存和尊嚴內容的部分自然應受到憲法保護。但這并不能妨礙其作為民事權利出現。環境人格權客體是存在于人自身的環境人格利益,因具有生命特征而享有(此處還涉及胎兒和具體后代人的法律地位問題),因死亡而消滅。環境人格利益為人之尊嚴地生存而必備,與人之生命、健康密切相連,該權利體現的是對人的關懷,這一點與民法本質不謀而合,應納入民法進行直接保護,僅靠憲法的間接保護是難以為繼的。除了中國沒有憲法訴訟導致公民不能直接適用憲法尋求救濟外,最主要的是憲法作為一國之根本法,是不可能詳細規定各具體權利的,即使人格權或環境權在憲法中的規定也僅僅是宣示性的規定。至于像環境人格權這樣一個屬于人格權或環境權的下位概念,更是不可能詳細規定也不應直接出現在憲法文本中。而且權利的規定不僅是一宣示性規定,其還涉及到權利的救濟問題,正如前面所提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導致其不可能對受害人提供完善的救濟,而且基本權利是用于對抗國家,一般其所涉及的侵權行為往往不直接涉及私人。所以盡管環境人格權內容可以暗含在憲法中,但是要想真正得到實現還需要由民法來加以保障,即環境人格權是一項民事權利,保護的是私益。但是環境人格利益真的是私益嗎?環境具有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物物相關,也就是說自然萬物都是相互聯系,不管某一因素是多么微小,它都會影響到其他萬物[5]。這就導致了對環境人格利益侵害并非只影響到其權利人,還會輻射到其他人(包括后代人)或物,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此環境人格利益并不單純是私益,還具有公共性,是公益。當然由于具體環境人格權類型的不同,有的私益性多一些公益性少一些,有的則相反,環境人格權的私權化也為環境人格利益找到了明確的權利人,這樣也彌補了環境作為非排他性的系統導致的主體缺位進而產生搭便車行為的缺陷,從而使環境利益的保護落到了實處。所以環境人格利益的保護不僅僅是保護私益,也保護了公益。但我們在強調其公益屬性的同時也不要忘記環境人格權畢竟是一項民事權利,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私益,至于公益是其在保護時自然而然產生的后果而非有心為之。所以它是社會性的私權,而非個人性的公權。
三、環境權與環境人格權之間的區別
(一)效力不同
憲法的效力在法律體系中是最高的,其效力是基礎的,不能來自更高法律,所有的法律效力都是來自于它,其本身就是基本規范,是構建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實在法律體系的效力終點[6]。所以基本權利的構成不會像民事權利那樣細致和復雜,可以為人直接引用,基本權利并不能取代民事權利和其他權利,當然其目的也不是為了取代這些具體權利,而是成為民事權利和其他權利的基礎,以自己的價值來衡量具體權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效力輻射整個法律體系。所以,基本權利的效力并不是只發生在國家和自然人之間,也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國家機關與國家機關之間,對法的所有領域都產生影響,所有的社會生活,不管行為是發生在市民社會還是政治國家,都需要在基本權利的基礎上進行整合。
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自然也不能直接適用于具體的法律關系中,所以,環境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所直接依據的不是環境權而是其在民法中的投射——環境人格權,即人在良好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并不僅僅是將環境作為可供人利用的物質資料,“世間的每一物都是人可以在其中發現人性的東西與增加人性的東西的容器”[7],是人之人格的體現。所以環境人格權作為一項民事權利,其法律效力要遠遠低于環境權,它是環境權在人格權法中的體現,被環境權所指導。畢竟環境人格權作為舒適權,本身就存在模糊性,它是人的客觀和主觀感受的統一,而人又千差萬別,盡管采取一般理性人標準,但是特殊人的利益也得兼顧,這都使其不能像物權或其他人格權那樣清晰,也給法官在法律適用中設置了很多障礙,而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其理念可以為法官進行法律解釋時提供指導。
(二)內容不同
環境權作為一項基本權利,是人在良好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而這樣一個宣示性的概念導致其所涵蓋的內容要比環境人格權寬泛得多,包括環境資源利用權、環境人格利益享受權、環境狀況知情權、環境事務參與權、環境侵害請求權等。很明顯這些權利有的屬于實體性權利,包括財產性權利,也包括人格性權利;有的屬于程序性權利,有的屬于本體性權利,有的屬于輔助性權利,所以環境權內容包含了性質、地位不同的權利。而環境人格權的范圍要窄的多,僅包括享受環境人格利益的權利,是實體性本權。
(三)功能不同
盡管環境人格權是環境權在人格權法上的投射,但是不能簡單地將環境人格權看成是環境權在人格權法上的具體化。這限縮了環境權的功能,事實上環境權對環境人格權的影響遠非如此。正如前面所論,環境權是一項基本權利,其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主觀權利和客觀規范。作為主觀權利的環境權針對的是國家,其適用范圍是國家行為要有理有據,自然人可依據基本權利條款要求國家不為一定的行為或者要求國家為一定行為,確保人民的福利,如果國家機關不履行上述義務,那么自然人可以尋求司法救濟。而其中最為核心的功能,即第一種功能,要求國家權力不得濫用,否則人民將有權要求停止侵害。而環境人格權是一項民事權利,其所受到的侵害,更多的是來自私主體,提起的是環境人格權請求權與環境人格權侵權請求權的救濟權,不僅可以要求私主體排除影響權利完滿狀態的侵害或危險,還可以要求財產和精神損害賠償以彌補損失。而作為客觀規范的環境權所發揮的價值秩序的影響,則不僅僅體現在私法領域,其在所有的法律領域都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或者說整個法律體系處處都體現著環境權的身影,處處受到環境權的牽制,也處處以環境權為理念衡量調整著社會關系。環境權對于環境人格權而言,其是強制地施加于其上的價值判斷,環境人格權的適用處處離不開環境權的指導和限制,但環境權在人格權法中的實現也必須依賴于環境人格權這一具體的權利。環境人格權不存在如環境權般高位階的效力,對整個法律體系而言,其并不是一種價值秩序,也不是基礎性的存在,環境人格權僅為一項民事權利,是人們享有人格利益的民法依據。
(四)環境權與環境人格權互為影響
環境權對環境人格權的輻射,在前面環境權的客觀規范功能中已進行了詳述,不管存不存在憲法保障機制,建沒建立違憲審查,都無礙于此種功能的發揮。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可以滲透于民法當中,通過環境人格權來實現其對環境人格利益的保護。當然這種滲透并不是簡單地從上而下,即直接存在這樣一項權利去對應環境權,這只是環境權對環境人格權影響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講,人格權法畢竟是人立的法,由于人之前瞻有限,這導致了許多新的環境人格權類型不可能在人格權法中得到體現,但法院不可以此為借口而推脫此類案件,這并不是說環境權可以直接被運用到具體的實踐中,而是說環境權仍然可以間接地通過人格權保護一般條款去保護這些利益。同時環境人格權也可以影響到環境權在憲法上的確立,也就是說在很多時候,由于憲法的根本性,導致了不管其修正還是修訂都比一般法更為嚴格,也無法輕易啟動,所以很多時候,在很多國家,環境權并沒有寫進憲法中,但在民法當中已經存在了環境人格權,當環境人格權的重要性被廣泛承認后,就為環境權成為基本權利提供了有利支撐,進而獲得最高位階的效力,這也符合了法律發展的規律。
參考文獻:
[1] 張麗君.論個人環境權[J].環境資源法論叢,2006,(00):72-73.
[2] 谷德近.論環境權的性質[J].南京社會科學,2003,(3).
[3] Holleman:the Natural Right Movement,Prager Publishers,1987,p4;沈宗靈.比較憲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馬俊駒,
曹治國.人權視野中的人格權[J].政治與法律,2006,(5).
[4] 呂忠梅.溝通與協調之途——論公民環境權的民法保護[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242.
[5] 張鋒.通往自然之路——人與自然關系和諧化的法律規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38.
[6] [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26.
[7]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G]//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430-431.
[責任編輯 陳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