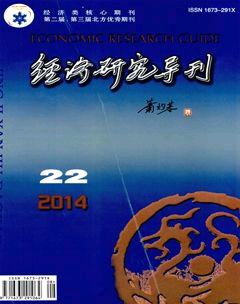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法律困境分析
高蘭蘭
摘 要: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程序運(yùn)作過程中存在著法律困境,分別表現(xiàn)在憲法、綜合性環(huán)境法律、單行環(huán)境法律與環(huán)境行政法律法規(guī)等四個方面。分析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法律困境,將有助于其應(yīng)急管理的法治化建設(shè)。
關(guān)鍵詞: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管理;法律困境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2-0306-02
一般來說,完善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是有效緩解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社會壓力的穩(wěn)定器和減壓閥。目前中國已基本建成了以政策法律體系、組織管理體系和應(yīng)急資源保障體系等三種基本保障要素,以“事前預(yù)防、應(yīng)急準(zhǔn)備、應(yīng)急響應(yīng)、事后管理”為主要程序,以保障環(huán)境安全與大眾健康為中心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一個健全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一定需要一個健全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法律體系作為支撐,才能保證有效應(yīng)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1]。國際經(jīng)驗表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的法治化,不但能夠提高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效率和效果,同時也能夠減少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社會壓力,從而保證公民權(quán)利得到尊重以及公共權(quán)力得以依法有效運(yùn)行。中國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在程序上的相對完整性,較好地保證了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管理需求,但是應(yīng)急程序運(yùn)作過程中的相關(guān)法律體系存在著制度與執(zhí)行上的困境,諸如應(yīng)急法律體系的條例缺損、應(yīng)急執(zhí)法的不作為違法與作為違法、事件主體的責(zé)任追究制度不健全等。就此,筆者將針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法律困境作重點(diǎn)分析。
一、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憲法困境
就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而言,憲法起到了應(yīng)對突發(fā)事件的基礎(chǔ)作用,但是其在應(yīng)急規(guī)定方面也需要有所改善,具體有以下幾點(diǎn):
1.缺乏緊急狀態(tài)的基本要素規(guī)定。自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緊急狀態(tài)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多次。現(xiàn)行憲法是傾向于政治和社會正常狀態(tài)的憲政安排,而對那些非正常狀態(tài)特別是緊急狀態(tài)的憲政秩序問題缺乏相應(yīng)的安排。雖然2004年憲法修訂增加了緊急狀態(tài)的條款,但關(guān)于緊急狀態(tài)的規(guī)定不甚完善,其缺乏緊急狀態(tài)的基本要素比如緊急狀態(tài)的分類等規(guī)定。也正因此,盡管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法律可以依據(jù)憲法中的緊急狀態(tài)條款,但這遠(yuǎn)遠(yuǎn)不夠,從而使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強(qiáng)制應(yīng)急制度在憲法層面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jù)。
2.缺乏特殊適用意義的法律規(guī)定。憲法沒有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發(fā)生時相關(guān)部門的緊急行政權(quán)進(jìn)行明確法律授權(quán),更沒有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強(qiáng)制應(yīng)急過程中所要采取的應(yīng)急措施進(jìn)行明確法律規(guī)定。現(xiàn)行的憲法主要是基于常規(guī)狀態(tài)下的政治社會秩序進(jìn)行法律設(shè)定,從而缺乏對非常規(guī)狀態(tài)下的國家公權(quán)力與公民私利的關(guān)系以及國家公權(quán)力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明確規(guī)定,而恰恰也正是非常規(guī)狀態(tài)下的國家行政主體,需要具有特殊指向和明確規(guī)定的法律授權(quán)。現(xiàn)行憲法采取了最具普遍適用意義的措辭,來規(guī)定國家環(huán)境保護(hù)任務(wù)的法律界限。憲法也沒有明確使用“應(yīng)急處理”等具有特殊適用意義的詞語,對于相關(guān)行政主體的應(yīng)急處置權(quán)僅包括動員和戒嚴(yán)。
3.缺乏針對國務(wù)院和軍隊的應(yīng)急處置權(quán)之明確規(guī)定。憲法中規(guī)定和制約的一般是處于常規(guī)狀態(tài)的政府和軍隊的公權(quán)力以及公民私權(quán)利的法律安排。而當(dāng)發(fā)生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尤其是超局部的緊急重大事件時,非正常狀態(tài)也即出現(xiàn)。隨著事件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原有的權(quán)力制約狀態(tài)與監(jiān)督格局也會發(fā)生變化,此時的政府和軍隊之公權(quán)力將會處于一種非常集中和非常強(qiáng)制的狀態(tài)。政府的這種狀態(tài)在應(yīng)對緊急事件的過程中可能會非常有效,但是由于公權(quán)力的行使必然會關(guān)聯(lián)到公民的私權(quán)利諸如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等等權(quán)利的臨時限制,有時還會涉及到軍隊的調(diào)配與軍需物資的緊急補(bǔ)給,行使不當(dāng)將會導(dǎo)致嚴(yán)重的政治社會后果,因此必須將緊急狀態(tài)下的國務(wù)院和軍隊的應(yīng)急處置權(quán)納入憲政法治中來,并給之廟宇嚴(yán)格的執(zhí)行程序[2]。而中國的環(huán)境保護(hù)應(yīng)急在憲法上的規(guī)定是含糊而不明確的,也缺乏職責(zé)程序的安排。
二、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綜合性環(huán)境法律困境
1.缺乏涉及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具體的應(yīng)急程序。《環(huán)境保護(hù)法》涉及環(huán)境突發(fā)性環(huán)境污染事件的最直接規(guī)定,只突出了事件相關(guān)利益方的應(yīng)急通報義務(wù),但是并沒有給出具體而全面的應(yīng)急原則和應(yīng)急指導(dǎo)方針。并且更重要的是,這部基本法也缺乏關(guān)于環(huán)境污染的預(yù)案管理與風(fēng)險管理,包括監(jiān)測、預(yù)警、信息公開與通報、信息的上報程序、公眾的舉報程序以及事件的評估程序、事件應(yīng)急的合作程序、保障程序、法律責(zé)任等具體方面的規(guī)定。
2.缺乏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構(gòu)的職能劃分。這部環(huán)境保護(hù)的基本法,沒有針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中央與地方各自的職責(zé)進(jìn)行明確的機(jī)構(gòu)分工與關(guān)聯(lián)。這種情況如果是應(yīng)對發(fā)生在國內(nèi)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還力所能及,但面對那些發(fā)生在跨國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將會導(dǎo)致應(yīng)急權(quán)限和程序的法律模糊,從而不利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管理。
3.缺乏部門法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性和統(tǒng)籌性。即使是最新修訂(2014年4月25日)的《環(huán)境保護(hù)法》,仍然缺少對那些當(dāng)突發(fā)性環(huán)境污染事件發(fā)生后導(dǎo)致的公共衛(wèi)生事件和其他公共事件等一系列連鎖事件的協(xié)調(diào)應(yīng)急管理機(jī)制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盡管《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法》具有專門的針對突發(fā)性事件的應(yīng)急處置法律依據(jù),但統(tǒng)觀此法律規(guī)定,大多為方向性和抽象性規(guī)定,可操作性不強(qiáng)[3]。在應(yīng)急管理機(jī)制上,確實規(guī)定了需要建立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綜合協(xié)調(diào)、屬地管理、分管治理和分級負(fù)責(zé)的一套程序,但是對于具體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限和職責(zé)的劃分尤其是中央與地方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限與管理職責(zé)的劃分相當(dāng)缺乏。因此,應(yīng)當(dāng)給應(yīng)急機(jī)構(gòu)相應(yīng)的緊急應(yīng)對權(quán)限,以及對這些權(quán)限的框定和違反權(quán)限所造成的損害結(jié)果的救濟(jì)渠道。
三、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單行環(huán)境法律困境
1.作為環(huán)境污染的預(yù)防治理與公害控制的單行法,《水污染防治法》沒有對傳染病病菌攜帶者污染水體引起公害作出明確的應(yīng)急規(guī)定,而且在這部單行法中,一些原則性規(guī)定不具有水污染危害后果救濟(jì)的操作性。
2.《水污染防治法》作為一個單行環(huán)境法律,其有關(guān)應(yīng)急處理的規(guī)定不夠詳細(xì)。這其中包括中央與地方、地方之間的政府上下級縱向與橫向的職責(zé)關(guān)聯(lián)、應(yīng)急預(yù)案和應(yīng)急響應(yīng)準(zhǔn)備、信息報告制度和公開制度、水污染事件的初步評估以及應(yīng)急事后評估、應(yīng)急工作中的關(guān)系銜接、物資人力與運(yùn)力補(bǔ)給供應(yīng)、疾病控制與救治、社會募捐資金、社會救助、法律責(zé)任的主體確定等各個方面,都缺少相應(yīng)的規(guī)定[4]。
3.現(xiàn)行的各個單行環(huán)境法律,缺乏對流域性的和區(qū)域性的重大水污染事件的關(guān)切。在涉及到這類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工作中,應(yīng)該規(guī)定相應(yīng)的指揮領(lǐng)導(dǎo)機(jī)制、信息報告機(jī)制、物資人力與交通補(bǔ)給機(jī)制等一系列有關(guān)應(yīng)急管理機(jī)制的具體規(guī)定。
4.現(xiàn)行的多個單行環(huán)境法律,缺乏對應(yīng)急法律責(zé)任的明晰。由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主體復(fù)雜,包括事件過程中的所有利益相關(guān)者比如政府部門尤其是環(huán)保部門、事件污染源企業(yè)組織或者公民個人、受事件影響的其他公民和組織,所以應(yīng)急工作中的責(zé)任與義務(wù)也變得復(fù)雜和多元,因此必須有區(qū)別地具體劃分應(yīng)急義務(wù)與職責(zé),從而更好地確定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主體責(zé)任。
四、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環(huán)境行政法律困境
在大量的有關(guān)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環(huán)境行政法規(guī)(包括政府部門發(fā)布的有關(guān)環(huán)境保護(hù)規(guī)章)中,較少有部門與部門之間、法規(guī)與法規(guī)之間的相互協(xié)調(diào),應(yīng)急管理體制與運(yùn)行機(jī)制多存在執(zhí)行分散和制度沖突,不利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處置。比如《國家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急預(yù)案》中作出規(guī)定,突發(fā)環(huán)境應(yīng)急事件發(fā)生后,國務(wù)院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全國環(huán)保部門職席會議協(xié)調(diào)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的應(yīng)急工作,并且各個專業(yè)部門需按照各自的職責(zé)職能劃分做好相應(yīng)專業(yè)領(lǐng)域的應(yīng)對,應(yīng)急的人力物資交通電力等保障部門也需按照各自的職責(zé)職能劃分做好應(yīng)急保障[5]。這個預(yù)案,只是一種指導(dǎo)性預(yù)案,并且是針對所有的包括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在內(nèi)的所有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急指導(dǎo)預(yù)案,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針對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的特殊適應(yīng)性。目前中國的普遍做法是,在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發(fā)生之后迅速成立相應(yīng)的臨時小組[6],這種臨時小組對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處置也只能依靠臨時判斷,缺乏專業(yè)性,缺乏科學(xué)要求。這種做法盡管有一定的效果,但卻割裂了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部門行政法規(guī)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與聯(lián)系,限制了事件應(yīng)急能力的發(fā)揮,影響了政府在應(yīng)急工作中的效率。2005年發(fā)生的松花江水污染突發(fā)性事件,非常明顯地反映了一個單線條的政策制定與執(zhí)行所導(dǎo)致的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效率低下。所以筆者認(rèn)為應(yīng)該更多地賦予地方政府在突發(fā)性環(huán)境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管理權(quán)限[7]。
另外,其他有關(guān)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的環(huán)境行政法律法規(guī)(包括政府部門就環(huán)境保護(hù)與污染方面的規(guī)章制度)也有若干缺陷:其一是基本上還沒有制定一項關(guān)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實施條例或者實施細(xì)則;其二是各個環(huán)境行政法律法規(guī)與其母法存在著規(guī)定上的偏差;其三是各個單行法在有關(guān)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中存在著法律規(guī)范上的相互沖突與矛盾,各自部門又各自另立法規(guī),所以這些法規(guī)一方面具有很強(qiáng)的獨(dú)立性,但在另一方面阻礙了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xié)調(diào),不利于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的應(yīng)急管理。
參考文獻(xiàn):
[1] 魏俊杰.中國突發(fā)性水污染事件應(yīng)急機(jī)制法律問題研究[D].臨安:浙江農(nóng)林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3.
[2] 聶春艷.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對法律制度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3.
[3] 宋麗平,束琴霞,揚(yáng)州.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急法律的完善研究[J].環(huán)境科學(xué)與管理,2013,(11).
[4] 李瑤.突發(fā)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急處置法律問題研究[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2.
[5] 朱光磊,張志紅.“職責(zé)同構(gòu)”批判[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5,(1).
[6] 程同順,李向陽.當(dāng)代中國“組”政治分析[J].云南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01,(6).
[7] 孟玉婷.突發(fā)性水污染應(yīng)對法律制度研究[D].太原:山西財經(jīng)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0.[責(zé)任編輯 陳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