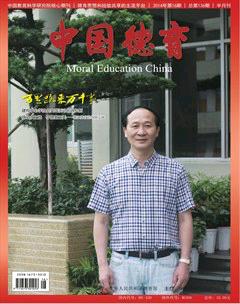課程德育要重視“問題教育”
摘 要 “問題教育”旨在通過解剖“不應當”的道德問題而闡明“應當”的道德要求,讓受教育者明了“正面”的道理。課程德育存在忽視“問題教育”的偏向。課程德育開展“問題教育”,要選好、用好“反面教材”,要將活動德育之“問題教育”內容轉移到課程德育之“正面教育”課堂上來。
關 鍵 詞 課程德育;正面教育;問題教育
作者簡介 錢廣榮,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共十八大報告在闡述“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時,做出“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的專項教育與治理”戰略決策。實施這項旨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的工作,既要著眼于當前,也要立足于長遠。就學校來說,課程德育長期以來存在忽視“問題教育”的偏向,影響了公民道德素質的提高。這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必須重視、進行認真研究和給予糾正的問題。
一、課程德育開展“問題教育”的
必要性與意義
所謂“問題教育”,亦可稱為“反面教育”,是相對于“正面教育”而言的,指的是將道德失范和誠信缺失之類道德問題作為反面教材,并關聯受教育者思想認識問題而開展的教育。當前我國道德領域以道德失范和誠信缺失為主要表征的突出問題,多屬于“明知故犯”,即知之不可為而為之的錯罪。當事者為什么會犯這類“低級錯誤”?究其原因,不能說與其在讀書期間沒有接受必要的“問題教育”無關。
科學的德育應當包括“正面教育”和“問題教育”兩個方面。缺乏“問題教育”的課程德育培養出來的學生,一般知“道”不少,得“道”不多,多是“道德書生”和“道德寶貝”。這樣的學生要成為真正“道德人”,還有待于走上社會后繼續接受道德教化。
學校德育作為一門教育科學,要恪守關懷社會現實和人的發展進步的意義向度,不可回避社會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更不應有意無意地掩飾現實問題的真相。把真實的問題告訴受教育者,并幫助他們學會正確看待這些問題,是課程德育應當具備的科學品質。
具體來看,課程德育重視“問題教育”的必要性與意義,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和認識:
其一,從學理上來看,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道德知識需要正視“道德問題”。在唯物史觀視野里,道德根源于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本質上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恩格斯說:“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經濟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99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1]320。這就是說,道德的根源及其本質特性決定道德的基礎和對象都是利益關系。由于實際生活中的利益關系是普遍的,所以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于是如何面對和處置“道德問題”不可避免成為一切德育的必備內容。科爾伯格的“道德兩難”教育主張之所以會引起中國德育學界的廣泛關注,就在于它反映了德育這一內在要求,將“正面教育”與“反面教育”—“問題教育”合乎邏輯地貫通了起來,并凸顯其間的“問題教育”。盡管,他的“兩難問題”并非都是違背道德的問題。
其二,從優良道德品質形成的演繹邏輯和客觀過程來看,受教育者接受“問題教育”是必備的環節。瓦·阿·蘇霍姆林斯基曾將人少兒時期的發展水準形象地比喻為“人的初稿”階段[2],其寓意顯而易見。“初稿”日益完善而“成文”,必須經過不斷的“補充”和“修改”,“問題教育”正是“補充”和“修改”的必要方式。在這種過程中,受教育者還需要在教育者的指導下應對來自環境中不良因素的“涂鴉”和“篡改”。教育者如果忽視“問題教育”,就不能把握這些過程要素,促使受教育者形成優良的道德品質。
其三,從教育者把握德育課程教材內容來看,教學中補充“問題”內容是必要的。目前課程德育教材的內容記述的道德現象與社會生活中實在的道德現象,并不是同一種性質和意義的現象:前者是“純粹理性”,后者是“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總是真善美與假丑惡同在,“道德人”與“不道德人”同處。而我們的學生就在“生活世界”之中,所見所聞的道德不同于書本記述的道德。教育者在實施課程德育過程中,如果不能增加相關“問題”內容,學生獲得的道德知識和理論就是片面的,就難以全面理解和把握社會和人生,也難以正確認識和看待自己。這種反差,是學生出校門后把知識“還給老師”的主要原因。
其四,從素質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來看,優良道德品質結構中應當包含必要的道德能力和道德經驗。“做事”需要必要的能力和經驗,“做人”是否也需要相應的能力和經驗?回答是肯定的。有的人道德選擇為什么會“力不從心”或“適得其反”?有的學生在公共生活場所見義勇為為什么會反被誣為肇事者?原因與缺乏一定的道德能力和經驗不無關系。這種能力和經驗的培育,同樣需要課程德育開展“問題教育”。
目前學校德育實效性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學校德育不盡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學校德育自身來檢討,不能不說與作為主渠道的課程德育輕視以至忽視“問題教育”存在某種必然性的邏輯關聯。《禮記·學記》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長善”若可基本上稱為“正面教育”,那么,“救其失”則是“問題教育”。今天的課程德育,應當傳承古人的這條重要經驗。
二、課程德育忽視“問題教育”的
認知歸因
一是教育者沒有真正認識和把握德育課程與智育課程在“解惑”上存在的差別,只是按照智育課程的范式來進行德育課程的教學。通俗地說,德育課程的“解惑”是幫助受教育者理解與“做人”相關的問題,智育課程的“解惑”是促使受教育者把握與“做事”相關的知識。如果忽視這種根本性的差別,自然就會忽視課程德育需要面向道德現象世界的“問題”開展“問題教育”。
二是誤以為“正面教育”就是“正面傳道”。其突出表現就是直截了當地傳授課本上的道德知識,講如何做人的大道理或古今中外道德榜樣的高尚品質,由此造成目前德育課上講本本、課下背本本、考試考本本的情況。須知,“正面教育”的主旨是“講正面”,“講正面”既可以“正面講”,也可以“反面講”亦即“問題教育”。“反面講”的“講正面”,就是要通過對“反面教材”的“解惑”,辨析和彰顯“正面”的“做人”道理。
三是誤用教育平等和民主的原則。其表現就是以為平等待生、實行課堂教學民主,就是“不得罪學生”,于是放棄嚴格要求學生,甚至不敢輕易批評和責罰學生。據說,在一個小學德育的課堂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有個學生在課堂叫嚷,老師說:“你要是不愿聽就給我出去!”那學生回嘴道:“你要是不愿講,就給我滾!”學校對此學生并未做處理。應當說,這位老師教育方法是不可取的,但學校對這個學生聽之任之、沒有就此進行“問題教育”,也是有失偏頗的。這里所體現的并不是師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原則,而是放棄了利用德育課進行“問題教育”的一次難得機會。所謂“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學生的老師”的德育觀,實際上是把德育本身的局限性和難免的缺陷全部歸咎于老師,恰恰是失之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原則的表現。
四是混淆了必要責罰與體罰的界限。在日常德育工作中,我們反對體罰有過錯的學生,因為這樣做會損傷學生的身心健康,于教育無益。但是,不可因此而一概否認責罰有過錯學生的必要性。對那些因缺乏起碼責任感而犯錯的學生,更應作如是觀。人的本質特性決定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馬克思說:“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3]責任感是人的一切優良品德的基礎。讓責罰型的“問題教育”進課堂,真諦在于通過理性辨析教育學生要對自己的過錯行為負責,培育學生的責任意識,這正是“做人”的根本所在。
三、課程德育開展“問題教育”的
基本理路
首先,要明確“問題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問題教育”旨在通過解剖“不應當”的道德問題而闡明“應當”的道德要求,讓受教育者明了“正面”的道理。換言之,“問題教育”的“反面說”是為了達到“說正面”的目的。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問題教育”也是一種“正面教育”或是“正面教育”的應有之義,兩者的德育宗旨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必要的“問題教育”在多數情況下可以讓學生刻骨銘心,培育和增強學生對于“道德失范”和“誠信缺失”的免疫力,教育效果尤佳。之所以如此,可能在于主體的內心信念。沒有接受過“反面教育”的人,多不可能養成敬畏和尊重道德規則的內心信念,社會不能依靠這樣的人營造良好的道德風尚。從貫徹和實現德育的宗旨看,科學的課程德育應當把“正面教育”與“問題教育”貫通起來,使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其次,要選好、用好“問題教育”的“反面教材”。課程德育的教材沒有寫進“問題教育”的內容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課程德育的實施過程不能沒有“問題教育”的內容。這里,選好、用好“問題教育”的“問題”最重要。這樣的“問題”有三類:一是實際存在的道德問題,包括現實社會生活中道德領域存在的反面問題;二是學生成長過程中實現道德品質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的問題;三是學生對這兩類問題在思想認識上存在的問題。選用的“問題”要少而準,富有典型的教育意義,切合不同階段學生的理解力。“問題教育”的關鍵在用好“問題”,即通過老師的分析和講解達到“正面教育”的目的。因此,開展“問題教育”也應防止把“問題教育”變成“問題展覽”,否則會適得其反。
最后,要將活動德育之“問題教育”內容轉移到課程德育之“正面教育”課堂上來。目前,我國學校德育一般都比較重視活動德育和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反面教育”,這種做法已經成為一條重要的經驗。然而,卻不能將相關的“問題教育”合乎邏輯、恰當地轉移到課程德育課堂上來,在“正面教育”中分析和理解對問題案例進行“反面教育”的必要性和意義。同時,也可以讓課程德育的“正面教育”走進活動德育的“問題教育”,在“反面教育”的過程中辨析、重溫課程德育之“正面教育”的道理,深化和強化“正面教育”的效果。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蘇霍姆林斯基.關于人的思考[M],尹曙初,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7.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9.
責任編輯/劉 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