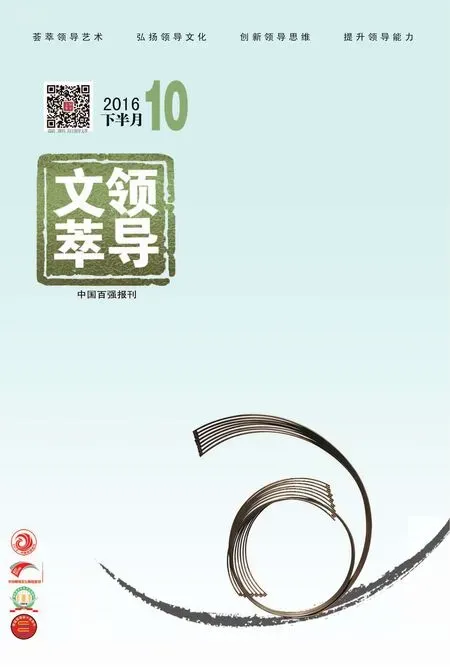中國如何建設(shè)性地平衡美國?
鄭永年
美國“重返亞洲”急劇地改變著亞洲國家間的關(guān)系。無論是中美兩國關(guān)系,還是中美兩國各自和亞洲各國的關(guān)系,都呈現(xiàn)出一種要陷入國際關(guān)系史上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趨勢(shì),即中美兩國之間的惡性戰(zhàn)略競爭。
這個(gè)悲劇注定不可避免嗎?也不見得。美國“重返亞洲”,改變了一些和中國有主權(quán)利益糾紛的亞洲國家對(duì)美國的期望值,使得這些國家和中國的關(guān)系遽然惡化,或大或小的沖突似乎變得現(xiàn)實(shí)起來。不過,中國一旦和亞洲國家,尤其是那些和美國有結(jié)盟關(guān)系的亞洲國家發(fā)生戰(zhàn)爭,美國的卷入或者不卷入,都會(huì)成為美國的難題。不卷入,美國在亞洲甚至全球的信譽(yù)必然受到嚴(yán)重的損害,導(dǎo)致美國的加速衰落;卷入,美國就會(huì)冒著和另一個(gè)核大國發(fā)生戰(zhàn)爭的風(fēng)險(xiǎn)。一邊是和其同盟的關(guān)系,一邊是和一個(gè)它視為潛在競爭者甚至敵人、但仍然需要合作的中國,在這兩者之間,美國是很難中立的。
這表明美國的“平衡中國”戰(zhàn)略本身需要被平衡。一旦美國“重返亞洲”戰(zhàn)略使得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之間關(guān)系失衡,美國就會(huì)面臨沖突和戰(zhàn)爭的風(fēng)險(xiǎn)。既然美國“重返亞洲”的戰(zhàn)略是來平衡中國的,也只有中國才有動(dòng)力和能力去“平衡”美國。中國是否能夠發(fā)展出有效的“平衡”美國手段,既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自我防衛(wèi),也決定了中國能否繼續(xù)維持亞洲和平。
在全球“再平衡”美國
美國“重返亞洲”強(qiáng)化了中美兩國之間,及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關(guān)系。但如果中國戰(zhàn)略和政策得當(dāng),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間的公開對(duì)抗和沖突。可以預(yù)見,中美兩國會(huì)在亞洲進(jìn)入相當(dāng)長一段時(shí)間的對(duì)峙局面,因此也是相互磨合的時(shí)期,但公開的不對(duì)抗和不沖突是可以實(shí)現(xiàn)的。這是由幾個(gè)重要因素決定的。
第一,中國并沒有像一些國家所說的那樣,具有強(qiáng)烈的擴(kuò)張野心。中國根本沒有像二戰(zhàn)前的德國、日本那樣的擴(kuò)張計(jì)劃,更沒有像蘇聯(lián)帝國和美國那樣的稱霸全球的計(jì)劃。中國只是想維護(hù)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國在這些核心利益問題上沒有多少妥協(xié)的空間,中國仍然在盡量保持伸縮性。
第二,美國本身力量的變化有效牽制著其“重返亞洲”的程度。實(shí)際上,美國不了解中國,其“重返亞洲”戰(zhàn)略是建立在其高度意識(shí)形態(tài)的國際關(guān)系理論之上的。從長遠(yuǎn)來看,“重返亞洲”是冷戰(zhàn)后美國最重大的戰(zhàn)略誤判。
第三,一些國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國具有主權(quán)糾紛的國家),需要很長一段時(shí)間才會(huì)意識(shí)到和美國“站邊”的成本。中國現(xiàn)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并且和亞洲國家之間發(fā)展出了相當(dāng)高的互相依賴程度。和中國的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對(duì)這些亞洲國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舉足輕重。隨著中國內(nèi)部消費(fèi)社會(huì)的建設(shè),中國經(jīng)濟(jì)對(duì)亞洲國家的重要性還會(huì)繼續(xù)增加。也就是說,在經(jīng)濟(jì)方面,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外交資源可以動(dòng)員。
第四,無論中國還是其他相關(guān)國家的政府作怎樣的努力,在很長時(shí)間里,無論是東海還是南中國海,主權(quán)糾紛將長期存在下去。只要中國沒有擴(kuò)張野心,也就是沒有把美國擠出亞洲的計(jì)劃和行為,美國不會(huì)公然代理一個(gè)亞洲國家而對(duì)抗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是有能力來管控主權(quán)問題的糾紛的。
避免軍事競賽持續(xù)經(jīng)貿(mào)合作
在亞洲,要達(dá)到平衡美國的目標(biāo),中國要兩個(gè)戰(zhàn)略平衡進(jìn)行。
第一,中國必須避免和美國的軍事競賽。換句話說,在軍事上,中國能夠維持在防守和威懾程度就已經(jīng)足夠了。
第二,中國需要根據(jù)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線,繼續(xù)把重點(diǎn)放在經(jīng)貿(mào)合作上。但中國必須改變從前只講經(jīng)濟(jì)不講戰(zhàn)略,或者經(jīng)濟(jì)和戰(zhàn)略不相配合的情況。
要建設(shè)性地“平衡”美國,中國也要在亞洲之外的其他地區(qū)開辟新的領(lǐng)域。戰(zhàn)略“走出去”符合中國國內(nèi)可持續(xù)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要。一旦中國戰(zhàn)略走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區(qū),中國就可以有效減輕在亞洲,尤其是在東亞和美國競爭的激烈程度。為了“重返亞洲”,把戰(zhàn)略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亞洲,美國在其他區(qū)域必然要進(jìn)行戰(zhàn)略性撤退,這就為其他大國提供了巨大的戰(zhàn)略空間。中國戰(zhàn)略進(jìn)入這些地區(qū),扮演有效角色,就是說中國和美國同樣,和這個(gè)國際秩序變得相關(guān)了。中國和美國的互動(dòng)就不再局限于亞太地區(qū),而是具有全球性質(zhì)。這樣,和美國的合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平臺(tái)。
并且,中國是有能力建立一個(gè)不同于美國的區(qū)域秩序的。中國的“走出去”戰(zhàn)略行為不可避免被西方指責(zé),例如被視為是新殖民主義。但從另一個(gè)側(cè)面來說,這是中國的強(qiáng)勢(shì),因?yàn)橹袊龅暮臀鞣阶龅牟灰粯印1M管中國要不斷改善自己的國際經(jīng)濟(jì)行為,但并不用過于害怕西方的指責(zé)。只要中國的確是為了促進(jìn)那里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并且無意把自己的政治秩序加于這些社會(huì),中國的外交模式最終會(huì)被那里的人民所接受。在這個(gè)過程中,美國會(huì)越來越感受到中國存在的不可或缺性。那個(gè)時(shí)候,中國就有了和美國合作的資格和機(jī)會(huì),也具有了迫使美國“合作”的能力。
簡單地說,中國和美國全球范圍內(nèi)的接觸政策,可以轉(zhuǎn)化成為中國“平衡”美國的有效政策。全球性接觸不僅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后院(亞洲)演變成為戰(zhàn)場,更可以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gè)真正的大國,一個(gè)有責(zé)任感又有能力履行責(zé)任的大國。
(摘自《新華月報(bào)》)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