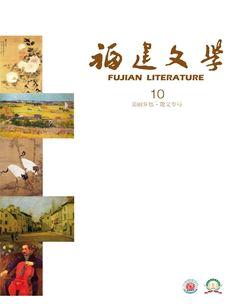耕地夢
張平
我們家的田
我和七十多歲的母親到野地摘草莓,路遇田地,母親指著說,這是我們家的田。
田?我們家的田?我忽然被什么扎了似的,多少年了,我早忘了自家田地的位置。何況村莊的田地隔過三年五載重新劃分。田?我循著母親手指的方向,那兒種著煙葉,煙葉田田,長得像茁壯的小屁孩。
沿田埂走了幾分鐘,母親手指著另一處方向,說,這也是我們家的田。我看那田地的禾苗,剛栽下不久。母親告訴我自家的田承包給了誰,在她說話的間隙,多少農事浮現眼前。
田?自家的田?是的,我是在哪會兒學著怎樣將一行行的禾苗栽下?我記得最早栽禾苗的年紀,是在讀五年級時,母親說我長大了,要幫助家里做些勞力活了。那個火熱的夏天,我將小腳丫插入水中,刺疼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你是農民的孩子,哪有不要學做農活的?”起初,我拒絕這種刺疼,父母親的話語激蕩在耳際,在夜深的村莊,這話語又似一根針扎在我的幼小的心靈。農家的孩子一定要干農活嗎?母親,以及村里的“鄉巴佬”,都說,要不做農民,就要努力讀書啊!
讀書可以不做農民,我當然深信不疑,那個時候,村莊還沒有一個中專生,大學生就甭提了。方圓幾十里的小鎮要是有誰家的孩子考上中專,消息就會在相鄰村莊間奔走。我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附近的一個村里一位農家孩子考上了大學,小鎮轟動了。我也因此失眠,一個小小年紀的失眠有時是無力的,我繼續干著農活,學會了手持鐮刀,在稻谷間穿行。我和大人比賽割稻,那揮鐮的麻利動作,我現在回想,若不是當年考上師范,我一定是個標準的農民。
不過,初次揮鐮,免不了被鐮齒刮傷,當鮮血從指頭滴下,我年少的身體又做怎樣的感嘆?哭泣過后,我繼續勞作,從此,我學會了咬牙,一個人不可能凡事一帆風順,咬牙會使人變得堅強。
也難怪我遺忘了自家的田,如今的生產方式,半機械化,插秧,除草劑,收割機,這些程序簡單,鄉親的頭腦也簡單了,風吹日曬的次數少了,也少了那瘋狂的勞動場面。
什么瘋狂的勞動場面?我憶起村莊有兩個著名的強勞力,他們身體強壯,高大,雙搶季節,晌午田野快餐,迎著毒日頭加班加點,我如今遇到他們兩位老人,背比別人更駝,膚色更黝黑。
“拼命是為了賺工分,分紅才多啊!”耳畔起伏著這樣的聲音,我沿著歲月的溝渠走向更遠。那時,我母親是代課老師,父親在村部混了個民兵營長,勞力都不強壯,代課工資,以及村里的收入也不高,所以我家赤字是常有的事。我們家有自己的田,父親和母親也更辛苦了,請人幫忙,雇些小工當然需要,不過,田間事自己打理才細心,哥哥、姐姐下地的時間比我和弟弟多得多,我知道他們被針扎的疼痛。
田?我們家的田?我疑問,弟弟弟媳常年在外做事,十幾年以來,它被人承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淘金熱,很多鄉親外出打工,我們家的田也曾荒蕪,這幾年一直承包給一戶親戚,一年租金二千多元。
早年父親還在沙地開墾幾畝荒地,不過,河岸經常遭遇洪水,誰也不敢保證莊稼不被破壞。所以,一年田租只需上交幾百公斤谷子。那片沙地具體在什么位置,我從來不知。
回到鄉間,一個人仿佛長了翅膀,而且想將翅膀無限擴張,很多淳樸的東西在記憶里丟失了,回到了鄉間,那些黑白分明的線條——犁的線條 ,田墾的線條,枝條的線條,云朵,大地的線條在提醒你,在灼熱你。那就是我的根啊!
我仿佛想起來了,可是,當我的車子,遠離村莊,村莊又是一團模糊的影子。那些我正憶起的,又擱在幽暗的河岸。
耕地夢
父親和唐叔在田埂悠然地吸著紙煙,我卻不停地喊:犁被卡住了,犁被卡住了。
他們倆聽后在暗自竊笑,唐叔向著我逗樂:好樣的犁手,想辦法呀!
我使勁扳動犁手,蹲下身去扒開犁尖的泥土,無濟于事。我于是坐在翻過的泥塊,撒手不干了。父親似乎還停頓了一會兒,甩掉了煙頭,走過來。
“犁把要抓牢,線條要直,就輕松了。”父親自言自語,我知道是說給我聽的,那會兒,我正呼吸著泥塊清新的氣息,也沒有正眼瞧父親。父親也是偶爾在吸煙歇息的一會兒,叫我操作,一個高不過玉米稈的孩子怎么會犁田呢,這是大人的活兒呢,我才不管呢!
父親還經常這樣教育我,他認為一個農民孩子從小就要學干農活,學握緊農具,否則長大了再學,就會延誤農事。父親在犁田時,也是有意無意讓我操作,一個孩子又怎會知曉他的良苦用心?
我瞧我操作的犁痕,幾步見方,歪歪扭扭的線條,我想一塊水田要是可以用直尺鉛筆描繪,我當然可以讓春天的線條筆直,讓春天的田野小花朵朵。
犁田的事兒跟我有什么關系?我心里嘀咕,我學握犁把,跟在牛屁股后得瑟,我是好玩呢。我扶著犁把,驅趕水牛,像是一列隊伍的軍官,在指揮一場戰斗。那犁不是在我的手中,是在我的筆下,和那色彩渲染的春天一樣在我的筆下,我的尖利閃亮的犁刃劃過的是時光新鮮的一頁。
你看,我跟在父親的后面,翻閱更新的土塊,吸引我眼球的是泥鰍,我的竹簍在不斷地盛入,這才是我的收獲啊!我勞動的間隙,我追趕蜻蜓,田野舞蹈的蜻蜓帶我闖入另一片天地。唐叔和父親的對話早已被我拋諸腦后。
有時,我似乎也感悟著什么,我注視一壟壟整齊的土塊,父親的腳印是那樣清晰,這是農民清晰的腳印,嵌入土地。我坐在水溝的一側,輕風拂過青草,我放牧的牛兒在低頭咀嚼,偶爾,它也側耳傾聽,長長地哞一聲。
犁把要抓牢?怎樣才牢?唐叔他們扛著犁把,牽著水牛悠然走在田間小路,那東西我視它是一座小山。我不是沒有試著抓牢它,我將肩膀湊過去,想一把頂起,它的鋒利卻穿越肩頭。
我漸漸明白了一個人成長的道理,一個農民的孩子肩頭就是要有尖利的東西在穿越。
一片田野只有尖利在穿越,一片田野才會遼闊,碧浪才會翻滾。讀初一時,我跟父親到田間勞作,我已初步掌握了犁田的要領。不過這些都是遙遠的事了,唐叔也很少回到村莊,當年生產隊里的勞動標兵,乘著兒子開的奔馳回到故鄉的他,早已把犁鏵甩掉了。
只有我在一片茂密的煙地尋找嗎?水牛長哞的聲音在暗處傳來,我知道我的心靈還保存著淳樸的線條,風止息的夜里,我經常在夢中耕地作畫,歪歪扭扭地抵達。
一次,我在豬欄一側看到彎身的犁具,雖然不完整,犁鏵的尖利早已遲鈍,銹色占領的時光在隱藏,我心靈的線條卻無比清晰,像父親的田間的腳印,我忽然想到對話的朋友,對!滄桑的犁鏵就是一位從未謀面的朋友,擱淺的船槳。然而,稻花搖曳在它的田地,它隱藏在一個角落,獨自耕作,獨自栽下禾苗,含苞,揚穗。
父親也老了,像極了一張犁。我到自家的田地走訪,一位親戚在摘煙葉,他承包我們的田多年,我遺忘了自家的田,更遺忘了原始的耕作方式。
遺忘癥的人何止我一個?我彷徨村莊的山水間,我還能看到一位肩上扛犁具的鄉親嗎?耕作的方式在轉變,那些時光里的印跡也只是一個舊符號,沒有線索勾起往事的火苗,那些人事就被風吹散,或是埋沒。
烤煙房的夏天
烤煙房在村完小旁邊,我手臂再長一些,我從我的木窗伸只手去,就可以觸摸到它們笨拙的身體。
一座座烤煙房比鄰,像幾位木訥的鄉親,蹲在村莊的一處田間地頭,用眼神交流,借風語表達。這是秋涼的時候,烤煙房勞累了,歇息了。我從木窗向外凝視,它們像一片沉重的葉子擋住我向遠的視線,看著它們,火熱的炭粒沒有熄滅,灶膛里的火光在跳躍。
于是,夏天沒有消逝,深居烤煙房的身體。
“老師,來一支煙?”農民很懂禮,看到我窗前的影子,喚了我一聲。我道了一聲謝,說不吸煙。他點燃煙,就把頭朝向灶膛,夜色中,火光映照的臉蛋特別明亮,古銅色的肌膚愈顯農事的操勞。
我喜歡打開夜色,在夜色中安靜地閱讀寫作。有時,幾個農民也會小聚一會兒,說笑,但不粗聲,大概怕影響旁邊睡眠的老師,他們把聲音壓得很低。
“今年的煙葉價格也不知怎樣,洪水沖毀了一些煙葉,聽說煙葉站會給予補助。”聽到他們的心語,接近生計,接近一個一個現實的夢。煙農的辛苦他們卻沒有言說,我知道一到煙葉采摘季節,他們一家大小忙得夠嗆,采煙葉,挑煙葉,最關鍵最勞神的是烤煙葉,我在村完小的那幾年,烤煙還是最初的作坊,沒有控溫的技術,所以,農民烤煙時,不能打瞌睡。怕小睡忘了翻煙葉,烤焦了,這樣煙葉的價格低廉,煙葉站還有可能不收購。
夏天炎熱,村莊白天的氣溫有時高達三九、四十攝氏度,夜里暑氣難以散去。烤煙的農民大都赤膊,豆大的汗粒不斷從他們身上流落。經常在早晨,我向窗外看去,烤煙房旁很多散亂的煙頭,胡亂臥倒的啤酒瓶,我知道他們是借酒借煙提神。
有幾次,我透過夜色和他們對話。他們羨慕我有固定的工作,我說老師的工資不高呢,清水衙門。他們說好呢好呢,然后伸出還沒有退下褲管的小腿,看,還沾著泥巴,沒空洗呢!
灶膛的火光照著他們沾著泥巴的小腿很清晰。
烤煙房飄來煙葉的香,在夜色中,那香誘惑著時光嗎?我在安靜地寫詩,一個夏天的星空在筆下那么遼闊,而哪一顆星星點的憂傷在透露?烤煙房劇熱地勞作,一刻也不停歇,在低吟的音響,我拆散村莊的人事,他們都是一個個無聲的孤獨的身體。
夏天的烤煙房就這樣嵌入我的靈魂,這么多年,我在小城。我依然清晰浮現村完小旁的那一排烤煙房,我想它們豎著的身體也是一株一株村完小的苦楝樹,立在風雨中。
拾稻穗的小矮人
提著竹籃,籃子里裝著幾塊熬熟的地瓜,地瓜香飄散,隱隱地穿越田埂。你看,那個矮小的影子走過去了,嘴里好像還嚼著什么,那個矮個子是誰?
是我啊,正幻想地瓜香,狗尾巴花的香,稻草的香沁人心脾,晃悠在田埂,真是有無數隱隱約約的香在進入身體的隧道。這樣的下午是輕松的,課本拋到九霄云外,我只捎帶美術紙頁,在浸染田野的色彩,這是心靈深處的美術紙,空白,空曠。
有三兩個伙伴,在田野也是輕松的,你看,他的口袋里還藏著黃豆的香。媽媽午餐時炒的。你把地瓜給我。下午的聲音很細微,也深入劇本,幾個小矮人彼此在交換,那會兒,他們正坐于田野一處轉角,敞開音箱,又秘密地行動。
這樣的日子,我又怎樣會忘卻?偷懶的一個小伙伴提議,干脆我們就藏在草間。
藏在草間作啥?偷稻穗呢,看他們用手掌麻利地搓碎谷粒,我的心兒卻有些發慌,老師囑咐的聲音從講臺延伸到田野,我的耳根也似乎有被什么東西灼熱。違反紀律呢,我說。
我給你一把豆子,一個小矮人說。
豆子可以堵住嘴巴嗎?
其實,他不用豆子交換,我也不敢揭秘,我這個老實人,在班上,看到同學吵架,腿就會發軟,他們要真干起來,我只有在心里十次百次地勸架。
我還是彎身做一只勤勞的螞蟻,在搬動谷粒,田間散落著很多谷穗,我細小地撿拾,我這只勤勞的螞蟻又未必受到老師的表揚呢。
那幾個藏在草間,胡作非為的,竹籃盛滿,口袋也盛滿。他們大搖大擺地將果實在老師的眼皮底過秤。
害臊!我心里不服氣,也在嘀咕。然而,我不敢告狀,有時害臊也是說給我自己的呀,一個隱瞞事實真相的人,他也有我這樣回憶,我喜歡這樣的過程,仿佛一個衰老的人瞬間變成小矮人,一個小矮人多好啊,可以藏在草間。身體是輕的,大地是輕的,時光也是輕的,而幻想的竹籃卻在盛滿,不斷地盛滿。
我也喜歡一個人獨自提著竹籃,在曠野呼吸,課本是那樣重啊。你想,一個人挎著沉甸甸的竹籃行走在夕陽的金色的光線中,身體有怎樣的金色?
多年以后,我在村完小任教,我清晰地記得老師宣布拾稻穗通知時,課堂的一片嘩然,他們作鳥獸狀,擁著老師,說老師真棒,他們提著竹籃,藏在草間,狗尾巴花扎你的臉蛋,誰的時光有這么愜意。
隱瞞真相,我的身體當然知道真相的過程。我還憶起,這些懶惰的小矮人,還利用拾稻穗的時間,騎牛賽跑,我還知道他們還干著另類的惡作劇,老鼠逃跑,他們仿佛堵住了老鼠天下所有的小路。
你看,他們揮著鋤頭,在悄悄地破壞田埂,他們在捉田鼠呢,夕陽里,他們的竹籃盛下的是著瞪眼珠子的田鼠。
我敢揭露真相嗎,捉田鼠,有時,我也是隊伍中的一員,一個個矮個子,怎能誘惑得住田野激蕩的風?
責任編輯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