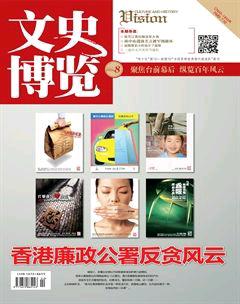“腳踢蔣介石”系演繹
父親在世的時候,很少談個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親過世后母親告訴我的。這幾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憶錄,還有他在“反右”期間寫下的兩份檢查,對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現在很多人談到父親,都把他當作一個傳奇。關于他的很多傳聞,都帶有虛構編造的成分,是后人演繹出來的,并不符合事實。我想說,父親確實有特立獨行、有骨氣的一面,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平常人,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靠一部書可以留名五百年
我祖父叫劉南田,早年在合肥做布匹生意,小時候遇到“長毛”(太平軍)攻打合肥,家里人就用布匹將祖父吊下城樓,躲過一劫。“長毛”走了以后,祖父回到合肥,重操舊業,家里經濟又好了起來。
祖父共有子女八人,六男二女,父親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父親生前沒有談過太多家里的事情,因此也不太清楚他的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連他自己的出生年份都說法不一。
現在比較常見的說法是,父親生于辛卯年(1891)。這一說法依據的是北京大學胡適、周作人等很多名人的回憶。父親27歲到了北大,當時北大有好幾個屬兔的人,父親和胡適、劉半農因都生于辛卯年,因此被并稱為北大“三只小兔子”。
父親是個非常好強的人,在北大,擔任預科教授,為了提升名聲,他開始發憤搞《淮南子》的校勘。這是很苦的差事。聽我母親說,父親經常從晚上9點開始工作,然后搞到天亮才睡覺,從來不吃早飯。
這樣做了一年多的時間,總算把《淮南鴻烈集解》做出來了。這本書出來后,受到了很高的評價,當時在學術界如日中天的胡適親自為之作序,而且做的還是文言文的長序,要知道那時候胡適正在提倡新文化運動,主張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由此可見,胡適對于父親這本書的認可。
父親曾經說過,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成就,他這一輩子,靠《淮南鴻烈集解》這部書,估計可以留名五百年。他后來還做了《三余札記》《莊子補正》等書,都非常有影響力,尤其是《莊子補正》,陳寅恪先生親自為之作序,并稱贊這本書“一匡當世之學風”。
現在很多人說他“狂”,其實他并不是“瞎狂”,他的“狂”是有依靠的,就是他的學問。他一輩子,似乎就是跟學問打交道。我記得他曾經在家里門上貼過一張條子,“來閑談者,恕不接待”,他不太關心人情世故的東西,心思都在做學問上。
“腳踢蔣介石”系文人演繹
關于父親的為人,現在的人說得最多的,就是他頂撞蔣介石的故事。關于這段往事,說法很多,有的到了幾乎離奇的地步,比如說他“腳踢蔣介石”,其實這是沒有的事情,完全是后人演繹出來的。
父親在北大做了《淮南鴻烈集解》以后,名聲逐漸大起來。1927年,安徽省政府邀請他回皖籌辦安徽大學。當時省里也沒給多少錢,但父親覺得作為一個安徽人,給家鄉教育做點事是應該的,因此到處奔走,找財政部要錢,聘請名師,租借校舍,總算把安徽大學的框架拉起來了。
結果,開學沒多久,就發生了學潮。事情的過程其實很簡單,1928年11月23日,安徽大學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舉行十六周年紀念會,下午5點多鐘,參加紀念會的人正在學校膳堂聚餐,突然闖進一批安徽大學的學生,說是受到邀請,要來女校參加晚會。結果,雙方就沖突了起來。
安大的學生血氣方剛,不僅砸了女校的桌椅,還打傷了學校的女仆。女校自然就告到了省政府。這時候,剛好蔣介石到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視察,聽說了這件事情,就把父親和女校校長程勉喊去,詢問內情,并要求嚴查。
作為安徽大學的實際負責人,父親到會后堅稱此事“有黑幕”,不愿嚴懲學生,結果惹惱蔣介石,直斥父親為“新學閥”。而父親也不是省油的燈,回罵蔣介石是“新軍閥”,遂被扣押。
據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石慧廬回憶,現場頂多是父親“把腳向下一頓”,結果就被后人演繹出了“腳踢蔣介石”,夸張過頭了。
這件事情發生后,我母親馬上向陳立夫、胡適、蔡元培等人求援。蔣介石那時候還算比較尊重知識分子,很快就同意放了父親,并允許他繼續回到北大任教。
所以,我六叔劉天達說過,父親不是當官的料,很難搞行政工作。憑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在政府謀個一官半職,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說,“只有終身之教授,哪有終身之校長”,不愿意過多參與政治。
父親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
“十二萬分”地佩服陳寅恪
父親一輩子很少欽佩什么人,能排得上號的,陳寅恪當列首位。
1929年離開安徽大學之后,父親回到北大待了一段時間,后來又應羅家倫的邀請,到清華大學國文系擔任教授。1932年,朱自清出國休假,父親代理過一年的國文系主任。
這時候,父親開始與陳寅恪往來密切。父親曾經說過,他“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先生,主要是因為陳先生的學問做得好。
父親曾有意校勘《大唐西域記》,但他不敢下手,因為他自覺梵文不行,要等陳先生眼睛好一點,拉他一起把《大唐西域記》的校勘做出來。
陳寅恪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代理國文系主任的父親找他出招考題的往事。這在當時還引起一場風波。
陳寅恪出的題目有一個對聯題,上聯是“孫行者”,要求考生對出下聯。這個題的本意是希望考生對出“胡適之”,但很多考生感覺這個題目很難,沒能對上來。當時的很多報刊還發表文章,聲討這個題目出得太離奇,陳先生曾專門寫有長文辯解過。這篇文章后來收在《陳寅恪集》里。
從那時開始,父親就與陳寅恪保持著深厚的友誼。抗戰后,父親南下昆明,陳寅恪也在那里待過一段時間。兩人經常一起外出散步,聊聊學問,談談讀書,偶有詩詞吟對。陳寅恪寫過一首《南湖》的詩,父親認真筆錄下來,這個原件現存于云南蒙自博物館。endprint
在西南聯大期間,父親完成了耗費他十年心血的《莊子補正》。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請他最佩服的陳寅恪為這本書作序。封面書名是請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寫的。
父親之所以對陳寅恪比較佩服,除了學問,還有他的獨立人格。新中國成立后,陳寅恪避居于嶺南大學,與政治遠離。后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曾有意特設一個職位,想請陳寅恪北上,并張羅了很多陳寅恪的學生、朋友前去動員,但都被陳寅恪婉言謝絕。
父親因為是全國政協委員,也曾接到類似的囑托,希望他能去廣州動員陳寅恪北上。但父親左思右想,最終沒有去。他應該還是比較了解陳先生內心的,對于他的那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銘記在懷。
父親的一生,就是按照這幾個字要求自己的。
一定要警惕日本這個民族
對于日本這個民族,父親一直抱有很大的警惕心。他一生去過三次日本,對這個民族太了解了。
他說,這個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地少人多,資源缺乏,因而一直覬覦著資源豐富的中國。對于這個民族,他一再強調不能有任何幻想,不能麻痹大意,要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正因為此,在九一八事變后,父親就特別留意日本,并在緊張的教學之余,埋頭翻譯出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告全日本國民書》,介紹日本由來已久的軍國主義思想,喚起民眾的警醒。
盧溝橋事變后,父親沒有能及時離開北京,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周作人曾兩次到我們家去動員,希望父親能去已被日本人掌控的北大教書,但父親借口“我現在身體不好”推辭了。
不久,日本憲兵又來家里抄家。我那時還小,但還有一點印象,記得日本憲兵來了以后,讓父親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開,然后拿走了一些信件。父親被搞得沒辦法,決定南下昆明,到西南聯大任教。
在西南聯大期間,父親應《云南日報》《中央日報》之邀,撰寫了一二十篇觀察日本問題的政論文章。
最近中日關系再度陷入冰河,此時重讀六七十年前父親關于日本的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叢生,不得不欽佩其觀察的獨到和思想的深邃。當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討論的許多問題,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證了。
1944年,在抗戰即將勝利前夕,父親就頗具前瞻性地寫下《日本敗后我們該怎樣對他》一文,主張一不向日本索要賠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點卻不可不據理力爭,就是琉球這個小小的島嶼必然要歸還中國”。
父親說,“這件事千萬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國民都要一致的堅決主張,務必要連最初喪失的琉球也都收回來”,“切不可視為一個無足重輕的小島,稍有疏忽,貽國家后日無窮之害”。只可惜,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果真貽害無窮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日本侵華給父親本人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禍災,但是他一直強調要理性冷靜地正確認識日本、正確認識日本人。
愛國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還是應該認真探尋這個獨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質,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確對待。
“貶低沈從文”是子虛烏有
關于父親在西南聯大的生活,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那就是他怒斥沈從文“跑警報”的傳聞。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軍飛機頻頻侵擾昆明,于是“跑警報”稱為一道風景。我們一開始住在一丘田,一旦敵機來了,就趕緊往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跑。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剛跑到那塊空地上,一架飛機就俯沖下來了,我甚至看到了飛機上日本兵的風鏡。幸好父親一下撲到我身上,讓我躲過一劫。后來我們搬到了龍翔街五號,過了馬路,走三四百米,就是學校。要跑警報的話,再走幾百米,就是虹山。
搬到龍翔街后,由于敵機經常來襲,學校開課也不正常了,我就在家,沒怎么上學。那時候,日本的飛機一般從越南飛過來,快到云南境內的時候,負責監控的部門就會在五華山上掛紅燈籠,一個燈籠代表預行警報,就要準備跑了。
父親總是拿個布包,包一兩本書,再拿著茶壺,過馬路,到虹山。我們在虹山還挖了個洞,飛機來的時候就躲在洞里,飛機走了就出來談天說地,還有賣小吃的,跟平常的市井小巷生活沒什么區別。
現在聽到一種說法,父親在“跑警報”時看到沈從文從身邊跑過,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你替誰跑?”這個說法過去我沒聽到過,不知道從哪里傳出來的。我曾向父親的學生任繼愈先生打聽過這件事,他也說沒有聽說過,我覺得不符合情理。
我特意查了一下,沈從文當時住丁字坡,在昆明的東邊,要跑警報的話,應該往圓通山方向。我們當時在龍翔街,在昆明的西邊,方向不同,根本碰不著。而且當時大家都是在逃命的情況下,父親跟他又沒有什么仇恨,按常理不會說出這種超出人之常情的話。所以說,這個說法是不可信的。
還有一種說法,西南聯大要評定沈從文為教授,獨獨父親提出反對意見,說“如果沈從文都能評上教授,那我豈不是太上教授了”!這個其實也是沒有根據的臆測。西南聯大評定沈從文為教授的時候,父親已經應滇南鹽商的邀請去了云南磨黑,根本不在昆明,哪有機會說出這樣的話!
近些年,關于父親的傳聞很多,有的已經近乎空穴來風,有的則頗有來源,只不過有夸大演繹的成分。比如,很多文章都提到父親有個綽號“二云居士”,意思是說,父親一愛云南煙土,也就是鴉片,二愛云南火腿。
父親確實抽過鴉片。我大哥劉成章英年早逝之后,父親的心情一度非常郁悶,不知道遇到哪位朋友勸他抽抽鴉片,解解悶,這樣就抽上了。母親知道后,也沒說什么,抽就抽吧,總比天天悶悶不樂強。
到了云南以后,因為當地盛產煙土,幾乎家家都有個煙床,沒事就抽幾口。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拉黃包車的,都在抽鴉片。我記得,我岳父、岳母都有抽鴉片的習慣,不足為奇。那時候,走親訪友,主人和客人各躺在煙床兩邊,主人點好煙槍,抽上兩口,再遞給客人抽幾口,幾乎成了一種時尚。
但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就把鴉片戒掉了。至于說到云南火腿,我父親牙齒不好,并不怎么吃火腿,頂多就是吃一點火腿月餅,量也很小。所以說,“二云居士”的稱謂,其實并不完全確切。
(責任編輯:亞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