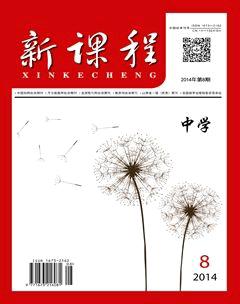在中國古代史教學中滲透可持續發展教育
摘 要:要實現人的持續發展,教育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將人類可持續發展教育納入基礎教育課程體系,要求歷史教師深入挖掘中學歷史教材中蘊含的可持續發展教育內容,以教材為載體,對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中國古代史;教學
可持續發展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這在1994年埃及召開的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上明確指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我國也指出:“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由此可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應該把培養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品質的人放在中心位置上。
這就對實施教育現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國實施教育現代化就需要根據可持續發展觀建立新的培養目標,現在的中學生就是十幾年后經濟建設的主力,他們頭腦中的觀念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所以幫助學生樹立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歷史學中凝聚了史學家對人類發展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和揭示社會生產與人類自身生產規律、法則的理解。這些極其富理性的人類活動的經驗和教訓有助于學生理解今天的現實,還可以指導他們未來的行動,為現實服務。所以,歷史教育在可持續發展教育中的真正意義在于將來為未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尋找智慧與
準則。
課堂教學是對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主渠道,但現實中我們的歷史教材更多的注重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演變,只從社會角度去詮釋中國、世界社會的歷史進程,忽視人地關系的分析,將自然環境與社會發展對立起來,很少同時從自然環境和社會變遷關系深入分析問題,更談不上用現代生態學去分析歷史問題。這樣,貫穿于中國古代歷史教學中的多是對無休止的墾殖、拓荒和人口膨脹絕對褒揚,特別是對一些主要因人為不合理開發和氣候變化造成生態環境變壞而衰落的分析,大多僅從社會角度加以分析。
如何在傳授歷史知識的同時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將歷史教育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有機的結合起來成為歷史教師研究的重要
課題。
筆者認為首先教師自身觀念要轉變,需要換一個角度去理解
歷史。
例如,在對我國各朝代的歷史學習中,都涉及到“以農為本”政策,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優良傳統,“以農為本”作為立國之策即使放到現代也不算錯。但如果能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相結合,去審視歷史,那么就會有不一樣的認識。比如,講到民族融合提到北方少數民族改游牧生活為農業定居生活,以往我們多以此自豪,認為是農耕文明對游牧文明的勝利,是中國民族大融合的表現,但從現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來看,它也是生態惡化的一個原因或說體現。雖然生活穩定了,但是草場變農田的局面帶來的結果是人口日益增長和土質沙化,導致經濟結構過分單一,社會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如果能在教學中進一步向學生指出“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往往因為政策上的誤導、理解上的偏差導致人們為了擴大耕地面積,人為地毀林開墾、圍湖造田,以致環境惡化,適當指出這一的消極方面,也富有教育意義。
再如歷次戰爭,我們更多的是分析戰爭的起因、過程、結果,很少去研究它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又比如我國歷朝歷代對黃河的治理,我們對此通常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去看待,把它作為某位統治者的政績,事實上,黃河之所以久治不愈,水患頻繁,正是自然對人類亂采伐、亂治理的懲罰。如果我們在教學中能夠透過這些現象看到本質,那么就會使學生認識到人應該與自然和諧相處,
從而認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其次,歷史教學的特點在于指導學生從人類社會進程中的正反兩個方面去認識:積極地善待自然或是無情地破壞自然所造成的不同結果,去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鑒往知來”的角度,給學生以深刻而發人深省的教育與啟迪,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人與自然和諧觀。在歷史教學中要轉變“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正確分析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使學生明確人類的活動破壞了環境,讓學生從思想上認識到:我們要想更好的發展就要保護環境,就必須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是歷史的唯一主角。傳統歷史學展現的是以人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的活動以及人的生產生活的圖景,人的作用完全超乎于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之上,即使涉及有關自然環境的因素。也只是一味地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或者利用。而這種觀念正是人類中心主義在歷史學中的直接反映,無疑鼓勵和助長了人類的貪婪和野心。
人類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就是由于強調“人定勝天”,盲目改造自然,過度開發土地,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最后文明隨之衰落毀滅的。例如: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由于不合理的水利灌溉和過度燒荒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而衰落了;印度哈拉帕文化,由于掠奪性開墾荒地,使土壤草皮化和沙漠化,最終走向衰落了;由于幾百年狂濫的農業開發、毀林開荒,瑪雅人失去了沃土,也失去了曾孕育瑪雅文明的基礎,最終,瑪雅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國樓蘭古國絕跡,絲綢之路改道,曾經是“天蒼蒼,野莽莽,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河套地區正日益受到沙漠化威脅,無一不是是大自然對人類不尊重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法則的懲罰。作為歷史教師,應當引導學生反思人類的行為,從歷史的角度反思地球的環境狀況,理性地思考人類在向自然索取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從而樹立責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面對當今人類生存環境的嚴峻形勢,歷史教師應充分挖掘歷史發展中的環保內容,在吸取先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經驗和教訓基礎上,使學生提高對國家、民族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憂患意識,增強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在講古代原始人類遺址時,課上提到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就誕生在黃河兩岸。它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目睹了歷代王朝的興衰成敗。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古代黃河的一些情況。黃河原稱“河”,西漢初年才有“黃河”一詞。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環境狀況良好,適合農業生產。中游氣候溫和,森林覆蓋率在50%以上,下游氣候濕潤,湖泊較多。那時的黃河清澈、晶瑩,也較溫順。雖然每到夏季來臨,暴雨成災,河水暴漲,淹沒一些農舍田莊,但它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情況。如今黃河為什么會這樣暴戾?黃河的暴戾有其自己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對環境的嚴重破壞,增加了自然災害的危害程度,商鞅變法時開展了大規模的墾殖,結果破壞了西安附近森林和秦嶺北坡邊緣森林。到秦始皇時期,因大興宮室,這里所剩余的樹木被砍伐殆盡,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黃河河水泥沙含量增多,河床因泥沙淤積而抬高,黃河開始泛濫。治理黃河成為漢朝統治者不得不時常關心的大事。漢武帝時期大規模治理黃河,以后八十多年里,黃河沒有發生過大水災,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但此后的人們并未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加之以古代中國重農輕牧的現象,黃河流域植被破壞成為長期、大量的現象。“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親河終于成了“中華之憂患”。與黃河水患的搏斗,成了中原大地上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
中國經驗型的文化傳統蘊藏著豐富的可持續發展內涵。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緣起緣滅”等思想,這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對于今天我們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指導作用,關心自然、愛護自然,教育學生學會關心生態環境,樹立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道德觀、倫理觀、法律觀具有重要意義。
從孟子的“盡心、知性、知無”,到董仲舒的“天亦有喜怒之氣、天人一也”都在強調“天地與我根,不得萬物與我一體”。管仲認為“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管子·地數》)。他提醒人們保護山湖草木,注意防火,按時封禁和開放,反對過度采伐。荀子根據生物資源消長規律,提出了一套保護生物資源的理論和措施。他說:“養長時,則六畜生,殺生時,則草木植。”“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正是這種思維才使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
秦國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了綜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既免除水災,又灌溉田地,避免了水土流失,為川西平原變成千里沃野創造了條件,使川西富庶一方,“天府之國”故此得名;都江堰在兩千年過去了至今仍造福于人民,它不僅給后人樹立了一個改造自然,保護環境,發展經濟的光輝典范,更為后人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寶貴經驗。
沒有歷史,一個社會就不會對自已的歷史起點,它的核心價值觀,以及過去的決定對當前的影響有一個共同的銘憶;沒有歷史,就不能對社會中政治的,社會的或道德的問題進行任何合理的探究,人們就不可能成為見識奇廣,有鑒別能力的公民。歷史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在環境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中應該并且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歷史教育應在經過一番探索之后,培養起學生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自覺意識,在當前普遍受到重視的可持續教育領域中作出本學科的獨特貢獻。
參考文獻:
陳鶯.為了可持續未來的中學歷史教育[D].福建師范大學,2007.
作者簡介:龔驕陽,女,1978年8月出生,本科,就職學校:北京一零一中學,研究方向:中學歷史教育。